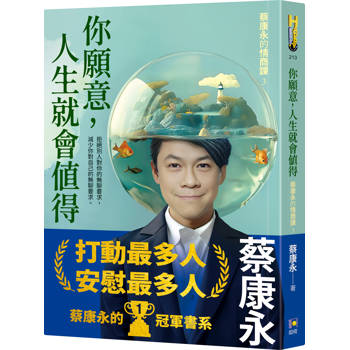經典文學名著,語文新課標推薦課外閱讀圖書。是托爾斯泰思想藝術的總結。作品以一起真實的刑事犯罪為基礎,通過描寫男女主人公複雜曲折的經歷,展示了當時俄國社會的黑暗,在深刻批判、司法、教會、土地私有製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同時宣揚不以暴力抗惡和自我修身的思想。此次收入“教育部統編《語文》推薦閱讀叢書”,特為中小學生課外閱讀製作,書前配有“導讀”,書後有“知識鏈接”,以給青少年朋友以必要閱讀指引和知識積累。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復活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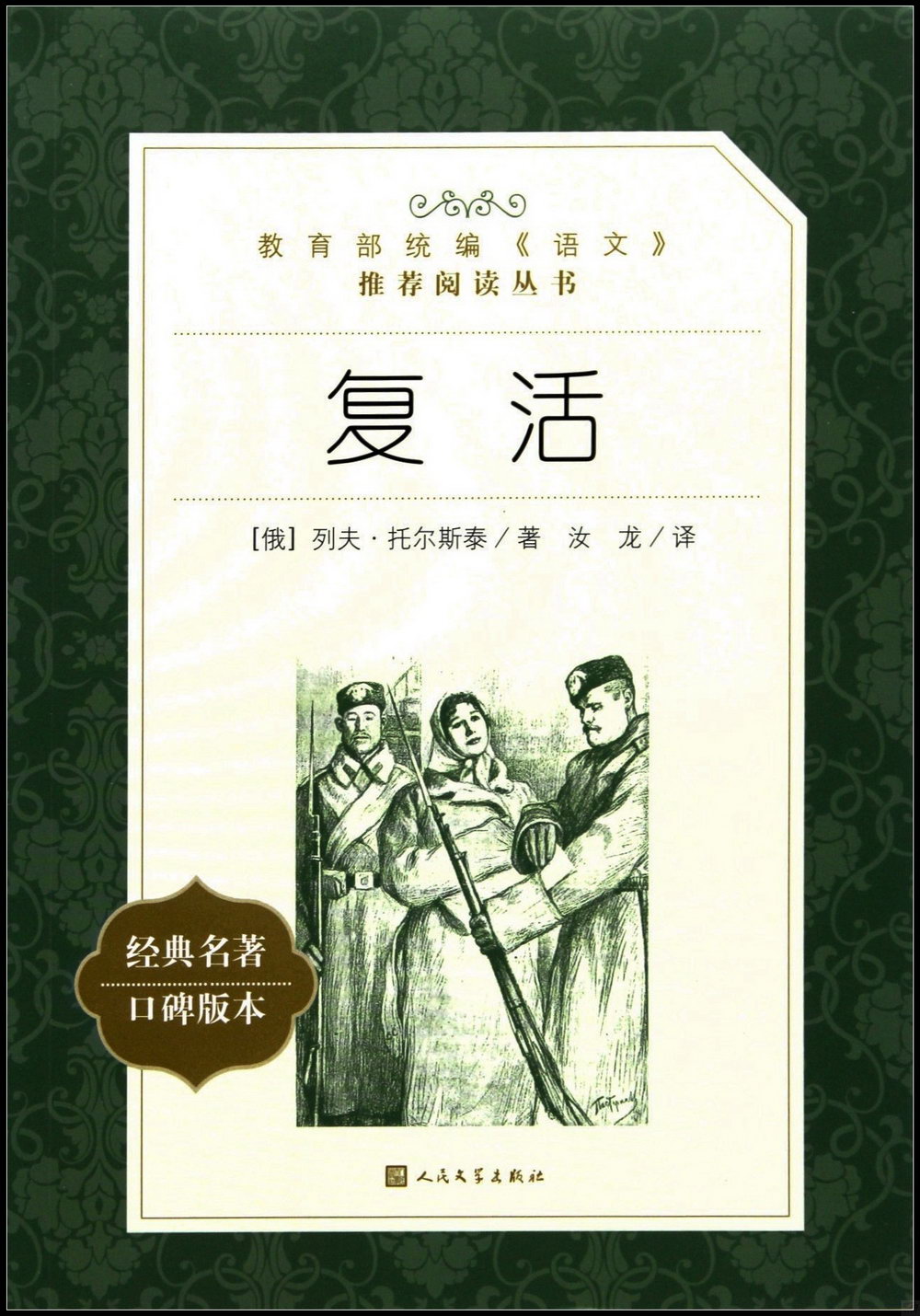 |
復活 作者:(俄羅斯)列夫·托爾斯泰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04-01 語言:簡體中文 規格:平裝 / 602頁 / 16k/ 22.4 x 15.8 x 3.6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2-1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復活
內容簡介
序
十九世紀末,俄國文壇出現了一部優秀的長篇小說《復活》。它和《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寧娜》一起成為托爾斯泰的三部代表作。
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出生於俄國一個大貴族家庭,本人是伯爵,早年受西歐啟蒙主義思想的影響,所以在他的前期創作,即十九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作品中,既不滿於專制農奴制、貴族階級的寄生和腐朽,又憎惡資本主義社會的“文明”,但還寄希望於“理想”的貴族,幻想通過溫和的改革使貴族和人民“互相親近”,變矛盾為“和諧”。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社會的劇烈變動,加上本人緊張的思索,引起了他的世界觀的劇變。他拋棄了上層貴族地主的一切傳統觀點,完全否定他所屬的那個階級,轉到宗法制農民的觀點上來,成為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廣大農民群眾思想情緒的表達者。同時,他又提出“勿以暴力抗惡”“道德自我完善”“博愛”等作為救世新術。這兩個互相對立的方面,使托爾斯泰顯得既偉大又可笑。而《復活》恰好是這兩個對立面的體現。
托爾斯泰的許多作品往往有真人真事為基礎,《復活》也一樣。一八八七年六月,彼得堡某地區法院的檢察官科尼來到托爾斯泰的莊園做客,講述了他接觸的一個案件:一個叫羅扎麗·奧尼的妓女被指控偷竊醉酒的嫖客一百盧布,判處監禁四個月。一位出庭當陪審員的青年貴族,認出了她就是當年被他誘姦過的親戚家之養女,那時她才十六歲。他良心發現,要求同女犯結婚以贖回過失,請求科尼協助解決。這個故事啟發了托爾斯泰的靈感,他便想據此寫一本以懺悔為主題的道德教誨小說。在十年的創作過程中,幾經思考,六易其稿,終於成書。但此時作者談到小說的主題思想已是“要講經濟的、政治的、宗教的欺騙”,“也要講專制制度的可怕”。
確實,《復活》對俄國社會的揭露和批判達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它以主要的篇幅揭露法庭、監獄和政府機關的黑暗,揭露官吏的昏庸殘暴和法律的反動。在堂皇的法庭上,一群執法者各有各的心思,隨隨便便將一個受害的少女馬斯洛娃判刑。在主人公不服上訴的過程中,又進一步暴露了沙皇政府機構從上到下都沒有好人:國務大臣是個貪賄成性的吸血鬼,樞密官是鎮壓波蘭人起義的劊子手,掌管犯人的將軍極端殘忍,副省長經常以鞭打犯人取樂,而獄吏也以折磨犯人為能事。作者據此憤怒地指出:人吃人的行徑並不是從原始森林裡開始,而是從政府各部門、各委員會、各司局裡開始的。
小說又撕下了官辦教會“慈善”的面紗,暴露神父麻醉人民的騙局,讓人們看清俄國政府和教會狼狽為奸的實質。小說不但比托爾斯泰過去的任何作品都更為深刻地指明了農民貧困的根源是地主的土地佔有製,而且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給農民帶來的雙重災難。這些方面無疑是小說的精華,可以說《復活》恰好反映了千百萬農民要求徹底剷除官辦教會、打倒地主階級及其政府、消滅地主土地佔有製並且進一步消滅資本主義剝削的願望和決心,托爾斯泰實際上提出了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托爾斯泰的確是偉大的思想家。
但是小說在反對政府及統治階級壓迫和奴役人民的同時,卻呼籲“禁止任何暴力”,否定暴力革命;在反對官辦教會的偽善時,卻主張信仰“心中的上帝”,號召人們“向你心中的上帝”祈禱,“天國就在你們心裡”;反對地主和資產者的剝削也只停留在軟弱無力的怨訴、咒罵上。更有甚者,作者的“博愛”思想競包括“愛仇敵、為仇敵效勞”,小說宣揚“要永遠寬恕一切人”,這就不但是錯誤,而且在俄國革命日益逼近的年代,越發顯得有害了。
所以,列寧在評價托爾斯泰時說得很中肯:托爾斯泰一方面“在晚期的作品裡,對現代一切國家製度、教會制度、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達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是“創作了世界文學中第一流作品”的“天才的藝術家”;另一方面,他是狂熱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惡”等教義的“托爾斯泰主義者”,“即是一個頹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憐蟲”。
托爾斯泰在這部小說中塑造了一個豐滿而復雜的形象——涅赫柳多夫公爵,這是一個“懺悔貴族”的典型。作者是運用他的“心靈辯證法”,即在這個人物思考和探索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中,充分展示人物思想的辯證發展,來刻畫人物的。
涅赫柳多夫出於貴族闊少的劣性,誘奸了天真純潔的農奴少女馬斯洛娃,從此把她推人墮落和不幸的深淵。但是,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惡行,而且是貴族階級對他影響的結果。他本來是一個純潔善良、有理想、追求真正愛情的青年,貴族家庭養成了他的種種壞毛病,貴族社會和沙俄軍界紙醉金迷、放浪荒唐的生活風氣又使他墮落,促使他去傷害馬斯洛娃。因此,他是貴族地主階級罪惡的體現者。
他由於青年時代受過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的影響,個人身上的善良品性也還沒有完全泯滅,加上他有尋根究底的好思索的性格,因此他和別的紈絝子弟多少有些不同。所以十年後他在法庭上重新見到馬斯洛娃時,才能被她的悲慘遭遇震驚,產生了懺悔之心。他先是承認自己“犯了罪”,決定替被冤枉判刑的馬斯洛娃上訴申冤,藉以挽救她,也為自己贖罪。當他奔走於各級政府機關,活動於權貴之門時,看到統治階級和國家機器的專橫無理,逐步意識到本階級的罪孽深重。在懺悔和醒悟的涅赫柳多夫眼裡,原來習以為常的生活驟然變了個樣,一切都顯得是罪惡的了。他憤怒起來,揭露了法庭、監獄、政府機關和官辦教會的黑暗。他看出農民貧困的“主要原因就在於他們用來養家活口的土地,都被地主奪去了”,還有資本主義對他們的禍害。於是他大聲疾呼:這種可怕的狀況“萬萬不可再繼續下去了”。所以他又是貴族地主階級罪惡的揭露者和批判者。
這種揭露和批判是來自舊營壘中的反戈一擊,所以就特別有力。不但如此,他還進一步對革命者產生了同情心,決定交出土地,到西伯利亞去,有了投向人民的表示。在整個過程中,他的貴族階級舊性不斷死灰復燃,因此他每走一步都要經過痛苦的鬥爭。這一切都使得這個人物形象顯得豐滿和真實可信。
涅赫柳多夫出現在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俄國,當時農民和地主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白熱化,他的懺悔和對本階級的背離,表明貴族地主階級內部分崩離析。他的這些活動正好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本質。
然而涅赫柳多夫究竟舊性蕩滌未盡,他只能在“愛”的宗教裡求得解脫,宣揚起“勿抗惡”和“道德自我修養”來,甚至乾脆捧出《福音書》來宣傳“愛仇敵、幫助敵人”的教義。這個形像變得更為複雜了。這是他貴族階級的局限性,也是作者世界觀的局限性。
同樣,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馬斯洛娃也是個成功的人物形象。她是農奴的私生女,被地主太太收養,半婢女半養女的身份也不能使她逃脫厄運。先是被地主少爺誘騙,懷孕後被趕出家門,走投無路,終於淪落為娼。繼而蒙冤被判刑,完全成了社會的犧牲品。
因此,她對這個社會懷著刻骨仇恨,以致當涅赫柳多夫去向她懺悔時,她還加以怒斥。不過她的轉變也是可信的。因為男主人公不僅已經轉過來關心她今後的命運,而且還要替其他無辜的“犯人”申訴。她開始信任他,接受他的規勸,表示要“向善”。她去西伯利亞受到革命者的思想影響,感情起了變化,和他們“打成一片”,終於完成了轉變,達到精神和道德上的“復活”。她從人民中來,又回到了人民當中。這個歸宿也是符合實際的。
然而,作者把女主人公的精神“復活”又歸結到“寬恕”和“仁愛”。這又讓人們難以理解了。
總之,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現實中的典型,他們的性格既複雜,又是完整的,其思想性格的發展變化都是合乎邏輯的。不過作者認為引起這種變化的原因在於每個人身上彷彿都有“獸性的人”和“精神的人”在互相對抗,“獸性的人”佔了上風,人就作惡;“精神的人”取勝了,人就向善。這種離開了社會環境的影響,而以“人性”和“獸性”的矛盾來解釋人的墮落、懺悔以及精神“復活”等問題的做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然而《復活》依然是一部輝煌的鉅作,它以深刻的描寫震撼著人們的心靈,空前的成就使它登上了十九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高峰,並成為不朽的世界名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