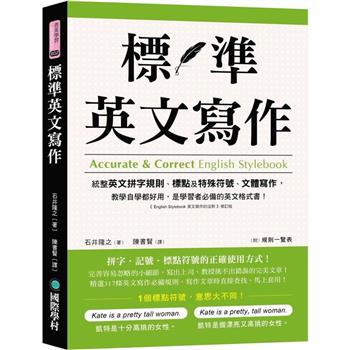五十二歲的大衛·盧裡教授離了婚;他充滿欲望,卻缺乏激情。一段和學生之間的情事使他失業後,他遭到朋友的回避,遭到前妻的嘲笑,只好退居於女兒露西的小莊園。盧裡教授的短暫訪問演變成期的逗留——他試圖在這一僅存的與他人的關係中找到生活的意義。然而,一場難以想像的事件迫使父女倆不得不面對他們之間的矛盾,以及新南非社會中複族狀況。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恥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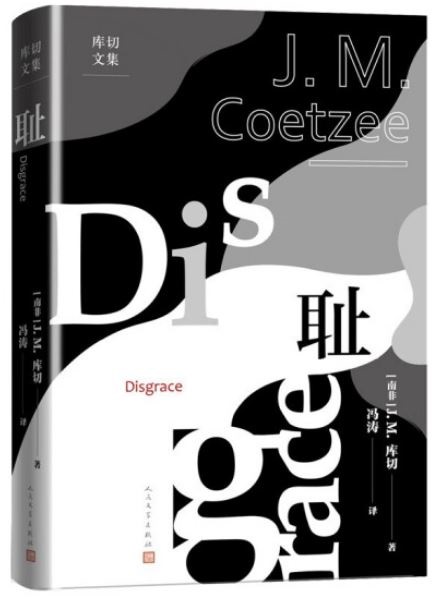 |
恥 作者:(南非)J.M.庫切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09-01 語言:簡體中文 規格:精裝 / 301頁 / 32k/ 13 x 19 x 1.5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恥
內容簡介
序
沉淪與救贖
《恥》譯後記
二〇〇三年,南非作家約翰·麥斯威爾·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因“通過眾多的假面描述了局外人如何被捲入始料未及的生活之中”(who in innumerable guises portrays the surprising involvement of the outsider)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而在此以前,他已經於一九八三年因《邁克爾·K的生活與時代》、一九九九年因《恥》兩次榮獲布克獎,成為有史以來兩獲布克獎的第一人。
庫切一九四〇年二月九日出生於南非開普敦的一個阿非利堪人(荷蘭裔南非白人)家庭,父親學的是法律,但只斷斷續續地做過律師,此外還做過政府雇員、參過軍,後來因為涉嫌挪用款項而放棄了律師工作,只能在一家小公司裡擔任會計工作,母親是位具有知識份子氣的小學教師。他們雖是阿非利堪人,並非英國後裔,在家庭當中卻一直都講英語,和他農場的親戚們講阿非利堪語(南非荷蘭語)。庫切小時候因為父親職業上的污點,因為他的罔顧家庭和酗酒貪杯而跟他關係疏遠,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對他憎惡不已;和母親則極為親密,他對這種母子間過於親密的關係有充分甚至過度的自覺,對這種關係既無比依戀,同時又有意識地想要抗拒和掙脫。長大後他對自己與父親的關係也有深刻的反思,這種反思集中體現在他的第三部自傳體小說《夏日》當中。庫切父系的祖上一直擁有一座“百鳥噴泉”農場,他一直將其視為他精神的故鄉,他的“初始地”,對他的成長和創作都起過極為重要的影響。
庫切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在中學階段哪怕是考試成績位元列第二都會難過不已。就讀開普敦大學期間修讀了英語文學和數學兩個專業,並且全都拿到了榮譽學位。一九六二年,庫切離開南非,來到了倫敦。南非從一九四八年起正式開始實施種族隔離政策,六十年代正是種族隔離最為劍拔弩張的時期,對所有的南非白人青年實行義務兵役制,而他隨時都有被強征入伍的危險。庫切到倫敦去,首先就是為了逃避兵役,他在第二部自傳體小說《青春》中明確說過:去當兵“他可受不了,他會割腕的。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走”。而所以去倫敦是因為英國是南非的宗主國,是他文化上的母國,在第一部自傳體小說《童年》中庫切就曾描述過他對英國的嚮往:“對於英國和與英國有關的一切事物,他深信自己都懷有忠誠的信念。”他在一篇文章中對從殖民地來到英國的奈保爾的評論也完全適用於他自身:“(他們)接受的殖民地教育,按照大都會的標準,是滑稽過時的。然而,正是這種教育使他們成為一種在母國已經衰微的文化的受託人。”
擁有數學學位的庫切在倫敦得以進入IBM公司工作,成為第一代電腦程式師,這也正是他在大學修讀數學的初衷:雖然“愛”與“藝術”才是人生中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標,但你得先有能力養活自己。與此同時,他決定遠端完成開普敦大學的英語碩士學位。雖然他最喜歡的詩人是龐德和艾略特,他還是選擇英國小說家福特·馬多克斯·福特作為他碩士論文的研究物件,因為龐德認為福特是被文學界所忽視的最偉大的散文作家,他基本上認同這一判斷。完成碩士論文後,他感覺身處冷戰時期的倫敦就像是陷入了一條死胡同,開始申請美國大學的助學金,一九六五年通過富布萊特專案的資助進入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攻讀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是借助電腦對他最喜歡的散文作家撒母耳·貝克特早期的小說作品進行風格分析。一九六三年,庫切返回南非完成碩士論文期間,與大學同學菲麗帕·賈伯爾結婚,而他的兒子尼古拉斯和女兒吉塞拉都是他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出生的。
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一年,庫切在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擔任助理教授,他尋求在美國的永久居留身份,提出的主要申請理由,是他出生於美國的一雙兒女如果不得不返回實行嚴格的種族隔離的南非有可能遭遇的種種困境。此時美國國內反對越戰的呼聲越來越高,學校當局對校內的反戰活動卻採取壓制政策,並請警方進駐學校。歷來不願意參加任何公眾集會的庫切,這次和同事們一起前往校長辦公室進行靜坐抗議,結果他們共四十五人因“非法侵入”罪而被逮捕。雖然後來完全撤銷了對他們的指控,但他永久居留美國的申請卻也因此而遭到拒絕。
無奈返回南非以後,庫切在自己的母校開普敦大學的英語系某到了教職,直到他於二〇〇一年十二月退休,一直都在這裡任教。一九八三年他被晉升為總體文學(相對于國別文學)教授,一九九九年以後更是被聘為傑出文學教授。一九八四至二〇〇三年間,庫切受邀經常性地在美國多所大學短期任教,其中包括紐約州立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哈佛和斯坦福大學,尤其是擔任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的委員和教授達六年之久,每年在芝大任教三個月。二〇〇二年,他與伴侶桃樂西·德萊弗一起移居澳大利亞的阿德萊德市,任阿德萊德大學英語系的名譽研究員,桃樂西也在同一所大學擔任學術研究員。二〇〇六年,庫切正式入籍澳大利亞,成為澳大利亞公民。
庫切於一九六九年開始他的文學創作,第一部小說《幽暗之地》於一九七四年在南非出版。一九七七年的《內陸深處》獲得南非最重要的CNA獎,在英美兩國出版,一九八〇年的《等待野蠻人》引起國際關注,而一九八三年的《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真正為他贏得了國際聲譽,榮獲布克獎。一九八六年出版重述魯濱孫故事的《福》,一九九〇年出版《鐵器時代》,一九九四年出版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主角的小說《彼得堡的大師》,一九九九年出版《恥》,為他贏得了第二個布克獎。定居澳大利亞以後,庫切於二〇〇五年出版小說《慢人》,二〇〇七年出版《凶年紀事》,二〇一三年出版《耶穌的童年》,二〇一六年出版其續篇《耶穌的學生時代》。
庫切對於自傳體寫作一直具有濃厚的興趣並持有獨到的見解,他認為所有的自傳都是在講故事,而所有的創作都是一種自傳。藝術家的創作目的不是為了忠實地再現事實,而是要使用與處理事實:“真正的自傳取決於資料的選擇和遺漏”,經過這種有意的選擇與遺漏以後,藝術家能比歷史家呈現出更為完整的人性真相。秉持這樣的原則,庫切創作了三部自傳體藝術作品:一九九七年的《男孩》、二〇〇二年的《青春》和二〇〇九年的《夏日》。
一九九九年的《動物的生命》是一部小說化的批評著作,二〇〇三年作為一部分被納入更為完整的同類型的作品《伊莉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凶年紀事》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視為這樣的作品。一九八八年的《白人寫作》是一組論述南非文學和文化的論文,一九九二年的《雙重視角》兼收他的論文以及與大衛·阿特維爾之間的訪談,一九九六年的《冒犯》是對南非種族隔離政策之下文學審查的專題研究,二〇〇三年的《異鄉人的國度》收集了他後期的文學評論作品。二〇一三年的《此時此地》是庫切與美國作家保羅·奧斯特的通信集,二〇一五年出版了與阿拉貝拉·庫爾茨合寫的《好故事:事實、虛構與精神療法的交流》。
庫切是當代文學界著名的隱士,他不喜歡抛頭露面,不喜歡接受記者的採訪,不喜歡談論自己的作品(他曾對自己的傳記作者J.C.坎尼米耶明確表示:“我一直遵循的原則是讓我的書在不受我的任何干預的情況下進入這個世界。我特別不希望在書上面加上任何作者的解釋。”),身為兩獲布克獎的第一人,這兩次頒獎他竟然都沒有出席。南非作家裡安·馬蘭曾說:“庫切是個幾乎具有僧侶般自律和獻身精神的人。他不喝酒、不抽煙、不吃肉。他騎行很長的距離以強身健體,一周的七天裡每天早上都至少花一個小時用於寫作。一個和他共事過十多年的同事說只見他笑過一次。一個和他一起參加過幾次宴會的熟人說沒有聽他說過一句話。”
《恥》譯後記
二〇〇三年,南非作家約翰·麥斯威爾·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因“通過眾多的假面描述了局外人如何被捲入始料未及的生活之中”(who in innumerable guises portrays the surprising involvement of the outsider)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而在此以前,他已經於一九八三年因《邁克爾·K的生活與時代》、一九九九年因《恥》兩次榮獲布克獎,成為有史以來兩獲布克獎的第一人。
庫切一九四〇年二月九日出生於南非開普敦的一個阿非利堪人(荷蘭裔南非白人)家庭,父親學的是法律,但只斷斷續續地做過律師,此外還做過政府雇員、參過軍,後來因為涉嫌挪用款項而放棄了律師工作,只能在一家小公司裡擔任會計工作,母親是位具有知識份子氣的小學教師。他們雖是阿非利堪人,並非英國後裔,在家庭當中卻一直都講英語,和他農場的親戚們講阿非利堪語(南非荷蘭語)。庫切小時候因為父親職業上的污點,因為他的罔顧家庭和酗酒貪杯而跟他關係疏遠,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對他憎惡不已;和母親則極為親密,他對這種母子間過於親密的關係有充分甚至過度的自覺,對這種關係既無比依戀,同時又有意識地想要抗拒和掙脫。長大後他對自己與父親的關係也有深刻的反思,這種反思集中體現在他的第三部自傳體小說《夏日》當中。庫切父系的祖上一直擁有一座“百鳥噴泉”農場,他一直將其視為他精神的故鄉,他的“初始地”,對他的成長和創作都起過極為重要的影響。
庫切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在中學階段哪怕是考試成績位元列第二都會難過不已。就讀開普敦大學期間修讀了英語文學和數學兩個專業,並且全都拿到了榮譽學位。一九六二年,庫切離開南非,來到了倫敦。南非從一九四八年起正式開始實施種族隔離政策,六十年代正是種族隔離最為劍拔弩張的時期,對所有的南非白人青年實行義務兵役制,而他隨時都有被強征入伍的危險。庫切到倫敦去,首先就是為了逃避兵役,他在第二部自傳體小說《青春》中明確說過:去當兵“他可受不了,他會割腕的。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走”。而所以去倫敦是因為英國是南非的宗主國,是他文化上的母國,在第一部自傳體小說《童年》中庫切就曾描述過他對英國的嚮往:“對於英國和與英國有關的一切事物,他深信自己都懷有忠誠的信念。”他在一篇文章中對從殖民地來到英國的奈保爾的評論也完全適用於他自身:“(他們)接受的殖民地教育,按照大都會的標準,是滑稽過時的。然而,正是這種教育使他們成為一種在母國已經衰微的文化的受託人。”
擁有數學學位的庫切在倫敦得以進入IBM公司工作,成為第一代電腦程式師,這也正是他在大學修讀數學的初衷:雖然“愛”與“藝術”才是人生中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標,但你得先有能力養活自己。與此同時,他決定遠端完成開普敦大學的英語碩士學位。雖然他最喜歡的詩人是龐德和艾略特,他還是選擇英國小說家福特·馬多克斯·福特作為他碩士論文的研究物件,因為龐德認為福特是被文學界所忽視的最偉大的散文作家,他基本上認同這一判斷。完成碩士論文後,他感覺身處冷戰時期的倫敦就像是陷入了一條死胡同,開始申請美國大學的助學金,一九六五年通過富布萊特專案的資助進入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攻讀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是借助電腦對他最喜歡的散文作家撒母耳·貝克特早期的小說作品進行風格分析。一九六三年,庫切返回南非完成碩士論文期間,與大學同學菲麗帕·賈伯爾結婚,而他的兒子尼古拉斯和女兒吉塞拉都是他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出生的。
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一年,庫切在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擔任助理教授,他尋求在美國的永久居留身份,提出的主要申請理由,是他出生於美國的一雙兒女如果不得不返回實行嚴格的種族隔離的南非有可能遭遇的種種困境。此時美國國內反對越戰的呼聲越來越高,學校當局對校內的反戰活動卻採取壓制政策,並請警方進駐學校。歷來不願意參加任何公眾集會的庫切,這次和同事們一起前往校長辦公室進行靜坐抗議,結果他們共四十五人因“非法侵入”罪而被逮捕。雖然後來完全撤銷了對他們的指控,但他永久居留美國的申請卻也因此而遭到拒絕。
無奈返回南非以後,庫切在自己的母校開普敦大學的英語系某到了教職,直到他於二〇〇一年十二月退休,一直都在這裡任教。一九八三年他被晉升為總體文學(相對于國別文學)教授,一九九九年以後更是被聘為傑出文學教授。一九八四至二〇〇三年間,庫切受邀經常性地在美國多所大學短期任教,其中包括紐約州立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哈佛和斯坦福大學,尤其是擔任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的委員和教授達六年之久,每年在芝大任教三個月。二〇〇二年,他與伴侶桃樂西·德萊弗一起移居澳大利亞的阿德萊德市,任阿德萊德大學英語系的名譽研究員,桃樂西也在同一所大學擔任學術研究員。二〇〇六年,庫切正式入籍澳大利亞,成為澳大利亞公民。
庫切於一九六九年開始他的文學創作,第一部小說《幽暗之地》於一九七四年在南非出版。一九七七年的《內陸深處》獲得南非最重要的CNA獎,在英美兩國出版,一九八〇年的《等待野蠻人》引起國際關注,而一九八三年的《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真正為他贏得了國際聲譽,榮獲布克獎。一九八六年出版重述魯濱孫故事的《福》,一九九〇年出版《鐵器時代》,一九九四年出版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主角的小說《彼得堡的大師》,一九九九年出版《恥》,為他贏得了第二個布克獎。定居澳大利亞以後,庫切於二〇〇五年出版小說《慢人》,二〇〇七年出版《凶年紀事》,二〇一三年出版《耶穌的童年》,二〇一六年出版其續篇《耶穌的學生時代》。
庫切對於自傳體寫作一直具有濃厚的興趣並持有獨到的見解,他認為所有的自傳都是在講故事,而所有的創作都是一種自傳。藝術家的創作目的不是為了忠實地再現事實,而是要使用與處理事實:“真正的自傳取決於資料的選擇和遺漏”,經過這種有意的選擇與遺漏以後,藝術家能比歷史家呈現出更為完整的人性真相。秉持這樣的原則,庫切創作了三部自傳體藝術作品:一九九七年的《男孩》、二〇〇二年的《青春》和二〇〇九年的《夏日》。
一九九九年的《動物的生命》是一部小說化的批評著作,二〇〇三年作為一部分被納入更為完整的同類型的作品《伊莉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凶年紀事》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視為這樣的作品。一九八八年的《白人寫作》是一組論述南非文學和文化的論文,一九九二年的《雙重視角》兼收他的論文以及與大衛·阿特維爾之間的訪談,一九九六年的《冒犯》是對南非種族隔離政策之下文學審查的專題研究,二〇〇三年的《異鄉人的國度》收集了他後期的文學評論作品。二〇一三年的《此時此地》是庫切與美國作家保羅·奧斯特的通信集,二〇一五年出版了與阿拉貝拉·庫爾茨合寫的《好故事:事實、虛構與精神療法的交流》。
庫切是當代文學界著名的隱士,他不喜歡抛頭露面,不喜歡接受記者的採訪,不喜歡談論自己的作品(他曾對自己的傳記作者J.C.坎尼米耶明確表示:“我一直遵循的原則是讓我的書在不受我的任何干預的情況下進入這個世界。我特別不希望在書上面加上任何作者的解釋。”),身為兩獲布克獎的第一人,這兩次頒獎他竟然都沒有出席。南非作家裡安·馬蘭曾說:“庫切是個幾乎具有僧侶般自律和獻身精神的人。他不喝酒、不抽煙、不吃肉。他騎行很長的距離以強身健體,一周的七天裡每天早上都至少花一個小時用於寫作。一個和他共事過十多年的同事說只見他笑過一次。一個和他一起參加過幾次宴會的熟人說沒有聽他說過一句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