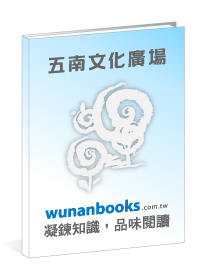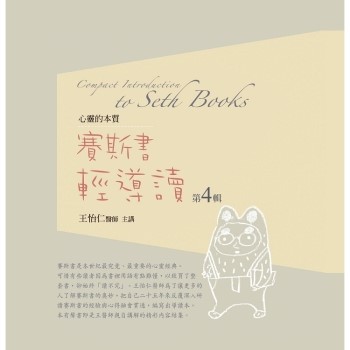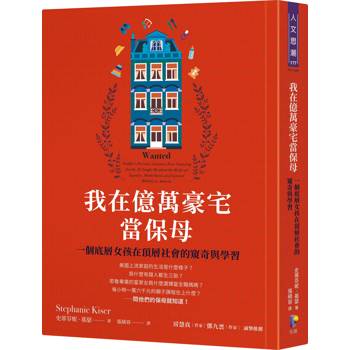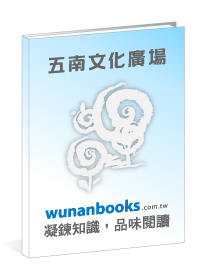 |
| 柳弧(22)
作者:〔清〕丁柔克 撰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02-08-01
語言:簡體中文 規格:384頁 / 20 x 14 cm / 普通級/ 初版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目前評分: 評分:
圖書名稱:柳弧(繁體版) 內容簡介
《柳弧》是一部清人筆記稿本,今存六卷。書中所記大多是發生在作者身邊的真人真事或道聽途說的奇聞逸事,對於了解清代末期的社會生活狀況和風土人情,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其中某些篇章,還具有較高的史料性。
作者丁柔克(1840-?),號燮甫,江蘇泰州人。其父丁楚玉,字子琳,道光十六年(1836年)進士,官雲南蒙自等縣知縣,咸豐中病逝於任所。丁柔克的岳父賈洪詔,字金門,湖北均州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進士,官至雲南巡撫,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卒,年九十三歲。
丁柔克自幼聰穎好學,琴棋書畫,醫卜星相,無不涉獵。賈洪詔稱他「無書不讀」,「壯志有奇氣」。但他早年顛沛流離,抑郁不得志。科場失意後,便捐了個候補道員的餃名。他曾在湖北省城內擔任過負責治安工作的總查官,本書《丁總查》一文,就是他有關這段經歷的自述。文中述及一個因貧困而行竊的人再度被捕時,丁柔克不但沒有嚴厲地處罰他,反而賜給他一千四百文錢,並命地保買了扁擔和籮筐,幫助他以賣菜為生。每月還親自驗視兩次,終於使他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人。他這種對待犯人的態度和工作方法,在封建社會的官吏中是難能可貴的。正因為他富於同情心,又精明干練,所以頗有政聲。他生平最得意的事,要算是同治八年(1869年)七月署理湖北漢陽知府時,主持賑災工作,使「災民皆得其所」。可惜好景不長,僅僅數十天便告交卸了,時年二十九歲。
光緒七年(1881年),丁柔克得到主持湖北沔陽厘局的差事。「公事之餘,秋燈黃葉┅┅因取生平見見聞聞,奇奇怪怪,與夫一切一知半解拉雜筆之於書。」(賈洪詔序)據此可知《柳弧》的寫作始於光緒七年。又據作者在《柳弧》稿本封面上所書「光緒捌年七月上浣重編」手跡,可以得知此書的具體編定時間。但書中有關中法戰爭的文字,可以證明至少在光緒九年至十一年間(1883-1885年),作者尚在繼續增補。另外,作者在《碑帖》一篇中自稱「此書第七卷中,予有論一則」。可證《柳弧》至少原有七卷,而現在則僅存六卷了。又據丁柔克自稱,他還撰有小說《歸鶴瑣言》三十二回和《泰豆地理集》、《倒海探珠集》、《醫學星宿海》、《麋j n@①齋楹聯》、《玉壺鳳肺》、《青芙館秘書》等書,但均未見有刻本問世,亦未見著錄。
《柳弧》的內容很雜,凡風土人情、奇聞軼事、官場百態、醫卜星相、狐仙鬼怪,無所不有。其中不乏具有文獻價值的篇章。例如《嘉慶酷法》一篇,抄錄了一道嘉慶皇帝的上諭,這位死後被尊謚為仁宗的皇帝,對湖北武生鄧漢珍與妻黃氏毆母辱姑一案的處罰是極其殘酷的,「朕思不孝之罪,別無可加,惟有剝皮揚灰。族長不能教誨子弟,當問絞罪;左右鄰舍知情不報於上,杖八十,充發烏魯木齊;教官不能化善,杖六十充發;府縣不能治民,削職為民,子孫永不許入考;黃氏之母不能教誨其女,臉上刺字,游省四門,充發。仍將鄧漢珍與妻黃氏發回漢川,對生母剝皮揚灰示眾。鄧漢珍之家掘土三尺,永不許居住。」至此,他仍意猶未盡,又命令「湖北總督將此案勒碑石,垂諭各省州縣衛示知,嗣後倘有不孝,照例治罪」。其實,按大清律例,「凡子孫毆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毆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斬,殺者皆凌遲處死」。而嘉慶皇帝的處罰,遠比刑律規定更為殘酷,還株連了一大批無辜者。充分暴露了封建社會所謂「仁政」和「法制」的虛偽性和暴虐性。難怪連丁柔克也措詞委婉地感嘆道:「讀此煌煌天語,能不毛發灑淅。」這道上諭《清實錄》未收,大約實錄的編修官們也覺得這實在有損皇帝的形象了。
咸豐六年(1856年)丁柔克十六歲時,曾親歷過雲南之亂。事後他寫道:「雲南之亂,始於爭石羊廠,漢回互斗。咸豐五年,忽傳回人有命奸細來省放火藥局之語,值臬司某一示中有『格殺勿論』四字,於是一夜中漢人忽殺回人,無論良賤老幼皆殺之。平日腐儒稚子亦操刀殺人以為樂。┅┅咸豐六年,各府州縣之回人┅┅以復仇為名,旗幟衣履皆尚白,數千人直撲省城。┅┅遂圍城百餘日。後草根、樹皮皆盡,遂食皮帽盒等,煮而食之,臭不可聞。┅┅時恆制軍夫婦對縊死矣。予家時尚有七八十人,無米食,皆咽糠餅焉。」(詳見《雲南之亂》)通過這篇記載,我們可以了解這次事件的起因、規模及影響。
中法戰爭時,湖北「距外洋甚遠」,本不必過慮。但「鄂省自聞預備江防,先則購鵝卵石用銀四千餘兩,並造沉石方大櫃數十支。繼則買繩索數千條,效上古結繩而治,為一網打盡之計。後又買大木,用銀四萬餘兩。忽一旦聞和,則石也、繩也、木也,皆歸無用矣。」(詳見《鄂省江防靡費》)此篇雖短小,卻對鄂省官員的迂腐可笑和盲目浪費做了大膽的抨擊。
《柳弧》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其中有不少篇幅對形形色色的封建官吏的丑惡面目,做了深刻的揭露。例如江右某令,不甚識字,凡批文都要幕友代筆,然後塞入大筆管內備用。一日,幕友有急事外出,正逢某令要批文,取筆一看,里面空空如也。惶恐之餘,不禁惱羞成怒,投筆罵道:「今日我偏不寫,看你等怎樣?」一副無賴嘴臉,令人啼笑皆非。據說,「各省紛紛考官,實因此公而起」(詳見《傀儡縣令》)。又有某大吏,一向以理學自命,「一日過某處,眷口皆在舟中,忽被竊,大吏大怒,雷動風行,摘某縣頂嚴緝,令大懼。無何,案破。而贓物中有大吏綉花春宮褲一條,復有貂皮四腿褲一條,賊堅指為大吏之物,而大吏之理學遂敗。」(詳見《大吏諸相》)
更有甚者,雲南某大吏荒淫無度,不僅屢屢強占民女以發泄其獸欲,甚至連下屬官員的妻子也不放過,強留署中三日,致使女方自縊而死。其罪惡累累若此,上方卻一味庇護,竟然一直逍遙法外(詳見《滇撫淫暴》).
目錄
柳弧序
柳弧卷一
柳弧卷二
柳弧卷三
柳弧卷四
柳弧卷五
柳弧卷六
序
余婿於變埔,名柔克,名太守也。家於吳,籍於燕,生於滇,仁於鄂。幼失怙,遭滇回匪亂,奉母氏倉皇遁之黔,遭苗亂;之蜀,逢幗匪;後之豫、之吳,則捻道發奠無不遇,誠《石鼓》詩所謂「賊斫不死神扶持」者也。飢流東走,垂二十年。而南北大軍務,皆以道陰未得與。躓名場,後至都,有父執某慨助千金,恐隨手散盡,同人復族之,遂帶引至鄂。時二十三歲,非其志也。到省一年,丁嫡母難,解官去。同治丁卿起復,又至噪聲。次年得署漢陽府,年廿九歲。數十日即交卸,辦靈民皆得所,此變甫生平稍愜心事也。變甫為人美姿,壯志有奇氣,酒酣耳熟則起舞。思欲效命疆場,順則鴻毛,鈍則馬革,此太夫事也,天靳之。又無書不讀,目十行,有神童目、子才稱。思黃卷青燈,巍科顯仁,繼書香為先人後,而天又靳之。無已,或在噪聲得一實缺,生平抱負可展布,則一郡可大治,而天復靳之。需次二十余年不能履任,令人齒冷。二十年中,大吏皆憂容之,得一差奉母氏免飢寒。丁丑年,變甫忽大病,就木矣而復生。生則復奉母,真已有榮啟期之二樂,而三樂則不可必也。庚辰,彭芍誕中函位噪聲,用人行政,更覺大公,與論題之。辛巳,檄委變甫辦沔陽驚務。公事之余,秋燈黃呀,變甫因取生平見見聞聞、奇奇怪怪與夫一切一知半解拉雜筆之於書。書既成,丐序於余。余老矣,憂游林下,無復他望,惟視海宇升平,堯民鼓腹。變甫毋爾志,尤宜努力為官為人,以為先人光寵。至於變甫之奠大夫,秘忽於軍營,則忠;變甫事母,則極孝;變甫之妹列節於其夫,則節烈;變甫之太夫人,則巾幗丈夫,訓子有方,待人則義。語雲:「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余知乾坤無麽也。是為序。
詳細資料
- ISBN:7101018661
- 叢書系列: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 規格:384頁 / 20 x 14 cm / 普通級 / 初版
- 出版地:大陸
|
|
|
|
|
 | 作者:嚴柔拏 出版社: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12-28 66折: $ 251 |  | 作者:許添盛醫師主講 出版社:賽斯文化 出版日期:2019-05-06 66折: $ 660 |  | 作者:許添盛 出版社:賽斯文化 出版日期:2014-11-03 66折: $ 58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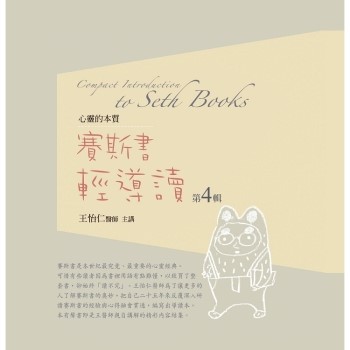 | 作者:王怡仁醫師主講 出版社:賽斯文化 出版日期:2019-07-01 66折: $ 871 | |
|
|
 | 作者:張忠謀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24-11-29 $ 869 |  | 作者:九井諒子 出版社: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1-22 $ 395 |  | 作者:史帝芬.維特 出版社: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1-20 $ 395 |  | 作者:盧勝彥 出版社:財團法人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出版日期:2025-01-20 $ 205 | |
|
|
 | 作者:甘詰留太 出版社:青文 出版日期:2025-01-20 $ 12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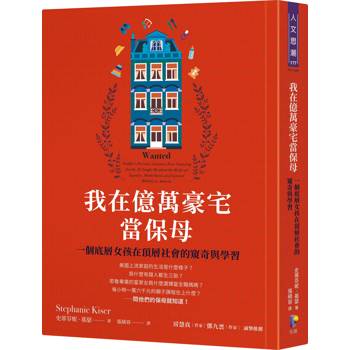 | 作者:史蒂芬妮‧基瑟(Stephanie Kiser) 出版社: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2-01 $ 308 |  | 作者:西成活裕 出版社: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01-21 $ 300 |  | $ 434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