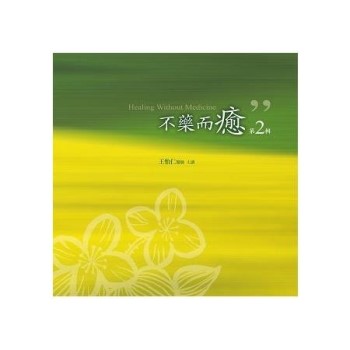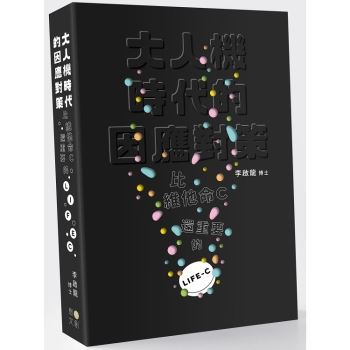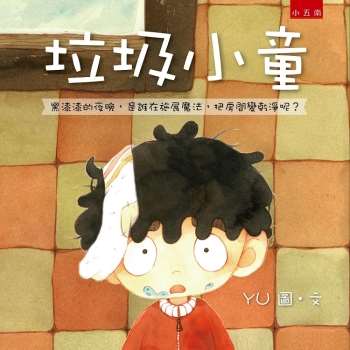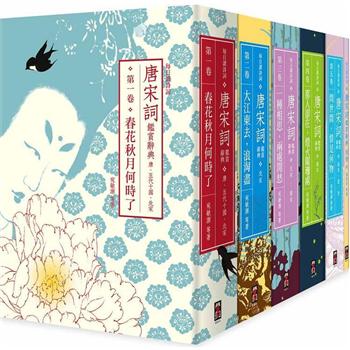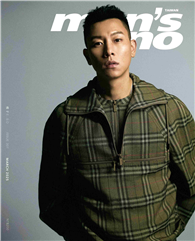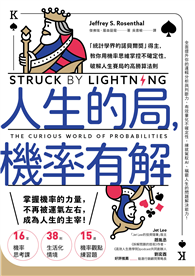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水經注校證(繁體版)的圖書 |
 |
水經注校證(繁體版) 作者:[北魏]酈道元 陳橋驛 校證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07-07-01 語言:簡體中文 規格:988頁 / 21 x 14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水經注校證(繁體版)
內容簡介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是我國古代的歷史地理名著,記載了一千多條水道及其所經地區的的自然地貌、人文遺跡、建置沿革和有關的歷史事件、神話傳說、人物典故、民俗物產等,引書400余種,記述眾多漢魏碑銘。作者以《四部叢刊》本為底本,參考35種版本,利用120大量地方志和其他文獻資料,融匯本人60余年研治體會,吸收王國維、胡適、岑仲勉、森鹿三等中外學術成果,對原書進行標點,撰作校證。各卷末的校證包括校異文、辨正誤、補異文、考原委等。
目錄
代序 我校勘水經注的經歷
整理說明
校上案語
水經注原序
卷一
河水
卷二
河水
卷三
河水
卷四
河水
卷五
河水
卷六
汾水 澮�#65533;文水 原公水 過水 晉水 湛水
卷七
濟水
卷八
濟水
卷九
清水 沁水 淇水 盪水 洹水
卷十
? 乃清漳水
卷十一
易水 滱水
卷十二
聖水 巨馬水
卷十三
灅水
卷十四
濕餘水 沽河 鮑丘水 濡水 大潦水 小潦水 �
卷十五
洛水 伊水 瀍水 澗水
卷十六
水 甘水 漆水 滻水 沮水
卷十七
渭水
卷十八
渭水
卷十九
渭水
卷二十
漾水 丹水
┅┅
整理說明
校上案語
水經注原序
卷一
河水
卷二
河水
卷三
河水
卷四
河水
卷五
河水
卷六
汾水 澮�#65533;文水 原公水 過水 晉水 湛水
卷七
濟水
卷八
濟水
卷九
清水 沁水 淇水 盪水 洹水
卷十
? 乃清漳水
卷十一
易水 滱水
卷十二
聖水 巨馬水
卷十三
灅水
卷十四
濕餘水 沽河 鮑丘水 濡水 大潦水 小潦水 �
卷十五
洛水 伊水 瀍水 澗水
卷十六
水 甘水 漆水 滻水 沮水
卷十七
渭水
卷十八
渭水
卷十九
渭水
卷二十
漾水 丹水
┅┅
序
我撰寫我讀水經注的經歷一文,迄今已達二十五年。中國的古籍浩如瀚海,據韓長耕教授的統計:「中國古代文獻包括現存的和有目無書即散佚的,大概不下十五萬種,而其中尚存世流傳可供披覽檢證的,也仍在十二萬種以上。」一部水經注在中國古籍中無非是滄海一粟。而且像我這輩年紀的讀書人,哪有不讀古書的,如我在拙著酈翠札記卷首自序中所說:「我是從童年時代就開始誦讀水經注的,其事屬於一種偶然的機遇,後來逐漸成為一種愛好,對於歷代以來的許多知識分子,這是一種極為普通的事。」為什麽當年競要對此區區一書小題大作,撰寫一篇經歷,而發表以後又為不少書刊所轉載,所以必須說明幾句。
那是一九七七年歲尾,由於政治氣氛的稍有松動,竺可楨先生主編的中國自然地理中的歷史自然地理分冊,經過多年的擱置而又開始啟動,如我在上述札記自序昕寫:
十幾位學者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集中了近兩個月,我與我尊敬的譚其驤先生隔室而居,朝夕過從,所以對他在災難年頭所受的折磨,當時已經洞悉。而在這項工作的後一階段,我所尊敬的另一位前輩侯仁之先生為了商討發展歷史地理學的問題從北京來到上海,這是我們經過這場生死大難以後的第一次見面,在「乍見反疑夢,相悲各問災(原詩作『年』的心情下,不免要互說這些年代的遭遇。我向他訴說了我因讀酈而遭受的坎坷以及在「牛棚」中繼續冒險讀此書的事,他不僅敦促我把此事經過寫出來,而且還透露了我的這番經歷,以致書林主編金永華先生不久專程到杭州求索此稿。我痛定思痛,寫了這篇短文。好在此文如上所述已在多處轉載,並且流傳到了國外,所以不必贅述。
原來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我們曾經經歷過一個「讀書有罪」,「讀書人有罪」的時代,我在拙撰記一本好書的出版文中提及:「像我這一輩年紀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無端被剝奪了二十多年工作時間的。:逼不僅是像我這類的普通讀書人,高層次的讀書人也是一樣。中華讀書報記者曾經訪問過著名生物翠家鄒承魯院士:「您當年回國是否後悔?」鄒先生回答:「我回國已經有半個世紀了,其中最初的二十六年時間中做了十年的工作,而如果不回來可以連續做二十六年,我是對這一點後悔。」記者隨即插入了重要的一句:「而且當年正是壯年的時候。」
┅┅
那是一九七七年歲尾,由於政治氣氛的稍有松動,竺可楨先生主編的中國自然地理中的歷史自然地理分冊,經過多年的擱置而又開始啟動,如我在上述札記自序昕寫:
十幾位學者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集中了近兩個月,我與我尊敬的譚其驤先生隔室而居,朝夕過從,所以對他在災難年頭所受的折磨,當時已經洞悉。而在這項工作的後一階段,我所尊敬的另一位前輩侯仁之先生為了商討發展歷史地理學的問題從北京來到上海,這是我們經過這場生死大難以後的第一次見面,在「乍見反疑夢,相悲各問災(原詩作『年』的心情下,不免要互說這些年代的遭遇。我向他訴說了我因讀酈而遭受的坎坷以及在「牛棚」中繼續冒險讀此書的事,他不僅敦促我把此事經過寫出來,而且還透露了我的這番經歷,以致書林主編金永華先生不久專程到杭州求索此稿。我痛定思痛,寫了這篇短文。好在此文如上所述已在多處轉載,並且流傳到了國外,所以不必贅述。
原來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我們曾經經歷過一個「讀書有罪」,「讀書人有罪」的時代,我在拙撰記一本好書的出版文中提及:「像我這一輩年紀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無端被剝奪了二十多年工作時間的。:逼不僅是像我這類的普通讀書人,高層次的讀書人也是一樣。中華讀書報記者曾經訪問過著名生物翠家鄒承魯院士:「您當年回國是否後悔?」鄒先生回答:「我回國已經有半個世紀了,其中最初的二十六年時間中做了十年的工作,而如果不回來可以連續做二十六年,我是對這一點後悔。」記者隨即插入了重要的一句:「而且當年正是壯年的時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