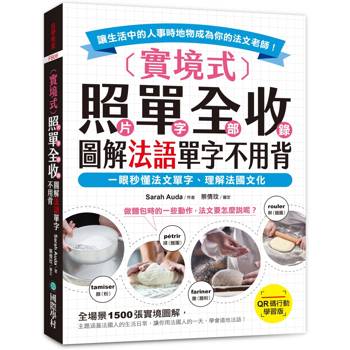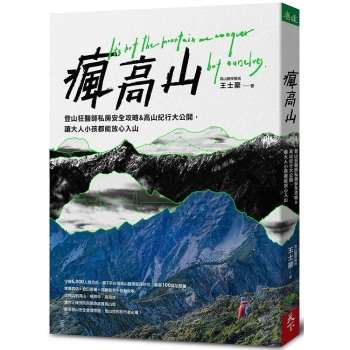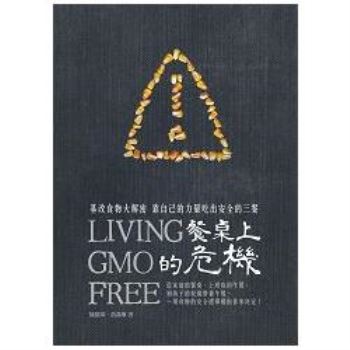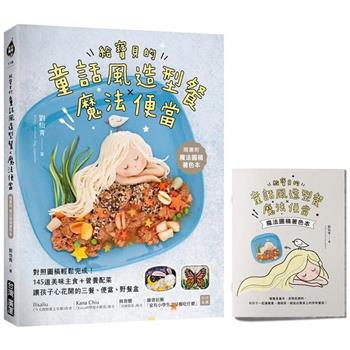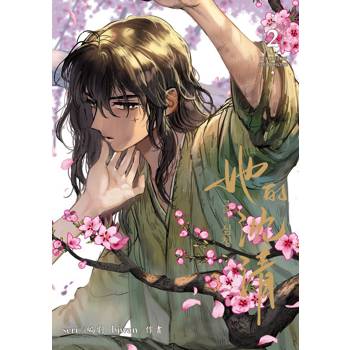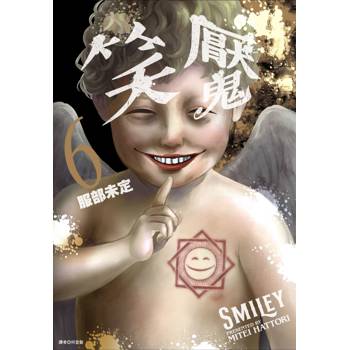譯者序
大多數人主要知道一個文化、一個環境、一個家,流亡者至少知道兩個;這個多重視野產生一種覺知:覺知同時並存的面向,而這種覺知——借用音樂的術語來說——是對位的(contrapuntal)。……流亡是過著習以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遊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對位的;但每當一習慣了這種生活,它撼動的力量就再度爆發出來。
——薩義德,《寒冬心靈》(The Mind of Winter,1984,p.55)
批評必須把自己設想成為了提升生命,本質上反對二切形式的暴政、宰製、虐待;批評的社會目標是為了促進人類 自由而產生的非強制性的知識。
——薩義德,《世界·文本·批評家》(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1983,p.29)
薩義德1935年11月1日出生於耶路撒冷,在英國佔領期間就讀巴勒斯坦和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接受英國式教育,1950年代赴美國就讀一流學府,獲普林斯頓大學學士(1957年),哈佛大學碩土(1960年)、博土(1964年),1963年起任教哥倫比亞大學迄今,講授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
薩義德著作等身,為當今聞名國際的文學學者暨文化批評家,並以知識分子的身份投入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其學術表現和政治參與都很引人矚目,如著名的非裔美國哲學家魏思特(Cornel West)在本書平裝本的封底推薦詞中稱頌薩義德為“當今美國最傑出的文化批評家;,但也由於熱切關懷、積極參與巴勒斯坦的政治,以致和喬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美國語言學家)一樣,成為美國最具爭議性的學院人士。他在許多場合提到1967年的中東戰爭是其人生的轉捩點:之前,學術與政治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之後,二者合而為一。這點在本書所附的訪談錄中也有明確表示。
在《認同·權威·自由:君主與旅人》(Identity,Authority and Freedom:The Potentate and the Traveller,1991)中薩義德進一步提到自己的三重身份:“我是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個美國人,這所賦予我的雙重角度即使稱不上詭異,但至產是古怪的。此外,我當然是個學院人士。這些身份中沒有一個是隔絕的;每一個身份都影響、作用於其他身份。……因此,我必須協調暗含于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種張力和矛盾。”(12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身份似同的設定並不是為了排除“異己”(“異”與自“己”的他者),而是為了更寬廣的人道關懷,正如他在另一篇訪談錄中所說的:“一方面你爭取代表自己的權利,要有自己的民族性;但另一方面,除非這些是連接上更寬廣的實踐(也就是我所謂的解放),否則我是完全反對的。”[《美國知識分子與中東政治:薩義德訪談錄》(“American Intellectuals and Middle East Politics:An Interview with Edward W.Said”),1988,p.52.]
薩義德的學術及個人生涯頗具特色。他是早期少數認識到歐陸理論的重要並率先引入美國學界的文學及文化學者。他所引介的包括現象學、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以及後殖民論述等等,也曾專文討論過包括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法國歷史學家)在內的理論家與批評家,更把這些理論與批評融入並落實于特定作家、作品及專題的研究,而不局限于嚴格定義下的文學。因此,在從事人文學科的科際整合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在文學與文化研究上的突出表現,和結合文學/文化理論及文本分析的批評理念與策略密切相關。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薩義德作品系列:知識份子論的圖書 |
 |
薩義德作品系列:知識份子論 作者:愛德華.W.薩義德 / 譯者:單德興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 出版日期:2007-06-01 語言:簡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58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薩義德作品系列:知識份子論
本書為薩義德總結近年文學、文化、政治批評的經驗,對“知識分子”這一重要議題所作的系列反思。他尖銳地指出,在當今媒體發達、政治與學術利益交融的時代,所謂的知識分子已經是一種特殊專業,集編輯、記者、政客及學術中間人於一身。他(她)們身不由己,往往成為各種權力結構中的一員。反而在去國離鄉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異端的“業餘者”、“圈外人”中,我們方能得見知識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風骨典型。
作者簡介:
薩義德(1935-2003)出生於耶路撒冷,早年接受的是英國教育,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赴美,先後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1963年起即在哥倫比亞大學講授英美文學和比較文學,直到去世。他是當今學界的重量級人物,出書二十多本,以《東方學:西方對於東方的觀念》聞名於世,為後殖民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批評開通了道路。他是學者,又是鬥士,一生都在向他認為的一切"暴行"和不公正挑戰,不管這種暴行和不公正是來自美國政府還是中東的原教旨主義。
章節試閱
譯者序
大多數人主要知道一個文化、一個環境、一個家,流亡者至少知道兩個;這個多重視野產生一種覺知:覺知同時並存的面向,而這種覺知——借用音樂的術語來說——是對位的(contrapuntal)。……流亡是過著習以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遊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對位的;但每當一習慣了這種生活,它撼動的力量就再度爆發出來。
——薩義德,《寒冬心靈》(The Mind of Winter,1984,p.55)
批評必須把自己設想成為了提升生命,本質上反對二切形式的暴政、宰製、虐待;批評的社會目標是為了促...
大多數人主要知道一個文化、一個環境、一個家,流亡者至少知道兩個;這個多重視野產生一種覺知:覺知同時並存的面向,而這種覺知——借用音樂的術語來說——是對位的(contrapuntal)。……流亡是過著習以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遊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對位的;但每當一習慣了這種生活,它撼動的力量就再度爆發出來。
——薩義德,《寒冬心靈》(The Mind of Winter,1984,p.55)
批評必須把自己設想成為了提升生命,本質上反對二切形式的暴政、宰製、虐待;批評的社會目標是為了促...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譯者序
序言
第一章知識分子的代表
第二章為民族與傳統設限
第三章知識分子的流亡——放逐者與邊緣人
第四章專業人士與業餘者
第五章對權勢說真話
第六章總是失敗的精神
附錄一論知識分子——薩義德訪談錄
附錄二擴展人文主義——薩義德訪談錄
附錄三薩義德專著書目提要
索引
後記
序言
第一章知識分子的代表
第二章為民族與傳統設限
第三章知識分子的流亡——放逐者與邊緣人
第四章專業人士與業餘者
第五章對權勢說真話
第六章總是失敗的精神
附錄一論知識分子——薩義德訪談錄
附錄二擴展人文主義——薩義德訪談錄
附錄三薩義德專著書目提要
索引
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