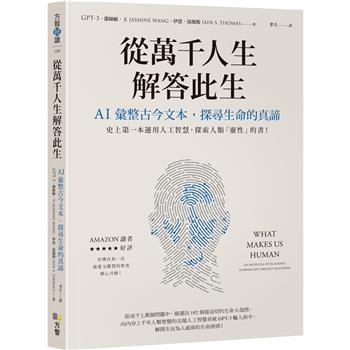在本書中,阿倫特力圖表明「積極生活」的三種活動——勞動、工作和行動——的區分是基於人的條件而做出的,她理解的人的「條件」,既不是所謂人的本質屬性,也不是康德意義上規定人類經驗方式的超驗條件,而是人在地球上被給定的那些生存條件:勞動的條件是人們必需維生,工作的條件是人們必需建造一個人造物的世界,行動的條件是人們必需在交往中彰顯自己,回答「我是誰」的問題。離開了這些條件,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了。在此意義上,人是被條件規定了的存在(conditioned beings)。但他們的活動又創造着自己下一步生存的條件,比如勞動超出家庭和國家界限的全球化發展,和人從宇宙的角度對地球采取行動,都根本上改變了人類未來的生存處境。
本書在結構上另一個值得關注之處是「積極生活」(vita activa)與「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二元對照。第1章給出的兩種生活的對照,為全書確立了一個隱含的背景框架。實際上,只有在此二元對照下,勞動、工作和行動才可能有效地保持自身,因為與兩種生活方式相應的,是古代西方對兩個世界的想象:柏拉圖的現象世界和理念世界,或基督教的塵世之城和天上之城,前者是變化的、有死滅的,后者是永恆不變的。在那里,制作或工作被當成一切活動的原型,人在制作中模仿神聖世界的創造,現實生活的真實性和榮耀都來自后者,后者才是他終極渴望回歸之所。阿倫特認為這種沉思生活高於積極生活的等級秩序,在傳統政治思想中導致了對政治的傷害,因為政治哲學家傾向於以制作模式把行動理解為按照某種真理來統治。但對立之消隱的災難后果,要在世俗化的現代才清晰地浮現出來。在神聖世界不再被信仰,沉思「被逐出有意義的人類能力行列」之后,制作活動也失去了衡量他的產品真實性的標准,作為人造物的世界越來越相對化,喪失了它得以立足的持久性和穩固性。二元世界觀的消失,一方面讓現代人喪失了作為生存條件的「世界」,另一方面人被拋回到自身,返回到孤獨內心來尋求真實性和確定性的基礎。「世界異化」和「向自身的回返」最終以犧牲世界和犧牲行動為代價。雖然在現代早期,人作為制造者獲得過短暫的勝利,那時人曾被高舉為目的,但「由於現代的世界異化和內省被提升為一種征服自然的無所不能的策略,也就沒有哪種能力像制作——主要是建造世界和生產世界之物的能力——一樣,喪失得如此之多」(本書第242頁)。在最后一章,阿倫特哀悼了技藝人(homo faber)的失落:匠人精神始終預設了一個物的世界,在那里,物質閃耀、語詞可聽,但在世界塌陷,甚至被還原為生物循環意義上的自然的情況下,zui終是勞動動物(animal laborans)取得了全面勝利,而這就是我們已生活於其中的世界。
漢娜?阿倫特(1906—1975),德裔美籍猶太人,生於德國漢諾威。曾師從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在海德堡大學獲博士學位。1933年因納粹上台而流亡海外,於1951年獲美國國籍。自1954年開始,阿倫特先后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布魯克林學院開辦講座;她還擔任過芝加哥大學教授、社會研究新學院教授。阿倫特以《極權主義的起源》、《在過去和未來之間》、《論革命》及《人的境況》等著作,為當代政治哲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成為20世紀最具原創性和影響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