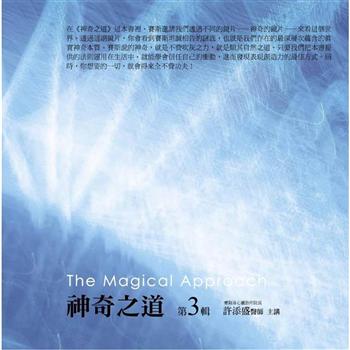《學術與政治》是馬克斯·韋伯的兩個演講名篇。一戰後,慕尼克大學的學生對未來的道路充滿了迷惘。應其之邀,韋伯做了這兩次演講,旨在為大學生解答學術與人生道路上的核心問題。在一個祛魅的時代,以學術或政治為天職,這意味著什麼?學術生活就如一場“瘋狂的賭博”,而政治則被韋伯喻為“堅定而從容地鑽透硬木板”。
他以冷峻、清醒與獨有的內心深處的激情,直面我們時代最深刻的命運,為我們描繪出學術與政治的職業狀況,闡明從事這兩種職業所需的素質與條件,揭示學者與職業政治家的責任與內在使命。《學術與政治》可看作韋伯晚年對畢生致力的兩大領域的反思,這兩篇演講在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也成為韋伯最重要的兩篇演講。本書同時收錄韋伯的方法論名篇“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此篇貫通學術與政治這兩大領域,闡釋了兩個領域之間的內在關係。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學術與政治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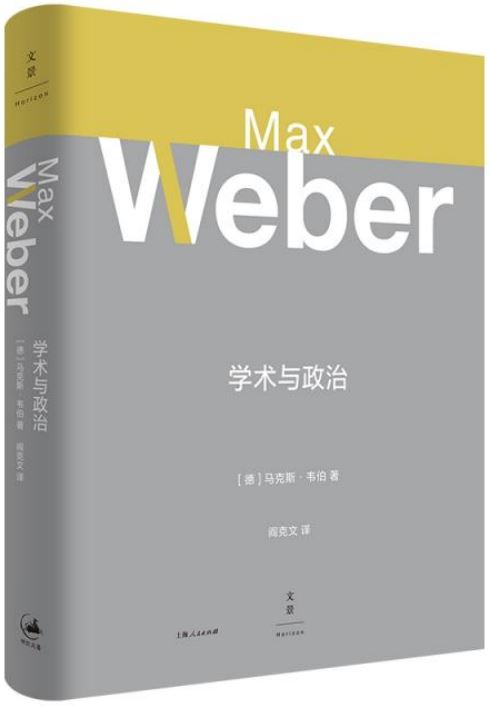 |
學術與政治 作者:(德)馬克斯·韋伯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08-01 語言:簡體中文 規格:精裝 / 257頁 / 32k/ 13 x 19 x 1.28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學術與政治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現代最具影響力和生命力的思想家,社會學三大“奠基人”之一。曾先後在柏林大學、維也納大學、慕尼克大學任教。他對於當時德國的政界影響極大,曾前往凡爾賽會議代表德國進行談判,並且參與了魏瑪共和國的起草設計。主要著作包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印度的宗教》《古猶太教》,以及未完成遺稿《經濟、諸社會領域及權力》等。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現代最具影響力和生命力的思想家,社會學三大“奠基人”之一。曾先後在柏林大學、維也納大學、慕尼克大學任教。他對於當時德國的政界影響極大,曾前往凡爾賽會議代表德國進行談判,並且參與了魏瑪共和國的起草設計。主要著作包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印度的宗教》《古猶太教》,以及未完成遺稿《經濟、諸社會領域及權力》等。
序
譯者前言
這兩篇傳世文獻早已為中文讀者普遍熟知,影響所及,大概已經難以估量,1998年的三聯版譯本及後來的若干不同譯本印行,對於推動這個文本的廣泛傳播,無疑各有功德。
不過,完全客觀地說,通過翻譯再現經典原著的本色,或許是沒有止境的。主要是基於這個原因,筆者最終認為,雖然多年前曾根據英譯本翻譯過這兩個文本,還是有必要重新理解一番德文原著,並盡可能忠實地用中文還原出來。將近三年前,根據1921年在慕尼克出版的《政治論文集》(Gesammelte Politiche Schriften)和1922年在蒂賓根出版的《學術理論文集》(Gesammelte Aufsae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筆者開始斷斷續續但始終小心翼翼地雕琢譯文,直到近自以為可以定稿了,這才如釋重負。同時,筆者真誠感到有義務必須提前表達的是,由衷感謝筆者十分敬重的羅衛東先生的慷慨勉勵、浙大高研院提供的工作條件和世紀出版集團·文景諸賢一向出眾的專業精神。
韋伯是根據自己的詳細大綱發表了這兩篇即席演講的,不久又親自對演講記錄稿做了修訂,然後正式發表,但基本上保留了口語化的風格,因此,從字面上和話語模式上看,文本本身並不深奧,更不晦澀,甚至可以說非常平易近人。但是,如果不得不先用一個樸素而又簡潔的說法突出這兩篇文獻的罕見價值,筆者認為,最貼切的應該就是,言近旨遠。
我們不妨從標題本身的技術問題談起。
首先是以學術為天職,Wissenschaft als Beruf,這裡所說的學術,Wissenschaft,大不同于英文和中文,它同時還有“科學”這個詞義,而且德語中沒有其他專用或通用單詞,可以分別替代Wissenschaft來指稱學術與科學這兩個特定術語。但作為語言調度大師的韋伯,根據語境,除了特意做出區分時會使用限制性組合詞,比如更早的時候泛指的Kulturwissenschaft(文化科學),本書中特指的Naturwissenschaft(自然科學)與Sozialwissenschaft(社會科學),一般情況下就只用Wissenschaft,有時是兼指學術與科學,有時則是僅指學術或科學,其所指和能指,對他來說似是“毋庸贅言”,對於德語聽眾或讀者來說大概也算不上費解。不過,這對中文譯者來說,就不是個無足輕重的考驗了,因為涉及理解韋伯的深層用意而不是單純的字面含義,必須仔細斟酌,在不同的上下文關係中使用不同的譯法,或者“學術”,或者“科學”。以政治為天職,Politik als Beruf 中的Politik也是如此,在德文中同樣是一詞兩義,既是政治,又是政策,沒有專用或特指的替代詞,但相比而言,卻沒有Wissenschaft那麼不易把握。以上兩種情況已分別體現在譯文中,還請方家明察。
其次,Beruf也是個使筆者感到很棘手的用詞。韋伯在早先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已經指出,馬丁·路德把拉丁文《聖經》翻譯成德文時特別使用了Beruf一詞,以表示這是“奉上帝的召喚”而理性從事的任何正當職業勞動,無論是體力還是腦力勞動,從而賦予了一切正當職業勞動,尤其是經濟活動以“增加上帝的榮耀”這一神聖含義,借此對職業勞動,尤其是對勞動產生的財富重新進行了道德評價,這種內生的動力無時或已,在它驅策下的職業勞動,即為“天職”。儘管幾個世紀之後隨著的不斷世俗化,以及無情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制度動力逐漸取代了內在的精神動力,Beruf的含義越來越成為一般世俗意義上的“職業”,但它內在的詞源性基因依然如故,韋伯就是在這個歷時(Diachronic)背景下使用該詞的,其內在與外在含義、神聖與世俗含義、特指與泛指含義,交融彌散於兩篇演講始終,對譯者遣詞造句也是不可等閒視之的考驗,如今已是白紙黑字,只有靜待讀者諸君指謬了。
由此來看,這個措辭上的技術問題,實質上也同時預示了,韋伯即將觸及一個對所有現代人,尤其是對現代學術人和政治人都至關重要的根本問題:如何面對可能會無休止的“意義”困境。
這裡有個宏觀背景,就是說,在這個看似無休止“進步”的現代性過程中,由於每個人乃至整個人類的任何“進步”都不可能抵達這個過程的性,一代接一代人的生與死,也就沒有性意義了。因此,一個人如果打算投身於註定了沒有止境也絕無可能有止境的學術與政治,還會認為這是在從事一項有意義的事業嗎?
這樣的追問似乎是暗示了一個極為沉重的問題:我們可能正在走向虛無。但既然還要活下去,韋伯給出的回答是,我們必須為自己的生命選擇某種立場,也就是對自身存在的意義作出說明,“單靠祈望和等待,只能一事無成,我們應當採取不同的行動:去做我們的工作以滿足“當下的要求”——不管那是為人處世還是履行我們的天職,都應如此。”
這種“不同的行動”,在韋伯那裡就體現為他的學術與政治關懷,而且至死方休,當然,精神意義上的韋伯仍然活著,人們至今仍在從這兩篇文獻中尋找行動指南,就可以作證。
毋庸贅言,韋伯這裡是提出了兩種角色期待,即對學術人和政治人的角色期待,也就是說,面對內在和外在的雙重約束條件,如何去承擔自己選擇的個人使命,以使自身的存在多多少少都有些意義。顯然,這根本不是個輕而易舉就能得出基本答案的問題,何況還有更重要的:答案之後的行動問題。
針對那個大動盪、大災變、大轉折時代造成的當下現實和未來前景的巨大不確定性,韋伯以極為罕見的冷峻、審慎和深邃的目光,注視著這個已經祛魅的價值多元化世界,並希望引導他的聽眾和讀者漸入“頭腦清明”的境界,認清現實的特徵和自身的處境,力求懷著客觀性的現實感去追尋有限但真實的希望,這才有可能抵達我們自身存在的確定性和價值,而這就意味著,不得不正視現代性條件下的存在意義問題,已經不是僅僅局限於韋伯那個時代的人們,只要現代性過程尚未宣告結束,這就是所有現代人都必須正視的嚴酷命運,至少現在來看,還遠不是“後現代”之類玄虛曖昧的概念遊戲能應付過去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今天仍在不斷重溫《學術與政治》,聽到的就不是遙遠的一百多年前在遙遠的德國這兩次演講的微弱回聲,它們仍是隨時能夠擊穿學術與政治混沌的電閃雷鳴。
這兩個領域,無論是在韋伯本人的畢生事業中,還是就其對經驗世界的認識價值而言,毫無疑問都有著不可消解的內在聯繫。但是不難發現,韋伯並沒有在這兩個場合對這種內在聯繫予以明確闡釋。筆者認為,承載了貫通作用的是另一份重要文獻,《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Die “Objek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在這裡,我們可以明確無誤地看到,韋伯充分揭示了,對經驗世界的主觀性認識,總是以極為多樣的價值立場為前提,而對經驗世界的客觀性認識,卻理應恪守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倫理要求-道德律令,兩者之間一直並將繼續存在著往往令人絕望的緊張關係,從而對健全的判斷力和負責任的行動構成了嚴峻挑戰,這意味著,無論在學術還是政治領域,未來很可能並不總是美好的,更重要的是,現代學術人和政治人還有潛力擺脫這種不祥的命運嗎?為了回答這樣的問題,韋伯等於是精心打造了一個非常複雜而又井井有條的思想訓練技術程式,從本質上說,這樣的思想訓練足以為“信念倫理”套上責任韁繩,為“責任倫理”澄清信念迷霧。基於這個認識,筆者認為十分有必要把這篇文獻附在《學術與政治》之後,因而根據1904年4月發表在《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獻》上的文本譯出了全文,以便更集中更充分地展示韋伯對這幾個問題的非凡洞察與思考,祈讀者諸君明鑒。
經驗世界是個無盡的意義之鏈,不管遙遠未來的意義何在,畢竟需要從當下做起。韋伯不厭其煩鞭辟入裡告訴我們的就是,怎麼做。
謹以這個譯本紀念馬克斯·韋伯逝世一百周年。
閻克文
2020年6月14日
這兩篇傳世文獻早已為中文讀者普遍熟知,影響所及,大概已經難以估量,1998年的三聯版譯本及後來的若干不同譯本印行,對於推動這個文本的廣泛傳播,無疑各有功德。
不過,完全客觀地說,通過翻譯再現經典原著的本色,或許是沒有止境的。主要是基於這個原因,筆者最終認為,雖然多年前曾根據英譯本翻譯過這兩個文本,還是有必要重新理解一番德文原著,並盡可能忠實地用中文還原出來。將近三年前,根據1921年在慕尼克出版的《政治論文集》(Gesammelte Politiche Schriften)和1922年在蒂賓根出版的《學術理論文集》(Gesammelte Aufsae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筆者開始斷斷續續但始終小心翼翼地雕琢譯文,直到近自以為可以定稿了,這才如釋重負。同時,筆者真誠感到有義務必須提前表達的是,由衷感謝筆者十分敬重的羅衛東先生的慷慨勉勵、浙大高研院提供的工作條件和世紀出版集團·文景諸賢一向出眾的專業精神。
韋伯是根據自己的詳細大綱發表了這兩篇即席演講的,不久又親自對演講記錄稿做了修訂,然後正式發表,但基本上保留了口語化的風格,因此,從字面上和話語模式上看,文本本身並不深奧,更不晦澀,甚至可以說非常平易近人。但是,如果不得不先用一個樸素而又簡潔的說法突出這兩篇文獻的罕見價值,筆者認為,最貼切的應該就是,言近旨遠。
我們不妨從標題本身的技術問題談起。
首先是以學術為天職,Wissenschaft als Beruf,這裡所說的學術,Wissenschaft,大不同于英文和中文,它同時還有“科學”這個詞義,而且德語中沒有其他專用或通用單詞,可以分別替代Wissenschaft來指稱學術與科學這兩個特定術語。但作為語言調度大師的韋伯,根據語境,除了特意做出區分時會使用限制性組合詞,比如更早的時候泛指的Kulturwissenschaft(文化科學),本書中特指的Naturwissenschaft(自然科學)與Sozialwissenschaft(社會科學),一般情況下就只用Wissenschaft,有時是兼指學術與科學,有時則是僅指學術或科學,其所指和能指,對他來說似是“毋庸贅言”,對於德語聽眾或讀者來說大概也算不上費解。不過,這對中文譯者來說,就不是個無足輕重的考驗了,因為涉及理解韋伯的深層用意而不是單純的字面含義,必須仔細斟酌,在不同的上下文關係中使用不同的譯法,或者“學術”,或者“科學”。以政治為天職,Politik als Beruf 中的Politik也是如此,在德文中同樣是一詞兩義,既是政治,又是政策,沒有專用或特指的替代詞,但相比而言,卻沒有Wissenschaft那麼不易把握。以上兩種情況已分別體現在譯文中,還請方家明察。
其次,Beruf也是個使筆者感到很棘手的用詞。韋伯在早先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已經指出,馬丁·路德把拉丁文《聖經》翻譯成德文時特別使用了Beruf一詞,以表示這是“奉上帝的召喚”而理性從事的任何正當職業勞動,無論是體力還是腦力勞動,從而賦予了一切正當職業勞動,尤其是經濟活動以“增加上帝的榮耀”這一神聖含義,借此對職業勞動,尤其是對勞動產生的財富重新進行了道德評價,這種內生的動力無時或已,在它驅策下的職業勞動,即為“天職”。儘管幾個世紀之後隨著的不斷世俗化,以及無情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制度動力逐漸取代了內在的精神動力,Beruf的含義越來越成為一般世俗意義上的“職業”,但它內在的詞源性基因依然如故,韋伯就是在這個歷時(Diachronic)背景下使用該詞的,其內在與外在含義、神聖與世俗含義、特指與泛指含義,交融彌散於兩篇演講始終,對譯者遣詞造句也是不可等閒視之的考驗,如今已是白紙黑字,只有靜待讀者諸君指謬了。
由此來看,這個措辭上的技術問題,實質上也同時預示了,韋伯即將觸及一個對所有現代人,尤其是對現代學術人和政治人都至關重要的根本問題:如何面對可能會無休止的“意義”困境。
這裡有個宏觀背景,就是說,在這個看似無休止“進步”的現代性過程中,由於每個人乃至整個人類的任何“進步”都不可能抵達這個過程的性,一代接一代人的生與死,也就沒有性意義了。因此,一個人如果打算投身於註定了沒有止境也絕無可能有止境的學術與政治,還會認為這是在從事一項有意義的事業嗎?
這樣的追問似乎是暗示了一個極為沉重的問題:我們可能正在走向虛無。但既然還要活下去,韋伯給出的回答是,我們必須為自己的生命選擇某種立場,也就是對自身存在的意義作出說明,“單靠祈望和等待,只能一事無成,我們應當採取不同的行動:去做我們的工作以滿足“當下的要求”——不管那是為人處世還是履行我們的天職,都應如此。”
這種“不同的行動”,在韋伯那裡就體現為他的學術與政治關懷,而且至死方休,當然,精神意義上的韋伯仍然活著,人們至今仍在從這兩篇文獻中尋找行動指南,就可以作證。
毋庸贅言,韋伯這裡是提出了兩種角色期待,即對學術人和政治人的角色期待,也就是說,面對內在和外在的雙重約束條件,如何去承擔自己選擇的個人使命,以使自身的存在多多少少都有些意義。顯然,這根本不是個輕而易舉就能得出基本答案的問題,何況還有更重要的:答案之後的行動問題。
針對那個大動盪、大災變、大轉折時代造成的當下現實和未來前景的巨大不確定性,韋伯以極為罕見的冷峻、審慎和深邃的目光,注視著這個已經祛魅的價值多元化世界,並希望引導他的聽眾和讀者漸入“頭腦清明”的境界,認清現實的特徵和自身的處境,力求懷著客觀性的現實感去追尋有限但真實的希望,這才有可能抵達我們自身存在的確定性和價值,而這就意味著,不得不正視現代性條件下的存在意義問題,已經不是僅僅局限於韋伯那個時代的人們,只要現代性過程尚未宣告結束,這就是所有現代人都必須正視的嚴酷命運,至少現在來看,還遠不是“後現代”之類玄虛曖昧的概念遊戲能應付過去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今天仍在不斷重溫《學術與政治》,聽到的就不是遙遠的一百多年前在遙遠的德國這兩次演講的微弱回聲,它們仍是隨時能夠擊穿學術與政治混沌的電閃雷鳴。
這兩個領域,無論是在韋伯本人的畢生事業中,還是就其對經驗世界的認識價值而言,毫無疑問都有著不可消解的內在聯繫。但是不難發現,韋伯並沒有在這兩個場合對這種內在聯繫予以明確闡釋。筆者認為,承載了貫通作用的是另一份重要文獻,《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Die “Objek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在這裡,我們可以明確無誤地看到,韋伯充分揭示了,對經驗世界的主觀性認識,總是以極為多樣的價值立場為前提,而對經驗世界的客觀性認識,卻理應恪守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倫理要求-道德律令,兩者之間一直並將繼續存在著往往令人絕望的緊張關係,從而對健全的判斷力和負責任的行動構成了嚴峻挑戰,這意味著,無論在學術還是政治領域,未來很可能並不總是美好的,更重要的是,現代學術人和政治人還有潛力擺脫這種不祥的命運嗎?為了回答這樣的問題,韋伯等於是精心打造了一個非常複雜而又井井有條的思想訓練技術程式,從本質上說,這樣的思想訓練足以為“信念倫理”套上責任韁繩,為“責任倫理”澄清信念迷霧。基於這個認識,筆者認為十分有必要把這篇文獻附在《學術與政治》之後,因而根據1904年4月發表在《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獻》上的文本譯出了全文,以便更集中更充分地展示韋伯對這幾個問題的非凡洞察與思考,祈讀者諸君明鑒。
經驗世界是個無盡的意義之鏈,不管遙遠未來的意義何在,畢竟需要從當下做起。韋伯不厭其煩鞭辟入裡告訴我們的就是,怎麼做。
謹以這個譯本紀念馬克斯·韋伯逝世一百周年。
閻克文
2020年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