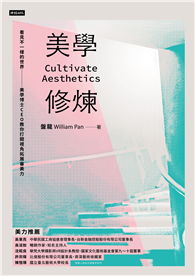巴爾幹半島為什麼會被稱為「歐洲火藥桶」?為什麼這個地區會成為歐洲動蕩的地方?著名地緣學家在遊歷巴爾幹諸國的深沉旅行中,回顧了巴爾幹地區的漫長歷史,以深刻的洞察力、以冷靜犀利的紀實筆觸,呈現了這一地區複雜的歷史變遷和民族關係以及背後大國勢力的競相角力,從奧斯曼征服到科索沃戰爭,巴爾幹一直扮演著歐亞政治版圖變化的重要力量。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巴爾幹兩千年的圖書 |
 |
巴爾幹兩千年 作者:(美)羅伯特·D.卡普蘭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0-01 語言:簡體中文 規格:精裝 / 368頁 / 16k/ 19 x 26 x 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1-1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巴爾幹兩千年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羅伯特·卡普蘭美國著名智庫Stratfor公司的首席地緣政治分析家。1952年生於紐約,長期為《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新共和》《華爾街日報》《國際利益》等頂尖媒體撰寫評論,出版的著作有《阿拉伯人》《地球末日》《帝國的野蠻》《地中海之冬》《季風帝國》《地理的復仇》《在歐洲的陰影下》《南海困局》等。
目錄
序曲:聖徒、恐怖分子、鮮血與聖水
第一部分
南斯拉夫:歷史的前奏曲
第1章 克羅地亞:“於是他們就可以去天堂”
第2章 舊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巴爾幹“西岸”
第3章 馬其頓:渴望摘星的手
第4章 白色的城市及其預言家
第二部分:羅馬尼亞:拉丁人激情的釋放
第5章 布加勒斯特雅典娜宮酒店
第6章 多瑙河的煩惱之角
第7章 摩爾達維亞:習慣於仇恨
第8章:德拉庫拉的城堡那邊的土地:布科維納有壁畫的修道院
第9章 特蘭西瓦尼亞的聲音
第10章 特蘭西瓦尼亞的故事: 花衣吹笛人的孩子回到了哈梅林
第11章 最後的一瞥:蒂米什瓦拉和布加勒斯特
第三部分:保加利亞:來自共產主義的拜占庭的故事
第12章 他人身體的溫暖
第13章 友誼的代價
第14章 惡與善
第四部分:希臘:西方新娘,東方新郎
第15章 告別薩洛尼卡
第16章“佐巴,教教我。教我跳舞吧!”
第17章 秘史
尾聲:通往阿德里安堡之路
第一部分
南斯拉夫:歷史的前奏曲
第1章 克羅地亞:“於是他們就可以去天堂”
第2章 舊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巴爾幹“西岸”
第3章 馬其頓:渴望摘星的手
第4章 白色的城市及其預言家
第二部分:羅馬尼亞:拉丁人激情的釋放
第5章 布加勒斯特雅典娜宮酒店
第6章 多瑙河的煩惱之角
第7章 摩爾達維亞:習慣於仇恨
第8章:德拉庫拉的城堡那邊的土地:布科維納有壁畫的修道院
第9章 特蘭西瓦尼亞的聲音
第10章 特蘭西瓦尼亞的故事: 花衣吹笛人的孩子回到了哈梅林
第11章 最後的一瞥:蒂米什瓦拉和布加勒斯特
第三部分:保加利亞:來自共產主義的拜占庭的故事
第12章 他人身體的溫暖
第13章 友誼的代價
第14章 惡與善
第四部分:希臘:西方新娘,東方新郎
第15章 告別薩洛尼卡
第16章“佐巴,教教我。教我跳舞吧!”
第17章 秘史
尾聲:通往阿德里安堡之路
序
聖徒、恐怖分子、鮮血與聖水
我渾身顫抖,手腳也有些忙亂。我故意選擇在這個令人毛骨悚然、黎明前的時刻造訪“舊塞爾維亞”遺留下來的皮克修道院。在東正教裡,精神指導要求人們進行辛勤的勞作,不過作為獎賞,會向他們曉諭有關地獄和救贖的資訊,但這同樣需要人們苦行力修方能得到。西方的入侵者如果不肯用他的整個存在來感知的話,他就不要指望自己能夠理解這一切。
置身于西元1250年繪成的使徒教堂內,我的雙眼一時不能適應,什麼也看不見。不過短短幾分鐘,可感覺非常漫長,像是從未間斷的幾百年,讓人充滿了挫敗感。我沒帶手電筒,也沒帶蠟燭。但是,當你什麼都看不見的時候,你的意志卻更加集中。
彼達·彼得洛維奇·尼格斯在《高山花環》這部用塞爾維亞語寫成的最偉大的詩篇中說,“眼睛並不妨礙視而不見的人;他穩穩當 當地……走在同一條路上,就像醉酒的人,始終扶著籬笆牆。”在這部著作中,對於改信伊斯蘭教的人們的大規模屠殺,被當作是為了打贏土耳其穆斯林1的戰鬥的必要手段。(xliii)就在黑暗即將減退的時刻,我瞬間明白了掙扎、絕望和仇恨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我的雙眼在黑暗中的摸索教給了國家生存的首要原則:哪怕是幾乎沒有任何光明,也可以創造出一個完整的世界。也就過了約莫一分鐘的時間,各種面孔就從幽暗中浮現出來:那一張張來自早熟的塞爾維亞的過去的面孔,愁容遍佈,飽經風霜,向人們展示出某種靈性和原始,西方人對此並不陌生,因為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身上已經得到了很好的體現。我感覺自己仿佛走進了一顆頭顱之內,看到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在燃燒。
夢想似乎是可以觸摸的了,如真如幻:穿著紫色袍子的聖尼古拉,在用他的黑色的、令人不敢直視的雙眼看著我的腦後;塞爾維亞的主保聖人、我所在的教堂的創立者聖薩瓦,從水一樣的真空中緩緩落下,慷慨地把仁慈和靈感送贈給我;升天的基督,雖是農夫出身的神,卻擺脫了身體煎熬的最後階段,已達到超凡脫俗的境界,比任何征服者或俗世的思想意識更令人畏懼。
使徒與聖徒和中世紀塞爾維亞的國王與主教混雜在一起。他們似乎都從信仰的變形鏡中走了出來:身軀被拖長,長著令人恐怖的手腳和頭。許多聖徒的眼睛已經被摳掉。根據某種農民的信仰,用來繪製聖徒眼睛的泥灰和染料,可以治好失明。
迷信,盲目崇拜?這是西方人的心靈在說話。用約瑟夫·康拉德的話來說,這樣的心靈“並不擁有一種得自於上古的、親身經歷的知識,因而就無從知曉歷史上的獨裁政體如何壓抑思想、捍衛權力和維持其存在。因而,”康拉德在《在西方的目光下》中認為,對於一個西方公民來說,“他怎麼也想不明白,遭受鞭撻竟然可以成為一種實際上的調查措施,或是一種懲罰。”
這所教堂提醒人們:黑暗越是深沉,反抗就越缺少理性,也就越令人恐怖。
根據艾瑞克·安布勒的《對戴爾徹甫的審判》,史達林大清洗的受害者之一、遭受監禁的戴爾徹甫夫人遺憾地表示:“在保加利亞和在希臘,在南斯拉夫,在所有曾受土耳其統治的歐洲國家,都是一模一樣的。”(xliv)“因此,躲避在牆壁後面的我們的人民,其實是生活在狹隘的虛幻的世界之中……他們用民族生活的畫面來裝點牆壁……既然我們又重新躲避到了牆壁後面,我們父輩的和我們童年時代的習慣也就回來了。”
在我的眼睛適應黑暗的時候,這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形式需要穿越的距離幾乎是無限的:奧斯曼帝國統治的數個世紀、最為邪惡的戰爭和共產主義的統治。在此處,一個充滿教條、神秘氣氛和野性之美的密室裡,民族的生活又被重溫了一遍。民族的生活也只有從這裡才能逐漸顯現出來。
“你不知道用錘子、釘子或是棍棒殺人是什麼感覺,對吧?”
艾什梅爾的喊聲蓋過了音樂,在忽明忽暗、豔麗的色彩的襯托下,他的臉變成了紫色。我仍然在皮克,在舊塞爾維亞,在一個阿爾巴尼亞的穆斯林光顧的迪斯可舞廳,離塞爾維亞的修道院不遠。
“你知道我為什麼不喝李子白蘭地,而總是喝啤酒嗎?因為遊擊隊員(二戰時塞爾維亞的遊擊隊員)們通常在殺人後喝李子白蘭地。你知道當著一個孩子母親的面,把孩子扔到空中,再用刀尖去接這個孩子是什麼感覺嗎?被綁到燃燒的木棍上呢?屁股被人用斧子劈開,以至於你乞求塞爾維亞人開槍打你的頭而他們卻不肯?”
“而這之後他們竟然還到教堂去。他們竟然還去他媽的教堂。我實在是無話可說了……”
艾什梅爾渾身發抖,“有些事情比邪惡更可怕,簡直是無法言說。”
艾什梅爾繼續喊叫著。他只有26歲,對他所說的事件並無親身的體會。他告訴我,老鼠在他家出沒。那是塞爾維亞人的錯。
時間定格在了1940年11月30日上午10:30分。布加勒斯特開始下雪。在為紀念一位抗擊土耳其人的羅馬尼亞將軍而于17世紀建造的伊利格甘尼教堂內,數百根點燃的蠟燭使得穹頂上穿紅色長袍的基督的形象更加醒目。用帶有純金刺繡的綠色旗子覆蓋著的棺材,排列在中殿的兩旁。祭台助手們用託盤為死者端上了深色糖麵包。天使長邁克軍團--法西斯的“鐵衛團”--(xlv)的14個成員,包括其首領科內柳·澤拉·科德里亞努,即將下葬,主持葬禮、並將宣佈逝者為聖徒的是羅馬尼亞正統教的牧師,他們一直在為逝者唱聖歌,揮動香爐。
兩年以前,國王卡羅爾二世下令勒死了這14個人,剝光了他們的遺體,扔在一條亂葬坑裡,為了讓這些遺體儘快腐爛,還在上面潑上了硫酸。但是到1940年末,卡羅爾國王逃走,羅馬尼亞落入鐵衛團的手中。受害者的遺體殘留物不過是幾個土堆而已,但仍被挖了出來,封裝在14具棺材裡面,重新安葬。在葬禮的結尾,弔唁者聆聽了已故軍團首領科德里亞努的一段錄音,其聲音極為尖利:“你們一定要等到為烈士們報仇的那一天!”
數周之後,復仇開始了。1941年1月22日,天使長邁克軍團的士兵先是唱了正統教的讚美詩,在脖子周圍放上了盛著羅馬尼亞泥土的袋子,相互喝了鮮血,又為自己撒了聖水,然後就入戶劫持了200名男人、婦女和兒童。他們把受害者驅趕上卡車,並開車到了該市的屠宰場,這是布加勒斯特南部靠近蒂姆堡維察河的幾棟紅磚樓房。受害者都是猶太人,他們驅使這些人在冰冷的黑暗中脫光衣服,趴在傳送裝置上。這些猶太人痛苦地吼叫著,卻仍然被驅趕著走完了屠宰所有自動化的程式。鮮血從被割掉頭顱和四肢的軀幹中流淌出來,軍團士兵把它們掛在鉤子上,並貼上“適合人食用”的標籤。他們還把一個五歲的小女孩的軀幹倒掛起來,“上面滿是鮮血……就像是一頭被屠宰的小牛,”一個第二天早上的目擊者如是說。
1989年12月17日晚上10點。在摩爾達維亞2的摩爾達維察修道院,因天色已晚,難以看清壁畫的內容,但修道院院長塔圖麗茲·喬治亞·本尼迪克塔仍然能夠想像出末日審判的場景:野生動物把所有他們吃掉的人都吐了出來,在正義簿上的若干善行抵消了所有的惡跡;使用耀眼的硫磺色染料繪製的天使,正在蓋住黃道十二宮的標記,等待宣佈時間的終結。
像往常一樣,本尼迪克塔院長祈禱了八個小時,但與在布加勒斯特不同的是,這裡沒有提示者,懺悔室了也沒有話筒。在羅馬尼亞北端的山毛櫸樹林裡,掌權者—--就像很久以前的那些土耳其人一樣----也幾乎沒有“安插盯梢的人”。天氣非常溫暖。本尼迪克塔院長前天還看到了彩虹,儘管當時並沒有下雨。在這一天,她聽到了殘害兒童的傳言。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整夜都待在教條裡祈禱。
之後三個晚上,其他修女也過來和她一起整夜祈禱。
於是上帝演示了一個奇跡。他把一種念頭放在了德拉克(魔鬼)的頭腦裡,安排了一次遙感會面。由於不再害怕,人們羞辱了德拉克。因此,那個像希律(Herod)一樣,就是那個像希律一樣殘殺巴勒斯坦的兒童一樣殺害蒂米什瓦拉的兒童的人,就在我們的主誕生的那一天被處死了。
“在羅馬尼亞,《聖經》是鮮活的,” 本尼迪克塔院長語氣堅定地對我說。“聖誕的故事被重新演示。現在,人們有義務進行祈禱,並借助歷史來審視自身的罪惡。”
18世紀末期,在土耳其佔領的漫漫黑夜中最為黑暗的時刻,一位名叫拉菲邇的保加利亞僧侶,在里拉修道院內花費了十二年的時間,雕刻了一尊木質的耶穌受難像,上面刻著600個人物形象,每一個都不過大米粒那麼大。
“這樣的一個十字架的價值有多大?”博尼費修斯神父大聲說。他是一個身材瘦小的駝背的人,留著鐵灰色的長髮和絡腮鬍子,皮膚像嬰兒的一樣柔軟。他已在修道院的牆壁內生活了27年。為了回答自己的問題,他又大聲說:“人的一生的價值有多大?拉菲邇為了雕刻出這個十字架,雙目失明啊!”
里拉修道院被土耳其人一次又一次地洗劫並被夷為平地。但每一次,它都被照原樣重建起來:有條紋的拱門、壓花的木質陽臺、鐘樓和盛放壁畫的建築群,而且在山頂白雪的映襯下,壁畫的顏色呈現出某種新的莊嚴氣象。在土耳其佔領期間,居住在里拉修道院的僧侶多達300人。在保加利亞共產黨統治期間,僧侶數量降低到(xlvii)12人。12個靈魂,為了守護整個民族的遺產,就生活在這個空曠的、老鼠肆虐的空間之中!有些房間的門被嚴實地封閉,幾個世紀之中從未有人踏入過。
現在,這些封閉的門正在被開啟。
我于1990年重返里拉修道院,距離我前一次的訪問又過去了9年。博尼費修斯神父已經去世。一度陰暗冷清的教堂,再度擠滿了來做禮拜的人,點燃的蠟燭幾乎成林,劈啵作響。在教堂的一角掛著國王伯里斯三世的照片,他於1943年被安葬在這裡,但共產黨掌權之後,於1946年挪動了他的墓地。伯里斯的肖像周圍擺滿了蠟燭、野花和聖餐面餅。人們彎腰去親吻他的肖像。
“耶穌基督又回到了保加利亞,”我的嚮導語調平淡地對我說。“我們必須讓共產黨人告訴我們,伯里斯到底被埋葬在哪裡。在現在的保加利亞,有許多秘密有待解開。”
“北伊皮魯斯將會血流遍地!”這句語氣生硬的話,就塗寫在希臘西北部與阿爾巴尼亞的邊界的路邊。北伊皮魯斯--也就是南阿爾巴尼亞--歷史上是希臘的一部分:是亞歷山大大帝的母親奧林皮婭,和皮洛士國王的出生地。皮洛士國王在軍事上慘重的勝跡在“皮洛士式的勝利”一語中得到了紀念。
但是,由於1913年的一份“可恥的”協議,“北伊皮魯斯”被劃入了“現已不存在的卑鄙的阿爾巴尼亞”,希臘成了一個“被肢解”的國家,這個邊境地區3的都主教賽萬次亞諾解釋說。在他的地圖上,北伊皮魯斯是接近50萬希臘人的家鄉,佔據了阿爾巴尼亞領土的50%。賽萬次亞諾被一些人稱作“希臘的霍梅尼”,據傳言曾設法讓遊擊隊員潛入南阿爾巴尼亞,圖謀在共產黨統治結束之後使該地區與希臘統一。
一踏入阿爾巴尼亞與他國接壤的地方,我乘坐的麵包車就進入了迷宮似的、連綿不斷的石灰岩峽谷,沿途怪石嶙峋,樹木已被砍伐光禿。剃著光頭的士兵驅趕的牛車,堵住了坑窪不平的道路。成群結隊身著寬鬆白色衣服、頭戴方頭巾的婦女,肩上扛著大鐮刀或鐵鏟,步履蹣跚地從莊稼地和煙草地收工回家。(xlviii)在一些空蕩蕩的地方,立著用波紋狀金屬和彌縫不嚴實的磚建造的居民房,周圍則是帶刺的鐵絲網和水泥碉堡。
每一樣人造品--肥皂塊、水龍頭、門把手--都像是剛剛發明出來的,流露出某種原始的特徵。褐煤燃燒後含鉛的煙霧在地面上久久消散不掉,賦予該地某種老照片才具有的某種顆粒狀的、泛黃的氛圍。借著鈉燈發出的光,我曾仔細查看過這些希臘裔的阿爾巴尼亞人的面孔。他們眼中的表情是那麼的遙遠。他們幾乎就像是鬼影。在瑟蘭德鎮上的一戶人家,一家五口人圍在一家破舊的俄式黑白電視機前,收看一個希臘頻道播放的“王朝”和CNN。“這裡的生活怎麼樣啊?”我問。“很好。我們需要的東西都齊全,”當父親的回答我說。但孩子們卻一直沉默不語。
這家人最大的男孩陪我到了賓館。“我秘密地接受了洗禮,”他在黑暗中悄悄對我說。“我是希臘人。我還能有什麼辦法?我信仰上帝……我們這裡所有的人都是些可憐蟲。”四天之後,在附近的一個村莊,有兩個人在試圖跨越邊界逃到希臘的時候被擊斃。他們的遺體被倒掛在廣場上。
這個世界就像是一個秘密收藏物品的容器:就是一個光線暗淡的舞臺,人們在這裡拋頭顱、灑熱血,有過美好的憧憬和極度的喜悅。然而,他們的表情依然是僵硬的、遙遠的,就像是被灰塵覆蓋的雕像。“在這裡,我們完全被我們自己的歷史所淹沒,”保加利亞前外交部長魯本·格澤夫這樣對我說。
於是,我養成了逛中世紀教堂和修道院的嗜好,喜歡上了搜尋古書和老照片。在路上遇到人的時候,我總是詢問他們有關過去的問題。只有這樣,現在才是可以理解的。
在這樣的地方,你必須具有對於隱晦不明的事物的熱愛。一連數月,我多次叨擾珍本書店和書商。……
從1915年四月到十月,美國新聞記者和政治激進分子約翰·裡德,在素描畫家鮑德曼·羅賓遜的陪同之下,(xlix)遊歷了塞爾維亞、馬其頓、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和土耳其。裡德出版了他對於他們兩人行程的描述,冠名為《東歐的戰爭》,其時為1916年,即他訪問俄羅斯並撰寫《震撼世界的十天》的前一年。在裡德所有的著作中,《東歐的戰爭》最少為人知,但為了得到首版的作者簽名本,我卻不得不付出399.11美元的高價。該書的蠟紙書頁保存了幾張鉛筆畫。裡德這樣說:
“突然而至的入侵,倉促絕望的抵抗,一座又一座城市被圍困、被消滅,置身於這樣的環境下,人們似乎失去了其獨有的個人的或種族的特色,因此,當消失在瘋狂的人海,捲入你死我活的戰鬥中時,他們相互之間已經沒有什麼差別了。”裡德喜歡在“他們安心把戰爭當作一種營生來做,開始調整自我,適應這種新的生活方式,並開始談論和考慮其他事情”之後再對他們進行觀察。
我也想做同樣的事情:不是在革命或劃時代的選舉發生的過程當中,而是緊隨事件發生之後,當各色人等開始調整自我,適應新的生活方式的時候,再對歐洲已被忘記的後門進行觀察。
我看過的老照片裡面,有一張是哈布斯堡的大公佛朗茨·費迪南,拍攝的是他1914年6月27日在塞拉耶佛城外參加軍事活動的情景,一天之後,他就被暗殺--而這一犯罪事件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跑動的馬蹄揚起了塵土。佛朗茨·費迪南筆直地騎在馬上,正面的那只腳牢牢地套在馬鐙裡,斜挎著馬刀。他留有鬍鬚的臉龐表露了某種堅毅,這種神情與更為天真的、少不更事的年紀更為吻合,他所生活的世界,仍可以模糊地歸結為梅特涅操控的復辟時代,對現代戰爭在技術上的邪惡和極權主義都少有覺察(儘管幾天或幾周之後,一切都將改觀)。
另一張照片則是佛朗茨·費迪南的暗殺者加夫裡洛·普林西普,一個來自塞拉耶佛附近的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普林西普還不到二十歲,貌似非常虛弱:一副瘦骨嶙峋、弱不禁風的樣子。但他的雙眼充滿了野性的能量,與當今恐怖分子死氣沉沉的眼神不一樣。當今的恐怖分子使用自動步槍和用空中陀螺儀引爆的炸彈從遠處來進行暗殺。
世界歷史上最令人驚心動魄的七十五年已經過去了,但由於這些照片被拍攝下來,這些歲月都得到了很好的聚焦。不過,如果以我在路上見到的人們和聽到的聲音為參照,那些照片似乎並沒有那麼古老。
貝爾格勒、布加勒斯特、索菲亞、雅典、阿德里安堡。對於雄心勃勃的新聞記者來說,這些都曾經是可供選擇的新聞電訊的電頭----相當於稍後一些的西貢、(l)貝魯特和馬納瓜。厄内斯特·海明威在1922年從阿德里安堡(即現在的埃迪爾內,在土耳其的色雷斯)發回了他最為著名的新聞報導,描述希臘難民“失魂落魄地行走在雨裡”的情況,他們的物品就堆放在旁邊的牛車上。
巴爾幹諸國就是最初的第三世界,這要比西方媒體發明這個詞語早很多。在這個毗鄰中東的多山的半島上,報紙的記者寫出了20世紀最初的關於渾身沾滿泥巴的難民積聚的報導,也完成了事實與臆想參半的新聞和遊記相結合的最早的著作,而那時亞洲和非洲仍顯得相當遙遠。
在貝魯特或別的什麼地方,不論發生了什麼,都首先在巴爾幹發生過,而且是在很久以前。
巴爾幹培育了本世紀第一批的恐怖分子。馬其頓國內革命組織(IMRO)就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巴解組織,由於有保加利亞的資助,致力於恢復被希臘和南斯拉夫在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之後佔領的馬其頓的部分地區。像當今貝魯特南部郊區的什葉派教徒一樣,這些在槍支和正統教《聖經》上宣誓效忠的IMRO殺手,來自斯高彼亞、貝爾格勒和索菲亞貧民窟的沒有根基的、缺乏教養的無產者。扣留人質和大規模屠殺無辜者是常有的事情。甚至伊朗神職人員的瘋狂行為都在巴爾幹有先例。在1912年和1913年的巴爾幹戰爭期間,在馬其頓的一個希臘主教下令暗殺一名保加利亞政客,並且派人把切割下來的首級送回教堂供人拍照。
20世紀的歷史從巴爾幹開始。在這裡,人們由於貧窮和民族的對抗而被孤立起來,除了仇恨別無選擇。在這裡,政治被降低到近乎無政府的狀態,因而在歷史上經常氾濫失控,漫過多瑙河並衝擊中歐。
例如,納粹主義就可以說肇始於巴爾幹。靠近南部斯拉夫世界的維也納,是一個醞釀民族怨恨的溫床,在這個城市的廉價旅館裡面,希特勒學會了如何以一種具有傳染性的方式表達仇恨。
人們爆發殘暴行為的地方的土地到底是什麼樣子?果真存在某種邪惡的嗅覺,風氣,或是那個地方的山川形勢果真具有某種特別之處,從而連累了這個地方的人們?(li)
我是從中歐,從紐倫堡和達濠,開始我的行程的,但我什麼也沒有感覺到。這些地方到處都是博物館;似乎已經沒有日常生活的煙火氣息。納粹經常舉辦大規模集會的露天體育館,只剩下了一堵牆,而這成為德國雅皮士聚會的場所。
在維也納,我第一次捕捉到了某種輕微的跡象。在維也納,W.A.莫札特的地位只配得到一尊雕像、一條小巷和一個廣場。卡爾·呂格博士得到了更大的紀念碑、更大的廣場,和林斯特拉斯區最威嚴的地方--卡爾·呂格博士之環:這裡坐落著新古典主義的議會大廈、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學建築、巴羅克風格的群山劇院、哥特風格的市政廳和人民公園。
呂格在世紀之交曾擔任市長,與同時期的另外一個奧地利政客、政治排猶主義之父G.V.熊納勒齊名。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說:“我把這個人看作是所有時代德國最偉大的市長……如果卡爾·呂格博士果真曾在德國生活的話,他肯定會成為我國人民中最為優秀的分子。”希特勒說,他自己的思想直接來自呂格。1895年5月29日,在獲知呂格在維也納市議會選舉中獲勝消息的當天晚上,希歐多爾·赫茨爾(Theodor Herzl)就連夜起草了猶太人離開歐洲的計畫。
我仔細地查看了矗立在卡爾·呂格博士廣場(不要把它錯當作卡爾·呂格博士之環)上的呂格紀念碑。一手放在胸前、衣著極其考究的、瀟灑的卡爾,正專注地展望未來,目光中充滿了決心;身強力壯的、裸著上身的工人,拿著鐵鏟和鎬頭,分佈在底座的周圍。
在當今的德國,這樣的一個紀念碑肯定會引發醜聞。但在當時的奧地利,這並沒有什麼不妥。“卡爾·呂格是維也納最偉大的市長,”奧地利當地的一個記者說,並同時聳了聳肩。“他並不真的是一個反猶主義者。他只是把反猶主義當作一種政治技巧。”
我繼續遊歷。梅特涅說,巴爾幹從倫韋格開始,這條路是維也納在東部和南部的出口。
你越是靠近德語世界的東部或南部邊緣,換言之,你越是靠近具有威脅性的、數量也更多的斯拉夫人,德意志民族主義就變得越來越不安全,因而也就越來越危險。(lii)在德語世界的東部邊界,波美拉尼亞和西西里亞的德意志人都質疑波蘭邊界的合法性。在南邊,在奧地利,在這個來自斯拉夫世界的血液果真在“德意志人的”血管裡流淌的地方,對於這個基本事實的否認,採取了極為頑固的、泛日爾曼的偏執狂的形式。
我來到了克拉根福,這是處在奧地利最南端的卡林西亞州的州府所在地,是公認的“前納粹的寶地”。相對於它的面積,來自卡林西亞的死亡集中營的衛兵的數量,超過了德國和奧地利的任何一個地方。20世紀80年代,在卡林西亞發生了一場贊成分別設立學校的運動:上帝禁止德國孩子與斯洛文尼亞人一起學習,因為斯洛文尼亞人是斯拉夫人。我參觀了右翼的自由黨的和“卡林西亞祖國服務局”的辦公室,後者是一個類似民兵的組織,成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五十年代重新活躍起來,並呈現出一種新納粹主義的取向。我試著去刺激一位自由党的發言人,但沒有成功。
提問:“西蒙·維森塔爾告訴我說,在一個像奧地利這樣的民主國家,任何在其名稱中使用“自由”這個字眼的政黨,都要麼是納粹的,要麼是共產主義的。你對此怎麼看?”
回答: “赫爾·維森塔爾是一個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他可以有他的看法,那是他的權力。但是,我可以講講我們為什麼是不同的嗎?……”
我被告知說,把奧地利包含在內的大德國觀念早已消亡。奧地利右翼關心的只是在語言的邊界地區保護德語語言的獨立完整性。用來裝飾自由黨辦公室牆壁的是枯燥泛味的現代藝術品,而不是橫幅或嚴格控制的照片。接著我遭遇了更深層次的失望:在克拉根福的街頭,我沒有遭遇到令人厭惡的、褐衫黨那樣死心塌地擁護納粹的狹隘排外;觸入眼簾的卻是托斯坦·凡勃侖所描述的有閑階級。
穿著著質地優良、樣式考究的衣服的學齡少年,不時地騎著彩色的山地自行車從我身邊快速掠過。我看到一名男子穿著紫色絨面上衣,帶著喬治·阿瑪尼眼鏡,婦女們穿的則是全套的吉爾·桑德或嬌蘭,戴的是最為微妙的秋天色調的絲綢圍巾。要不是由於辦公室窗戶的鍍鉻合金的顏色,這裡的仿巴羅克的建築物,就像是從黑森林牌櫻桃蛋糕上精心切下來似的。玩具火車、新秀麗箱包、樂高空間站模型、蒂凡尼的珠寶,充斥著在路邊的展示櫥窗。從母嬰用品店再過去幾個門面,有一家專賣來自巴黎的女性內衣的商店,其式樣花裡胡哨,價格也高得離奇。店中白膚金髮碧眼的女孩使用的香水,散發出汗水和動物的氣息。(liii)党衛軍精銳部隊的後代,已經蛻變為被精心調教的、會表演的老虎,並且,為了安全起見,這些老虎還被規規矩矩地關在舒適的中產階級的籠房裡。
這裡的每個人都按照日常的軌道來生活……。在旅行社的展示窗裡,以色列只不過是當地的太陽崇拜者冬天的度假地。自由党和祖國服務局的那些真正的信仰者,越來越被孤立,也不得不維持舉止得體的外表。這裡呈現出來的不再是排猶主義或其他的傳統的過度行為,而是赤裸裸的消費主義。卡林西亞人變成了一個被馴服的物種。
從1989年開始,為了增加其在議會的席位,自由黨越來越多地談論起與斯洛文尼亞人的合作。年老的納粹追逐者維森塔爾對我講了這樣的理由:“如果沒有經濟危機,自由黨別無選擇,只能適應形勢。”這位睿智而瘦削的長者鎮定地告誡我說,邪惡的治癒,不需要痛苦的煎熬或悔恨,而只需要資產階級民主和持續一個十年、又一個十年、再一個十年的富裕所提供的令人沉溺其中的鎮靜,因為人們一旦於渾然不覺中鎮靜下來,這一模式就變得根深蒂固,即便是經濟災難也無法撼動它。
這是20世紀的最後一個十年。我認真聆聽的是維森塔爾的告誡,而不是梅特涅的話:巴爾幹不再是從維也納的門戶開始,甚至也不再是從克拉根福開始。
在奧地利與曾是南斯拉夫的地方接壤的南部邊界,甚至火車一等包廂裡的供暖系統也被停止使用。餐車也被隔離開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鍍鋅的立式櫃檯,只供應啤酒、李子白蘭地、不帶過濾嘴的劣質煙捲兒。經過多次停靠站之後,指甲裡藏汙納垢的男人們擁擠到櫃檯前喝酒抽煙。不相互大聲說話或痛飲烈酒的時候,這些人則會靜悄悄地、專注地翻看色情雜誌。與他們在奧地利的同屬勞動階層的人們不同,他們沒有留男女皆宜的髮型,顯然他們在冬天來臨的時候也不指望去突尼斯或以色列度假。在這個地方,如果人們足夠幸運,擁有最起碼的本土文化保護上的一致性的話,那麼,自由党和祖國服務局的人很可能就會拋棄他們的現代藝術,拋棄那種認慫的做法,敢於直面一個記者的提問。(liv)
雪花落在了窗戶上。黑色的褐煤煙霧從磚和廢金屬搭成的煙囪裡冒了出來。這片土地就像是一個元氣耗盡、除了咳嗽就知道咒駡的妓女的臉,醜陋不堪而毫無生機。殘暴行為給這片水土留下的痕跡不難辨認:共產主義曾充當過它的不可一世的守護者。
因此,我不可能久留此地。不久,不論是九十年代末期,還是以後的數十年,整個畫面都將褪色,就像在克拉根福一樣,一切都已改變。(lv)
我渾身顫抖,手腳也有些忙亂。我故意選擇在這個令人毛骨悚然、黎明前的時刻造訪“舊塞爾維亞”遺留下來的皮克修道院。在東正教裡,精神指導要求人們進行辛勤的勞作,不過作為獎賞,會向他們曉諭有關地獄和救贖的資訊,但這同樣需要人們苦行力修方能得到。西方的入侵者如果不肯用他的整個存在來感知的話,他就不要指望自己能夠理解這一切。
置身于西元1250年繪成的使徒教堂內,我的雙眼一時不能適應,什麼也看不見。不過短短幾分鐘,可感覺非常漫長,像是從未間斷的幾百年,讓人充滿了挫敗感。我沒帶手電筒,也沒帶蠟燭。但是,當你什麼都看不見的時候,你的意志卻更加集中。
彼達·彼得洛維奇·尼格斯在《高山花環》這部用塞爾維亞語寫成的最偉大的詩篇中說,“眼睛並不妨礙視而不見的人;他穩穩當 當地……走在同一條路上,就像醉酒的人,始終扶著籬笆牆。”在這部著作中,對於改信伊斯蘭教的人們的大規模屠殺,被當作是為了打贏土耳其穆斯林1的戰鬥的必要手段。(xliii)就在黑暗即將減退的時刻,我瞬間明白了掙扎、絕望和仇恨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我的雙眼在黑暗中的摸索教給了國家生存的首要原則:哪怕是幾乎沒有任何光明,也可以創造出一個完整的世界。也就過了約莫一分鐘的時間,各種面孔就從幽暗中浮現出來:那一張張來自早熟的塞爾維亞的過去的面孔,愁容遍佈,飽經風霜,向人們展示出某種靈性和原始,西方人對此並不陌生,因為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身上已經得到了很好的體現。我感覺自己仿佛走進了一顆頭顱之內,看到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在燃燒。
夢想似乎是可以觸摸的了,如真如幻:穿著紫色袍子的聖尼古拉,在用他的黑色的、令人不敢直視的雙眼看著我的腦後;塞爾維亞的主保聖人、我所在的教堂的創立者聖薩瓦,從水一樣的真空中緩緩落下,慷慨地把仁慈和靈感送贈給我;升天的基督,雖是農夫出身的神,卻擺脫了身體煎熬的最後階段,已達到超凡脫俗的境界,比任何征服者或俗世的思想意識更令人畏懼。
使徒與聖徒和中世紀塞爾維亞的國王與主教混雜在一起。他們似乎都從信仰的變形鏡中走了出來:身軀被拖長,長著令人恐怖的手腳和頭。許多聖徒的眼睛已經被摳掉。根據某種農民的信仰,用來繪製聖徒眼睛的泥灰和染料,可以治好失明。
迷信,盲目崇拜?這是西方人的心靈在說話。用約瑟夫·康拉德的話來說,這樣的心靈“並不擁有一種得自於上古的、親身經歷的知識,因而就無從知曉歷史上的獨裁政體如何壓抑思想、捍衛權力和維持其存在。因而,”康拉德在《在西方的目光下》中認為,對於一個西方公民來說,“他怎麼也想不明白,遭受鞭撻竟然可以成為一種實際上的調查措施,或是一種懲罰。”
這所教堂提醒人們:黑暗越是深沉,反抗就越缺少理性,也就越令人恐怖。
根據艾瑞克·安布勒的《對戴爾徹甫的審判》,史達林大清洗的受害者之一、遭受監禁的戴爾徹甫夫人遺憾地表示:“在保加利亞和在希臘,在南斯拉夫,在所有曾受土耳其統治的歐洲國家,都是一模一樣的。”(xliv)“因此,躲避在牆壁後面的我們的人民,其實是生活在狹隘的虛幻的世界之中……他們用民族生活的畫面來裝點牆壁……既然我們又重新躲避到了牆壁後面,我們父輩的和我們童年時代的習慣也就回來了。”
在我的眼睛適應黑暗的時候,這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形式需要穿越的距離幾乎是無限的:奧斯曼帝國統治的數個世紀、最為邪惡的戰爭和共產主義的統治。在此處,一個充滿教條、神秘氣氛和野性之美的密室裡,民族的生活又被重溫了一遍。民族的生活也只有從這裡才能逐漸顯現出來。
“你不知道用錘子、釘子或是棍棒殺人是什麼感覺,對吧?”
艾什梅爾的喊聲蓋過了音樂,在忽明忽暗、豔麗的色彩的襯托下,他的臉變成了紫色。我仍然在皮克,在舊塞爾維亞,在一個阿爾巴尼亞的穆斯林光顧的迪斯可舞廳,離塞爾維亞的修道院不遠。
“你知道我為什麼不喝李子白蘭地,而總是喝啤酒嗎?因為遊擊隊員(二戰時塞爾維亞的遊擊隊員)們通常在殺人後喝李子白蘭地。你知道當著一個孩子母親的面,把孩子扔到空中,再用刀尖去接這個孩子是什麼感覺嗎?被綁到燃燒的木棍上呢?屁股被人用斧子劈開,以至於你乞求塞爾維亞人開槍打你的頭而他們卻不肯?”
“而這之後他們竟然還到教堂去。他們竟然還去他媽的教堂。我實在是無話可說了……”
艾什梅爾渾身發抖,“有些事情比邪惡更可怕,簡直是無法言說。”
艾什梅爾繼續喊叫著。他只有26歲,對他所說的事件並無親身的體會。他告訴我,老鼠在他家出沒。那是塞爾維亞人的錯。
時間定格在了1940年11月30日上午10:30分。布加勒斯特開始下雪。在為紀念一位抗擊土耳其人的羅馬尼亞將軍而于17世紀建造的伊利格甘尼教堂內,數百根點燃的蠟燭使得穹頂上穿紅色長袍的基督的形象更加醒目。用帶有純金刺繡的綠色旗子覆蓋著的棺材,排列在中殿的兩旁。祭台助手們用託盤為死者端上了深色糖麵包。天使長邁克軍團--法西斯的“鐵衛團”--(xlv)的14個成員,包括其首領科內柳·澤拉·科德里亞努,即將下葬,主持葬禮、並將宣佈逝者為聖徒的是羅馬尼亞正統教的牧師,他們一直在為逝者唱聖歌,揮動香爐。
兩年以前,國王卡羅爾二世下令勒死了這14個人,剝光了他們的遺體,扔在一條亂葬坑裡,為了讓這些遺體儘快腐爛,還在上面潑上了硫酸。但是到1940年末,卡羅爾國王逃走,羅馬尼亞落入鐵衛團的手中。受害者的遺體殘留物不過是幾個土堆而已,但仍被挖了出來,封裝在14具棺材裡面,重新安葬。在葬禮的結尾,弔唁者聆聽了已故軍團首領科德里亞努的一段錄音,其聲音極為尖利:“你們一定要等到為烈士們報仇的那一天!”
數周之後,復仇開始了。1941年1月22日,天使長邁克軍團的士兵先是唱了正統教的讚美詩,在脖子周圍放上了盛著羅馬尼亞泥土的袋子,相互喝了鮮血,又為自己撒了聖水,然後就入戶劫持了200名男人、婦女和兒童。他們把受害者驅趕上卡車,並開車到了該市的屠宰場,這是布加勒斯特南部靠近蒂姆堡維察河的幾棟紅磚樓房。受害者都是猶太人,他們驅使這些人在冰冷的黑暗中脫光衣服,趴在傳送裝置上。這些猶太人痛苦地吼叫著,卻仍然被驅趕著走完了屠宰所有自動化的程式。鮮血從被割掉頭顱和四肢的軀幹中流淌出來,軍團士兵把它們掛在鉤子上,並貼上“適合人食用”的標籤。他們還把一個五歲的小女孩的軀幹倒掛起來,“上面滿是鮮血……就像是一頭被屠宰的小牛,”一個第二天早上的目擊者如是說。
1989年12月17日晚上10點。在摩爾達維亞2的摩爾達維察修道院,因天色已晚,難以看清壁畫的內容,但修道院院長塔圖麗茲·喬治亞·本尼迪克塔仍然能夠想像出末日審判的場景:野生動物把所有他們吃掉的人都吐了出來,在正義簿上的若干善行抵消了所有的惡跡;使用耀眼的硫磺色染料繪製的天使,正在蓋住黃道十二宮的標記,等待宣佈時間的終結。
像往常一樣,本尼迪克塔院長祈禱了八個小時,但與在布加勒斯特不同的是,這裡沒有提示者,懺悔室了也沒有話筒。在羅馬尼亞北端的山毛櫸樹林裡,掌權者—--就像很久以前的那些土耳其人一樣----也幾乎沒有“安插盯梢的人”。天氣非常溫暖。本尼迪克塔院長前天還看到了彩虹,儘管當時並沒有下雨。在這一天,她聽到了殘害兒童的傳言。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整夜都待在教條裡祈禱。
之後三個晚上,其他修女也過來和她一起整夜祈禱。
於是上帝演示了一個奇跡。他把一種念頭放在了德拉克(魔鬼)的頭腦裡,安排了一次遙感會面。由於不再害怕,人們羞辱了德拉克。因此,那個像希律(Herod)一樣,就是那個像希律一樣殘殺巴勒斯坦的兒童一樣殺害蒂米什瓦拉的兒童的人,就在我們的主誕生的那一天被處死了。
“在羅馬尼亞,《聖經》是鮮活的,” 本尼迪克塔院長語氣堅定地對我說。“聖誕的故事被重新演示。現在,人們有義務進行祈禱,並借助歷史來審視自身的罪惡。”
18世紀末期,在土耳其佔領的漫漫黑夜中最為黑暗的時刻,一位名叫拉菲邇的保加利亞僧侶,在里拉修道院內花費了十二年的時間,雕刻了一尊木質的耶穌受難像,上面刻著600個人物形象,每一個都不過大米粒那麼大。
“這樣的一個十字架的價值有多大?”博尼費修斯神父大聲說。他是一個身材瘦小的駝背的人,留著鐵灰色的長髮和絡腮鬍子,皮膚像嬰兒的一樣柔軟。他已在修道院的牆壁內生活了27年。為了回答自己的問題,他又大聲說:“人的一生的價值有多大?拉菲邇為了雕刻出這個十字架,雙目失明啊!”
里拉修道院被土耳其人一次又一次地洗劫並被夷為平地。但每一次,它都被照原樣重建起來:有條紋的拱門、壓花的木質陽臺、鐘樓和盛放壁畫的建築群,而且在山頂白雪的映襯下,壁畫的顏色呈現出某種新的莊嚴氣象。在土耳其佔領期間,居住在里拉修道院的僧侶多達300人。在保加利亞共產黨統治期間,僧侶數量降低到(xlvii)12人。12個靈魂,為了守護整個民族的遺產,就生活在這個空曠的、老鼠肆虐的空間之中!有些房間的門被嚴實地封閉,幾個世紀之中從未有人踏入過。
現在,這些封閉的門正在被開啟。
我于1990年重返里拉修道院,距離我前一次的訪問又過去了9年。博尼費修斯神父已經去世。一度陰暗冷清的教堂,再度擠滿了來做禮拜的人,點燃的蠟燭幾乎成林,劈啵作響。在教堂的一角掛著國王伯里斯三世的照片,他於1943年被安葬在這裡,但共產黨掌權之後,於1946年挪動了他的墓地。伯里斯的肖像周圍擺滿了蠟燭、野花和聖餐面餅。人們彎腰去親吻他的肖像。
“耶穌基督又回到了保加利亞,”我的嚮導語調平淡地對我說。“我們必須讓共產黨人告訴我們,伯里斯到底被埋葬在哪裡。在現在的保加利亞,有許多秘密有待解開。”
“北伊皮魯斯將會血流遍地!”這句語氣生硬的話,就塗寫在希臘西北部與阿爾巴尼亞的邊界的路邊。北伊皮魯斯--也就是南阿爾巴尼亞--歷史上是希臘的一部分:是亞歷山大大帝的母親奧林皮婭,和皮洛士國王的出生地。皮洛士國王在軍事上慘重的勝跡在“皮洛士式的勝利”一語中得到了紀念。
但是,由於1913年的一份“可恥的”協議,“北伊皮魯斯”被劃入了“現已不存在的卑鄙的阿爾巴尼亞”,希臘成了一個“被肢解”的國家,這個邊境地區3的都主教賽萬次亞諾解釋說。在他的地圖上,北伊皮魯斯是接近50萬希臘人的家鄉,佔據了阿爾巴尼亞領土的50%。賽萬次亞諾被一些人稱作“希臘的霍梅尼”,據傳言曾設法讓遊擊隊員潛入南阿爾巴尼亞,圖謀在共產黨統治結束之後使該地區與希臘統一。
一踏入阿爾巴尼亞與他國接壤的地方,我乘坐的麵包車就進入了迷宮似的、連綿不斷的石灰岩峽谷,沿途怪石嶙峋,樹木已被砍伐光禿。剃著光頭的士兵驅趕的牛車,堵住了坑窪不平的道路。成群結隊身著寬鬆白色衣服、頭戴方頭巾的婦女,肩上扛著大鐮刀或鐵鏟,步履蹣跚地從莊稼地和煙草地收工回家。(xlviii)在一些空蕩蕩的地方,立著用波紋狀金屬和彌縫不嚴實的磚建造的居民房,周圍則是帶刺的鐵絲網和水泥碉堡。
每一樣人造品--肥皂塊、水龍頭、門把手--都像是剛剛發明出來的,流露出某種原始的特徵。褐煤燃燒後含鉛的煙霧在地面上久久消散不掉,賦予該地某種老照片才具有的某種顆粒狀的、泛黃的氛圍。借著鈉燈發出的光,我曾仔細查看過這些希臘裔的阿爾巴尼亞人的面孔。他們眼中的表情是那麼的遙遠。他們幾乎就像是鬼影。在瑟蘭德鎮上的一戶人家,一家五口人圍在一家破舊的俄式黑白電視機前,收看一個希臘頻道播放的“王朝”和CNN。“這裡的生活怎麼樣啊?”我問。“很好。我們需要的東西都齊全,”當父親的回答我說。但孩子們卻一直沉默不語。
這家人最大的男孩陪我到了賓館。“我秘密地接受了洗禮,”他在黑暗中悄悄對我說。“我是希臘人。我還能有什麼辦法?我信仰上帝……我們這裡所有的人都是些可憐蟲。”四天之後,在附近的一個村莊,有兩個人在試圖跨越邊界逃到希臘的時候被擊斃。他們的遺體被倒掛在廣場上。
這個世界就像是一個秘密收藏物品的容器:就是一個光線暗淡的舞臺,人們在這裡拋頭顱、灑熱血,有過美好的憧憬和極度的喜悅。然而,他們的表情依然是僵硬的、遙遠的,就像是被灰塵覆蓋的雕像。“在這裡,我們完全被我們自己的歷史所淹沒,”保加利亞前外交部長魯本·格澤夫這樣對我說。
於是,我養成了逛中世紀教堂和修道院的嗜好,喜歡上了搜尋古書和老照片。在路上遇到人的時候,我總是詢問他們有關過去的問題。只有這樣,現在才是可以理解的。
在這樣的地方,你必須具有對於隱晦不明的事物的熱愛。一連數月,我多次叨擾珍本書店和書商。……
從1915年四月到十月,美國新聞記者和政治激進分子約翰·裡德,在素描畫家鮑德曼·羅賓遜的陪同之下,(xlix)遊歷了塞爾維亞、馬其頓、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和土耳其。裡德出版了他對於他們兩人行程的描述,冠名為《東歐的戰爭》,其時為1916年,即他訪問俄羅斯並撰寫《震撼世界的十天》的前一年。在裡德所有的著作中,《東歐的戰爭》最少為人知,但為了得到首版的作者簽名本,我卻不得不付出399.11美元的高價。該書的蠟紙書頁保存了幾張鉛筆畫。裡德這樣說:
“突然而至的入侵,倉促絕望的抵抗,一座又一座城市被圍困、被消滅,置身於這樣的環境下,人們似乎失去了其獨有的個人的或種族的特色,因此,當消失在瘋狂的人海,捲入你死我活的戰鬥中時,他們相互之間已經沒有什麼差別了。”裡德喜歡在“他們安心把戰爭當作一種營生來做,開始調整自我,適應這種新的生活方式,並開始談論和考慮其他事情”之後再對他們進行觀察。
我也想做同樣的事情:不是在革命或劃時代的選舉發生的過程當中,而是緊隨事件發生之後,當各色人等開始調整自我,適應新的生活方式的時候,再對歐洲已被忘記的後門進行觀察。
我看過的老照片裡面,有一張是哈布斯堡的大公佛朗茨·費迪南,拍攝的是他1914年6月27日在塞拉耶佛城外參加軍事活動的情景,一天之後,他就被暗殺--而這一犯罪事件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跑動的馬蹄揚起了塵土。佛朗茨·費迪南筆直地騎在馬上,正面的那只腳牢牢地套在馬鐙裡,斜挎著馬刀。他留有鬍鬚的臉龐表露了某種堅毅,這種神情與更為天真的、少不更事的年紀更為吻合,他所生活的世界,仍可以模糊地歸結為梅特涅操控的復辟時代,對現代戰爭在技術上的邪惡和極權主義都少有覺察(儘管幾天或幾周之後,一切都將改觀)。
另一張照片則是佛朗茨·費迪南的暗殺者加夫裡洛·普林西普,一個來自塞拉耶佛附近的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普林西普還不到二十歲,貌似非常虛弱:一副瘦骨嶙峋、弱不禁風的樣子。但他的雙眼充滿了野性的能量,與當今恐怖分子死氣沉沉的眼神不一樣。當今的恐怖分子使用自動步槍和用空中陀螺儀引爆的炸彈從遠處來進行暗殺。
世界歷史上最令人驚心動魄的七十五年已經過去了,但由於這些照片被拍攝下來,這些歲月都得到了很好的聚焦。不過,如果以我在路上見到的人們和聽到的聲音為參照,那些照片似乎並沒有那麼古老。
貝爾格勒、布加勒斯特、索菲亞、雅典、阿德里安堡。對於雄心勃勃的新聞記者來說,這些都曾經是可供選擇的新聞電訊的電頭----相當於稍後一些的西貢、(l)貝魯特和馬納瓜。厄内斯特·海明威在1922年從阿德里安堡(即現在的埃迪爾內,在土耳其的色雷斯)發回了他最為著名的新聞報導,描述希臘難民“失魂落魄地行走在雨裡”的情況,他們的物品就堆放在旁邊的牛車上。
巴爾幹諸國就是最初的第三世界,這要比西方媒體發明這個詞語早很多。在這個毗鄰中東的多山的半島上,報紙的記者寫出了20世紀最初的關於渾身沾滿泥巴的難民積聚的報導,也完成了事實與臆想參半的新聞和遊記相結合的最早的著作,而那時亞洲和非洲仍顯得相當遙遠。
在貝魯特或別的什麼地方,不論發生了什麼,都首先在巴爾幹發生過,而且是在很久以前。
巴爾幹培育了本世紀第一批的恐怖分子。馬其頓國內革命組織(IMRO)就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巴解組織,由於有保加利亞的資助,致力於恢復被希臘和南斯拉夫在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之後佔領的馬其頓的部分地區。像當今貝魯特南部郊區的什葉派教徒一樣,這些在槍支和正統教《聖經》上宣誓效忠的IMRO殺手,來自斯高彼亞、貝爾格勒和索菲亞貧民窟的沒有根基的、缺乏教養的無產者。扣留人質和大規模屠殺無辜者是常有的事情。甚至伊朗神職人員的瘋狂行為都在巴爾幹有先例。在1912年和1913年的巴爾幹戰爭期間,在馬其頓的一個希臘主教下令暗殺一名保加利亞政客,並且派人把切割下來的首級送回教堂供人拍照。
20世紀的歷史從巴爾幹開始。在這裡,人們由於貧窮和民族的對抗而被孤立起來,除了仇恨別無選擇。在這裡,政治被降低到近乎無政府的狀態,因而在歷史上經常氾濫失控,漫過多瑙河並衝擊中歐。
例如,納粹主義就可以說肇始於巴爾幹。靠近南部斯拉夫世界的維也納,是一個醞釀民族怨恨的溫床,在這個城市的廉價旅館裡面,希特勒學會了如何以一種具有傳染性的方式表達仇恨。
人們爆發殘暴行為的地方的土地到底是什麼樣子?果真存在某種邪惡的嗅覺,風氣,或是那個地方的山川形勢果真具有某種特別之處,從而連累了這個地方的人們?(li)
我是從中歐,從紐倫堡和達濠,開始我的行程的,但我什麼也沒有感覺到。這些地方到處都是博物館;似乎已經沒有日常生活的煙火氣息。納粹經常舉辦大規模集會的露天體育館,只剩下了一堵牆,而這成為德國雅皮士聚會的場所。
在維也納,我第一次捕捉到了某種輕微的跡象。在維也納,W.A.莫札特的地位只配得到一尊雕像、一條小巷和一個廣場。卡爾·呂格博士得到了更大的紀念碑、更大的廣場,和林斯特拉斯區最威嚴的地方--卡爾·呂格博士之環:這裡坐落著新古典主義的議會大廈、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學建築、巴羅克風格的群山劇院、哥特風格的市政廳和人民公園。
呂格在世紀之交曾擔任市長,與同時期的另外一個奧地利政客、政治排猶主義之父G.V.熊納勒齊名。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說:“我把這個人看作是所有時代德國最偉大的市長……如果卡爾·呂格博士果真曾在德國生活的話,他肯定會成為我國人民中最為優秀的分子。”希特勒說,他自己的思想直接來自呂格。1895年5月29日,在獲知呂格在維也納市議會選舉中獲勝消息的當天晚上,希歐多爾·赫茨爾(Theodor Herzl)就連夜起草了猶太人離開歐洲的計畫。
我仔細地查看了矗立在卡爾·呂格博士廣場(不要把它錯當作卡爾·呂格博士之環)上的呂格紀念碑。一手放在胸前、衣著極其考究的、瀟灑的卡爾,正專注地展望未來,目光中充滿了決心;身強力壯的、裸著上身的工人,拿著鐵鏟和鎬頭,分佈在底座的周圍。
在當今的德國,這樣的一個紀念碑肯定會引發醜聞。但在當時的奧地利,這並沒有什麼不妥。“卡爾·呂格是維也納最偉大的市長,”奧地利當地的一個記者說,並同時聳了聳肩。“他並不真的是一個反猶主義者。他只是把反猶主義當作一種政治技巧。”
我繼續遊歷。梅特涅說,巴爾幹從倫韋格開始,這條路是維也納在東部和南部的出口。
你越是靠近德語世界的東部或南部邊緣,換言之,你越是靠近具有威脅性的、數量也更多的斯拉夫人,德意志民族主義就變得越來越不安全,因而也就越來越危險。(lii)在德語世界的東部邊界,波美拉尼亞和西西里亞的德意志人都質疑波蘭邊界的合法性。在南邊,在奧地利,在這個來自斯拉夫世界的血液果真在“德意志人的”血管裡流淌的地方,對於這個基本事實的否認,採取了極為頑固的、泛日爾曼的偏執狂的形式。
我來到了克拉根福,這是處在奧地利最南端的卡林西亞州的州府所在地,是公認的“前納粹的寶地”。相對於它的面積,來自卡林西亞的死亡集中營的衛兵的數量,超過了德國和奧地利的任何一個地方。20世紀80年代,在卡林西亞發生了一場贊成分別設立學校的運動:上帝禁止德國孩子與斯洛文尼亞人一起學習,因為斯洛文尼亞人是斯拉夫人。我參觀了右翼的自由黨的和“卡林西亞祖國服務局”的辦公室,後者是一個類似民兵的組織,成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五十年代重新活躍起來,並呈現出一種新納粹主義的取向。我試著去刺激一位自由党的發言人,但沒有成功。
提問:“西蒙·維森塔爾告訴我說,在一個像奧地利這樣的民主國家,任何在其名稱中使用“自由”這個字眼的政黨,都要麼是納粹的,要麼是共產主義的。你對此怎麼看?”
回答: “赫爾·維森塔爾是一個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他可以有他的看法,那是他的權力。但是,我可以講講我們為什麼是不同的嗎?……”
我被告知說,把奧地利包含在內的大德國觀念早已消亡。奧地利右翼關心的只是在語言的邊界地區保護德語語言的獨立完整性。用來裝飾自由黨辦公室牆壁的是枯燥泛味的現代藝術品,而不是橫幅或嚴格控制的照片。接著我遭遇了更深層次的失望:在克拉根福的街頭,我沒有遭遇到令人厭惡的、褐衫黨那樣死心塌地擁護納粹的狹隘排外;觸入眼簾的卻是托斯坦·凡勃侖所描述的有閑階級。
穿著著質地優良、樣式考究的衣服的學齡少年,不時地騎著彩色的山地自行車從我身邊快速掠過。我看到一名男子穿著紫色絨面上衣,帶著喬治·阿瑪尼眼鏡,婦女們穿的則是全套的吉爾·桑德或嬌蘭,戴的是最為微妙的秋天色調的絲綢圍巾。要不是由於辦公室窗戶的鍍鉻合金的顏色,這裡的仿巴羅克的建築物,就像是從黑森林牌櫻桃蛋糕上精心切下來似的。玩具火車、新秀麗箱包、樂高空間站模型、蒂凡尼的珠寶,充斥著在路邊的展示櫥窗。從母嬰用品店再過去幾個門面,有一家專賣來自巴黎的女性內衣的商店,其式樣花裡胡哨,價格也高得離奇。店中白膚金髮碧眼的女孩使用的香水,散發出汗水和動物的氣息。(liii)党衛軍精銳部隊的後代,已經蛻變為被精心調教的、會表演的老虎,並且,為了安全起見,這些老虎還被規規矩矩地關在舒適的中產階級的籠房裡。
這裡的每個人都按照日常的軌道來生活……。在旅行社的展示窗裡,以色列只不過是當地的太陽崇拜者冬天的度假地。自由党和祖國服務局的那些真正的信仰者,越來越被孤立,也不得不維持舉止得體的外表。這裡呈現出來的不再是排猶主義或其他的傳統的過度行為,而是赤裸裸的消費主義。卡林西亞人變成了一個被馴服的物種。
從1989年開始,為了增加其在議會的席位,自由黨越來越多地談論起與斯洛文尼亞人的合作。年老的納粹追逐者維森塔爾對我講了這樣的理由:“如果沒有經濟危機,自由黨別無選擇,只能適應形勢。”這位睿智而瘦削的長者鎮定地告誡我說,邪惡的治癒,不需要痛苦的煎熬或悔恨,而只需要資產階級民主和持續一個十年、又一個十年、再一個十年的富裕所提供的令人沉溺其中的鎮靜,因為人們一旦於渾然不覺中鎮靜下來,這一模式就變得根深蒂固,即便是經濟災難也無法撼動它。
這是20世紀的最後一個十年。我認真聆聽的是維森塔爾的告誡,而不是梅特涅的話:巴爾幹不再是從維也納的門戶開始,甚至也不再是從克拉根福開始。
在奧地利與曾是南斯拉夫的地方接壤的南部邊界,甚至火車一等包廂裡的供暖系統也被停止使用。餐車也被隔離開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鍍鋅的立式櫃檯,只供應啤酒、李子白蘭地、不帶過濾嘴的劣質煙捲兒。經過多次停靠站之後,指甲裡藏汙納垢的男人們擁擠到櫃檯前喝酒抽煙。不相互大聲說話或痛飲烈酒的時候,這些人則會靜悄悄地、專注地翻看色情雜誌。與他們在奧地利的同屬勞動階層的人們不同,他們沒有留男女皆宜的髮型,顯然他們在冬天來臨的時候也不指望去突尼斯或以色列度假。在這個地方,如果人們足夠幸運,擁有最起碼的本土文化保護上的一致性的話,那麼,自由党和祖國服務局的人很可能就會拋棄他們的現代藝術,拋棄那種認慫的做法,敢於直面一個記者的提問。(liv)
雪花落在了窗戶上。黑色的褐煤煙霧從磚和廢金屬搭成的煙囪裡冒了出來。這片土地就像是一個元氣耗盡、除了咳嗽就知道咒駡的妓女的臉,醜陋不堪而毫無生機。殘暴行為給這片水土留下的痕跡不難辨認:共產主義曾充當過它的不可一世的守護者。
因此,我不可能久留此地。不久,不論是九十年代末期,還是以後的數十年,整個畫面都將褪色,就像在克拉根福一樣,一切都已改變。(l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