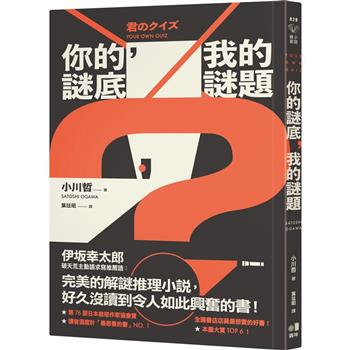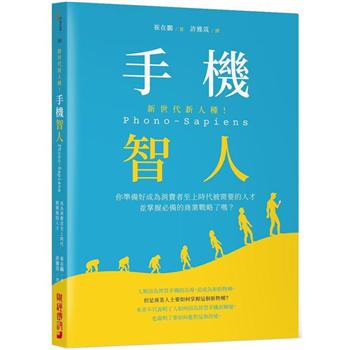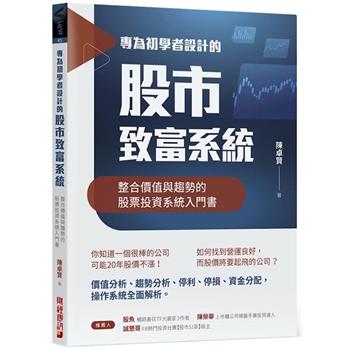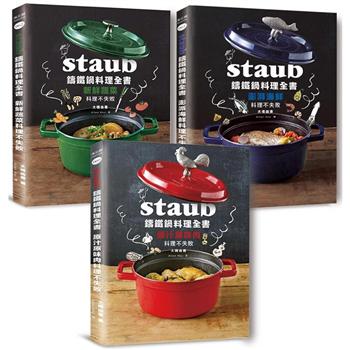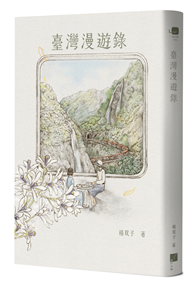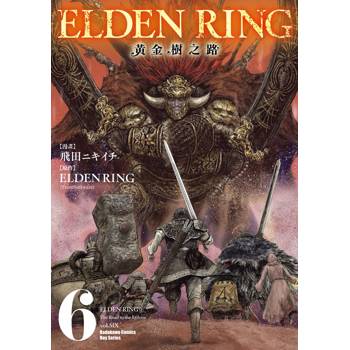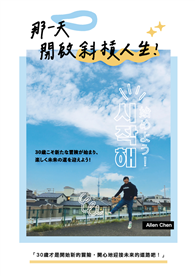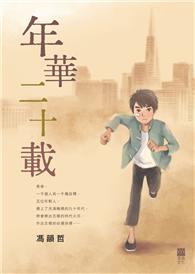近年來,關於性別、種族、宗教、地域等身份政治元素的討論逐漸佔據世界輿論場的中心,與此同時,道德審判又詭異地呈現出越發保守與嚴苛的面貌,仿佛在這個越發動蕩、危險的世界中,個體生命的尊嚴只能通過身份認同來彰顯。然而,身份政治已經逐漸顯露出它的後果——世界被撕裂成一座座孤島,人與人的聯結越發艱難;隨着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消費主義的無孔不入,信息與數據的過度生產和控制,我們被物化為無差別的慾望主體,一個符號,一串程序,甚至與他者的邊界都因同質化而顯得可疑:我們驚惶不安地想確認的不是“身份”,而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中的存在與位置;我們真正想守衛的不是一段關係,而是與真實的人類建立起的聯結。那麼,我們這些身份不明又一無所有的現代人,要如何找到自己,又該如何相愛呢?
“No woman is an island-ess.”克麗絲·克勞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傑出的示範。女性,藝術家,39歲,已婚,這是克麗絲的社會身份。在一次拜訪中,她瘋狂地愛上了丈夫的同事迪克,並開始和丈夫一起給迪克寫情書。“已婚夫婦會經常這樣為了寫情書而通力合作嗎?”“西爾維爾,這位教授普魯斯特的歐洲知識分子非常善於分析愛情的細枝末節。”作為丈夫,西爾維爾對自己進行了一場精神分析:“這是自去年夏天以來,克麗絲第一次這般興高采烈、情緒飽滿。既然他愛着克麗絲,就不忍心看到她傷心。也有可能是他正在寫的那本有關現代主義與納粹大屠殺的書遇到了瓶頸,或是對下個月即將重返教學工作感到恐懼。還有一種可能,他是個變態。”“艾瑪(西爾維爾將克麗絲比作包法利夫人)剛開始迷上你時,簡直是對我殘存自尊的嚴重打擊。我們的性生活又變得充滿活力,起因卻是一項全新的色情行為:給你寫信,迪克。每一封信不都是一封情書嗎?迪克,自從我開始給你寫信,我寫的都是情書啊。而我之前並不知道的是,這些情書其實是我寫給愛情的信,其實是我在靦腆地重新喚醒在相當壓抑的情感下休眠的力量。”
在給迪克寫情書的過程中,不僅是婚姻關係的雙方獲得了對愛情的別樣理解和久違的性生活,更重要的是,通過給迪克寫信,她逐漸意識到,迪克只是一個被用來投注愛意的對象,一個不重要的客體:“親愛的迪克,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殺了你。你變成了我‘親愛的日記’……”而這樣的迷戀,其實更像是一場實驗,一場案例研究:“相比遊戲,這更像是個項目。我在給你的那些信里寫下的每個字都是真心的,但同時,我開始將其看作一次最終能了解愛情和迷戀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她從中找到了作為抒情主體的“自我”:“誰應該有發言權,又是為什麼呢?這才是唯一的問題。”她的談論範圍從個人的感情擴大到自己的事業,擴展到對文學、藝術、哲學、精神分裂、女性主義等諸多領域,擴大到對他人與世界的關切:“如果因為女性囿於‘個人化’而未能創造出‘普世‘藝術,那為何不把“個人化”變得普世起來,使其成為我們藝術的主題呢?”有趣的是,克麗絲將這些書信寄給了迪克,並以這些為素材舉辦了一場展覽:“這些信件似乎開啟了一種新的文學類型,一種介於文化批評和虛構作品之間的文體。你曾經說過,你多麼希望按照這個思路來改造你們學校的寫作課程。你願意讓我在我明年3月的文化研究研討會上讀一段嗎?這似乎向著你所倡導的對抗性表演藝術前進了一步。”
而這本《我愛迪克》,便是這場展覽的文字版本,是克麗絲的精神自傳,同時,它也是一場抽象浪漫主義的愛情遊戲,一部革命性女性主義邪典小說,一冊20世紀文化批評研究合集,一本艾瑪·包法利自己寫的《包法利夫人》……克麗絲以如此自覺而健全的寫作提供了一種珍貴的想象:我們可以從慾望的海洋與數據的洪流中奪回身體和感知,重新成為一個“人”——“沒有什麼固定不變的自我,但它存在着,而借由寫作,你可以設法捕捉到自我的變化。”;並與其他“人”建立確鑿的聯結——“我們墜入愛河,是希望能把自己固定在對方身上,不再墜落。”
“迪克,我知道當你讀到這封信時,你會明白信中所述都是真的。你明白這個遊戲是真實的,或者說比現實更真實,比它所意指的一切都更真實。”“我愛迪克”,這是一句熾熱而坦蕩的單戀聲明,也是一場革新書信體的文學實驗,更是一份英勇的女性主義宣言——關於如何使用第一人稱來言說,以及女性如何重新生成她自己。
克麗絲·克勞斯(Chris Kraus,1955— ),美國作家、電影製片人、藝術家。生於紐約,童年在康涅狄格州和新西蘭度過,16歲即從新西蘭的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畢業,成為一名記者,21歲時返回紐約,進入導演李·布魯爾的工作室學習電影製作,拍攝了一系列實驗性電影和短片,在全球多個藝術展上放映。克麗絲·克勞斯已經出版了9本著作,現居洛杉磯,投身於各類藝術活動和社會活動。
譯者:李同洲,做過外國文學編輯,譯有《那兩個女孩》《阿爾戈》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