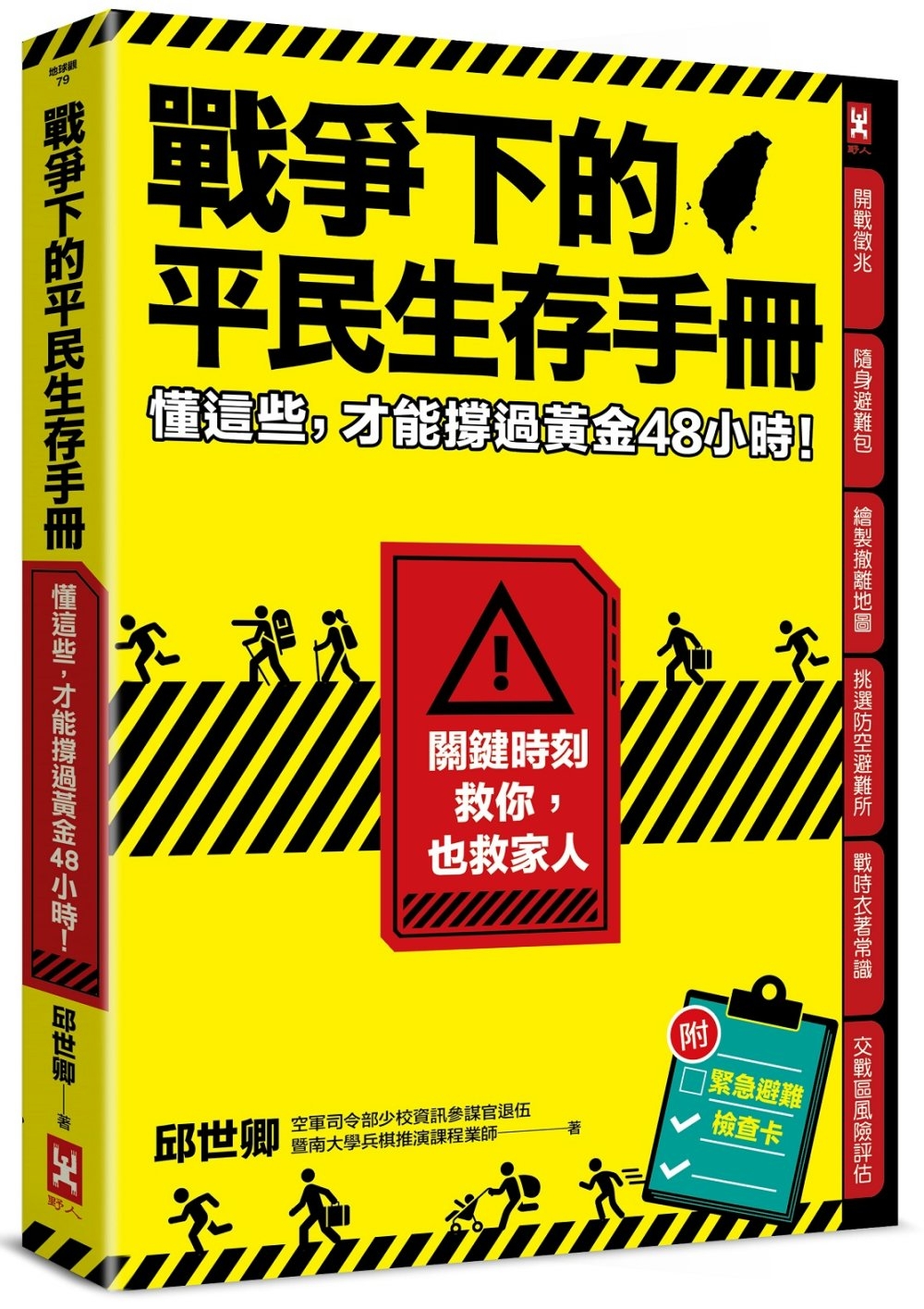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傲慢與偏見的圖書 |
 |
傲慢与偏见 作者:(英)简·奥斯丁著 / 譯者:王科一译 出版社:CNPeReading 出版日期:2018-04-01 語言:中文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傲慢與偏見
內容簡介
傲慢與偏見》是英國著名女作家簡‧奧斯丁的代表作。描寫傲慢的單身青年達西與偏見的二小姐伊麗莎白、富裕的單身貴族彬格萊與賢淑的大小姐吉英之間的感情糾葛,作品充分表達了作者本人的婚姻觀,強調經濟利益對人們戀愛和婚姻的影響。小說情節富有喜劇性,語言機智幽默,是奧斯丁小說中最受歡迎的一部,並被多次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
目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
序
關于簡‧奧斯丁,應該從哪兒說起呢?著名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有句名言說︰“在所有偉大作家當中,簡‧奧斯丁是最難在偉大的那一瞬間捉住的。”簡‧奧斯丁(1775—1817)生長于英國南部有文化教養的牧師家庭,本人一生四十多個年頭的歲月基本上是在英國的鄉間度過的,她的六部完整作品——《理智與情感》(1795)、《傲慢與偏見》(1796)、《諾桑覺寺》(1798)、《曼斯菲爾德莊園》(1812)、《愛瑪》(1814)、《勸導》(1816)——大都是描寫她自己熟悉的鄉間所謂體面人家的生活與交往,看來平凡而瑣碎。在她的六部小說中,沒有拜倫式慷慨激昂的抒發,也極少見驚心動魄的現實主義描寫。對于簡‧奧斯丁,要想捕捉她的“偉大”之所在,應從何處下手呢?她筆下那一場一場的舞會、一次一次的串門喝茶、一頓一頓的家宴和一桌一桌的紙牌,還有那些數不清的散步、閑談等如何能體現她的小說藝術的偉大呢?
評價奧斯丁,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題材問題。毫無疑問,奧斯丁是寫小題材的。據她自己說︰“鄉間村莊里的三四戶人家”是她“得心應手的好材料”。她還把自己的藝術比作在“兩寸象牙”上“細細地描畫”。這是奧斯丁在藝術上自覺的選擇。當有人建議她在創作上改換路子寫這寫那,她都婉言謝絕,堅持說︰“不,我必須保持自己的風格,按自己的方式寫下去……”
小天地可以反映出大問題。別小看“鄉間村莊里的三四戶人家”的家務事,英國社會的階級狀況和經濟關系盡在其中。至少在奧斯丁的作品里是如此。以《傲漫與偏見》為例,僅第二十九章羅新斯莊園的一次宴請和飯後的一桌牌就說明了多少問題。咖苔琳‧德‧包爾夫人僅憑自己的家產、地位便在柯林斯牧師夫婦面前那樣驕橫,柯林斯牧師竟對她那樣謙卑,他被邀請為夫人湊上一桌牌,便感到不勝榮幸,“他贏一次要謝她一次,如果贏得太多,還得向她道歉”。其實這不是一般的阿諛奉承問題。要知道,柯林斯教區牧師的職務是咖苔琳夫人提拔的,他視夫人為“施主”,當然不好意思再贏她的錢。這僅是個小小的細節,卻有趣地反映了當時教會對地產的依附。至于威廉‧盧卡斯爵士,既然本身已經封了爵位,何至于在牌桌上“不大說話,只顧把一樁樁軼事和一個個高貴的名字裝進腦子里去”?原來,他是在鎮上做生意起家的,曾在當市長的任內向國王獻過辭,從而獲得爵士頭餃。他是個商人變貴人的典型,骨子里還是個商人,難怪羨慕貴族,從莫里哀的茹爾丹先生以來就是如此,或許可追溯到更早的羅馬喜劇。再如,彬格萊先生和他的兩個姊妹出場不久,第四章便交代說,“她們出生于英格蘭北部的一個體面家族。她們對自己的出身記得很牢,可是卻幾乎忘了她們兄弟的財產以及她們自己的財產都是做生意賺來的”。對于細心的讀者,看到這“北部”一詞,就一目了然。杉格萊一家是在工業首先發達起來的北部發家致富的,這樣賺來的錢帶著銅臭氣,與貴族攀交的彬格萊小姐當然不願意正視它。這是當時普遍的階級心理。後來的蓋斯凱爾夫人在小說《北部與南部》中對照了農業的南部與工業的北部,更充分地描寫了發了財的北部企業家在文化教養上的欠缺與自卑。奧斯丁這里輕輕一筆帶過,起到了畫龍點晴的作用。
……
評價奧斯丁,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題材問題。毫無疑問,奧斯丁是寫小題材的。據她自己說︰“鄉間村莊里的三四戶人家”是她“得心應手的好材料”。她還把自己的藝術比作在“兩寸象牙”上“細細地描畫”。這是奧斯丁在藝術上自覺的選擇。當有人建議她在創作上改換路子寫這寫那,她都婉言謝絕,堅持說︰“不,我必須保持自己的風格,按自己的方式寫下去……”
小天地可以反映出大問題。別小看“鄉間村莊里的三四戶人家”的家務事,英國社會的階級狀況和經濟關系盡在其中。至少在奧斯丁的作品里是如此。以《傲漫與偏見》為例,僅第二十九章羅新斯莊園的一次宴請和飯後的一桌牌就說明了多少問題。咖苔琳‧德‧包爾夫人僅憑自己的家產、地位便在柯林斯牧師夫婦面前那樣驕橫,柯林斯牧師竟對她那樣謙卑,他被邀請為夫人湊上一桌牌,便感到不勝榮幸,“他贏一次要謝她一次,如果贏得太多,還得向她道歉”。其實這不是一般的阿諛奉承問題。要知道,柯林斯教區牧師的職務是咖苔琳夫人提拔的,他視夫人為“施主”,當然不好意思再贏她的錢。這僅是個小小的細節,卻有趣地反映了當時教會對地產的依附。至于威廉‧盧卡斯爵士,既然本身已經封了爵位,何至于在牌桌上“不大說話,只顧把一樁樁軼事和一個個高貴的名字裝進腦子里去”?原來,他是在鎮上做生意起家的,曾在當市長的任內向國王獻過辭,從而獲得爵士頭餃。他是個商人變貴人的典型,骨子里還是個商人,難怪羨慕貴族,從莫里哀的茹爾丹先生以來就是如此,或許可追溯到更早的羅馬喜劇。再如,彬格萊先生和他的兩個姊妹出場不久,第四章便交代說,“她們出生于英格蘭北部的一個體面家族。她們對自己的出身記得很牢,可是卻幾乎忘了她們兄弟的財產以及她們自己的財產都是做生意賺來的”。對于細心的讀者,看到這“北部”一詞,就一目了然。杉格萊一家是在工業首先發達起來的北部發家致富的,這樣賺來的錢帶著銅臭氣,與貴族攀交的彬格萊小姐當然不願意正視它。這是當時普遍的階級心理。後來的蓋斯凱爾夫人在小說《北部與南部》中對照了農業的南部與工業的北部,更充分地描寫了發了財的北部企業家在文化教養上的欠缺與自卑。奧斯丁這里輕輕一筆帶過,起到了畫龍點晴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