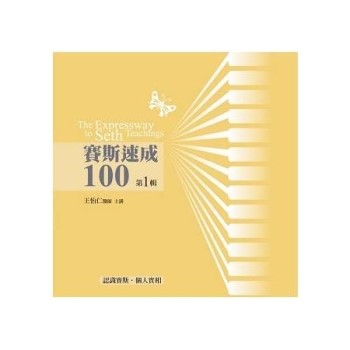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納博科夫精選集Ⅱ:防守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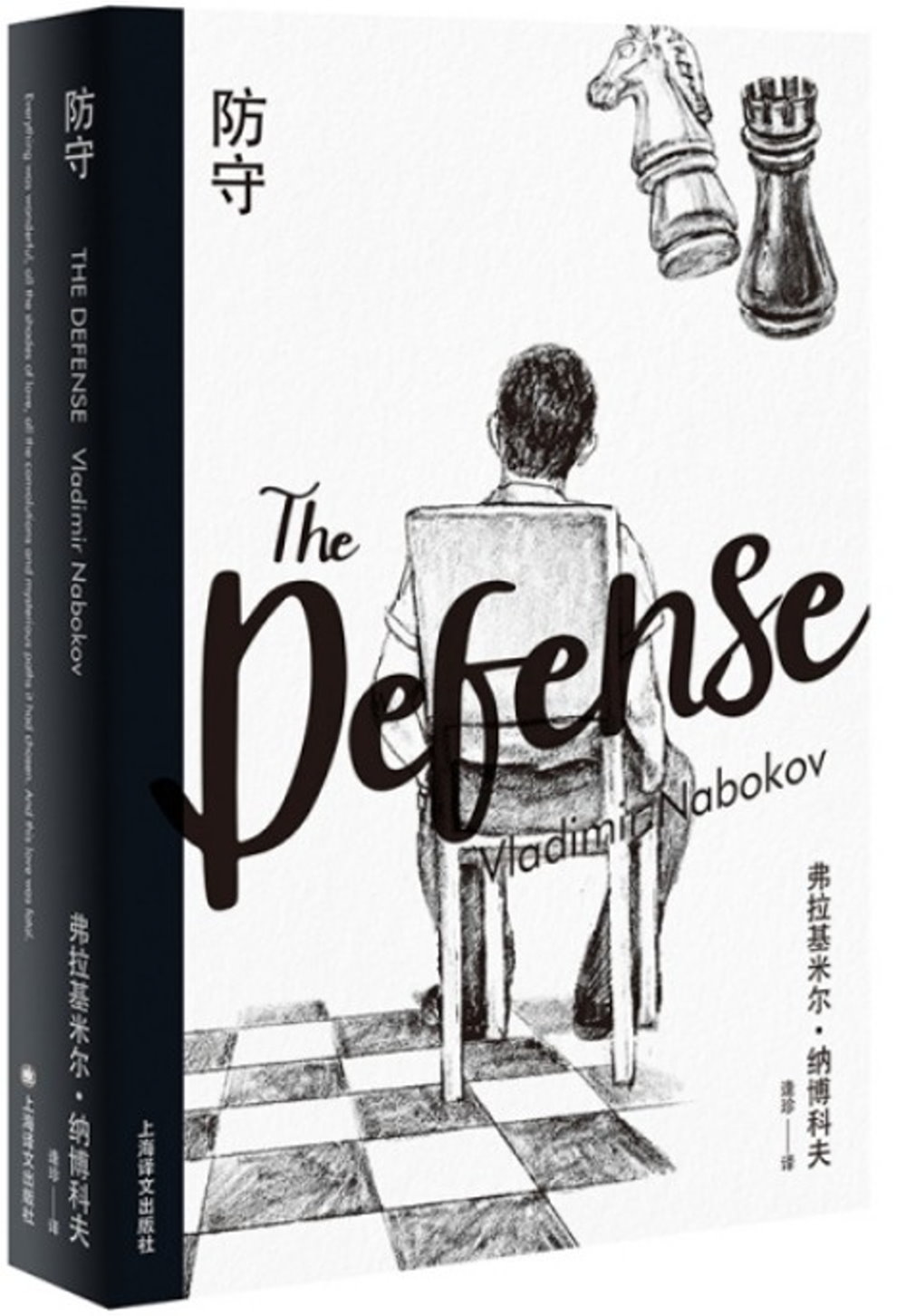 |
納博科夫精選集Ⅱ:防守 作者:(美)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8-01 語言:簡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72頁 / 32k/ 13 x 19 x 1.36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納博科夫精選集Ⅱ:防守
內容簡介
《防守》是二十世紀公認的小說大師納博科夫長篇小說代表作,講述一個天才少年由於長期沉溺於棋局而逐漸精神失常的故事,激情、迷醉、瘋狂和隕落是貫穿整部小說的旋律。主人公盧仁小時候是個不引人注目、性格孤僻憂鬱的孩子,現實生活總是讓他感到焦慮,於是他把象棋作為逃避現實生活的避難所。事實證明,他是個象棋天才,並一躍成為象棋大師。然而,他也為此付出了代價:棋局漸漸取代了他的現實生活,真實的生活反而成了夢境。納博科夫在這部早年作品中傾注了巨大的熱情,以解剖學般的精准筆法勾勒出天才光環背後的隱秘角落。
作者介紹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1899-1977)
納博科夫是二十世紀公認的傑出小說家和文體家。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納博科夫出生於聖彼德堡。布爾什維克革命期間,納博科夫隨全家於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國。他在劍橋三一學院攻讀法國和俄羅斯文學後,開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學生涯。一九四〇年,納博科夫移居美國,在威爾斯利、斯坦福、康奈爾和哈佛大學執教,以小說家、詩人、批評家和翻譯家的身份享譽文壇,著有《庶出的標誌》《洛麗塔》《普寧》和《微暗的火》等長篇小說。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納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麗塔》由巴黎奧林匹亞出版社出版並引發爭議。一九六一年,納博科夫遷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
納博科夫是二十世紀公認的傑出小說家和文體家。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納博科夫出生於聖彼德堡。布爾什維克革命期間,納博科夫隨全家於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國。他在劍橋三一學院攻讀法國和俄羅斯文學後,開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學生涯。一九四〇年,納博科夫移居美國,在威爾斯利、斯坦福、康奈爾和哈佛大學執教,以小說家、詩人、批評家和翻譯家的身份享譽文壇,著有《庶出的標誌》《洛麗塔》《普寧》和《微暗的火》等長篇小說。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納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麗塔》由巴黎奧林匹亞出版社出版並引發爭議。一九六一年,納博科夫遷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
序
前言
這部小說的俄文書名是Zashchita Luzhina,意思是“盧仁防守”,指的是國際象棋中的一種防守技巧,這種技巧可以說是我在這部小說中創造的主人公盧仁大師發明的。盧仁這個名字的發音,如果把“u”拖長一些發成“oo”,就和“illusion”一詞同韻。早在一九二九年春,我就開始寫這部小說了。當時我在法國東比利牛斯省的一個溫泉小鎮勒布魯療養,常在那一帶捕捉蝴蝶。同年在柏林完成創作。當時的情景我記得特別清晰,長滿荊豆和冬青的山間有一塊斜面岩石,這部小說的主題構思最初就是在那兒形成的。假如當時認真地多想想的話,說不定會有進一步的奇思妙想。
Zashchita Luzhina刊登在俄文流亡者季刊《現代紀事》(巴黎)上,用的是我的筆名“弗•西林”,之後立即由流亡者主辦的斯洛弗出版社出版(柏林,一九三○年)。紙面平裝本,二百三十四頁,長二十一釐米,寬十四釐米,純黑色的護封,燙金書名。這個版本現在很難見到,可能會越來越少。
可憐的盧仁不得不等待三十五年才出了一個英文本。不錯,三十年代後期有個美國出版商對該書表示過興趣,刮了一陣要出英文本的風。但是後來證明,這位出版商原是那種夢想控制作家藝術靈感的人。他建議我用音樂取代象棋,把盧仁寫成一個發狂的小提琴家,這樣我們短暫的合作也就草草收場了。
今天重讀這部小說,重溫其故事情節,我頗有點安德森[注:Karl Ernst Adolf Anderssen (1818—1879),德國著名國際象棋棋手,號稱無冕之王。一八五一年在倫敦執白對萊昂內爾•基耶塞裡茨基,中局連棄雙車取勝,後世將此局譽為“安德森的不朽之局”。基耶塞裡茨基(Lionel Adalhert Bagration Felix Kieseritsky, 1806—1853)為愛沙尼亞著名國際象棋棋手,一八三九年赴法國教授象棋並以下收費棋謀生。]回顧他那盤得意棋局的感覺。他向時運不濟而又高傲的基耶塞裡茨基連棄雙車,基耶塞裡茨基在後世無數的棋譜裡帶著永遠的疑問反復遭此棄子攻殺。我的故事不好寫,但我非常樂意利用這樣或那樣的形象和這樣或那樣的場景,為盧仁的生活構建一種致命的模式。
我寫了一座花園,寫了一次旅行,還寫了一系列的無聊瑣事,都帶著技能比賽的味道。尤其是最後幾章,用一著正規的象棋攻殺的形式,瓦解了那個可憐人最深處的一點理智。說到這裡,我想為那些為賺錢而寫評論的人省些時間和氣力。這些人看書一般都是邊看邊念,遇到一部對話不多的小說時,只要能從《前言》中撿到夠用的資訊,就別指望他們認真讀完全書。所以我不妨提醒他們注意磨砂玻璃窗意象(這個意象與盧仁的自殺有關,更確切地說是與他的“自將”有關),它要到第十一章時才首次出現。或者請他們注意我筆下這位悶悶不樂的大師回憶他下棋之旅時的感傷方式,他想起的不是淺橘紅色的行李標籤和幻燈演示片,而是不同的旅館衛生間和走廊公共盥洗室裡的瓷磚——那些呈藍白相間的方格的地面,他坐在寶座般的坐便器上,垂眼一望,想像中便出現了酣戰中的棋局;要麼是鋪在羅丹的雕塑《思想者》和房門之間的亞麻地毯上故意排得不對稱的圖案,市場上稱為“瑪瑙彩”,按著馬一步三彩格的樣式在這裡或那裡破壞著地毯灰色的底色,不然還是挺規則的方格;要麼是一些又大又光的黑黃色相間的長方形,它們的H形縱列被熱水管這條黃褐色垂直線無情地截斷;要麼是那個豪華衛生間,他從漂亮的大理石地板上認出了一個完整而朦朧的棋局,佈局和多年前一天夜裡他拳頭支著下巴沉思過的一模一樣。不過我設置的象棋效應不光出現在這些獨立的場景中,在這部引人入勝的小說的基本結構中也能找到象棋效應的連鎖反應。
於是在第四章快結束時,我在棋盤的一角走出了意想不到的一步,十六年的歲月用一段文字一筆帶過,盧仁突然長成一個邋遢的中年人,到了德國的一個旅遊勝地。讀者在一張花園小桌旁發現了他,他正用手杖指著一扇他想起來的旅館窗戶(不是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塊玻璃方格)同一個人說話。從放在鐵桌上的坤包可以斷定這是個女人,但直到第六章我們才會見著她。這時從第四章開始的往事回憶逐漸集中在盧仁已故的父親身上,第五章中專寫他的過去。寫到他時,讀者可以看出他一面回憶兒子早期的象棋經歷,一面在自己頭腦中將其程式化,好把它編造成一個青少年感傷故事。到第六章,我們轉回庫爾豪斯,發現盧仁還在擺弄那只坤包,還在同他那位讀者尚未看清的夥伴說話。這時讀者看清了她,她從他手中拿回坤包,說了老盧仁的去世,她也就成為小說佈局的要緊部分。這三個中心章節的整體部署使人想起——或者說應當使人想起——某種象棋難題,其要點不僅僅是通過這麼多步將死對方,還要有一個被稱為“逆向分析”的過程,其要求是根據當前態勢圖進行複盤研究,證明黑方剛走的這一步不可能是王車易位,或者肯定是吃了白方的過路兵。
在這篇只作初步介紹的《前言》中,沒有必要多談棋子和攻防策略方面更為複雜的問題。不過有一點必須說明,在我的所有俄語書中,《防守》包含、散發著最大的“熱情”——鑒於想像中象棋是種玄而又玄的東西,說“飽含熱情”也許不合常理。事實上,即便是那些對國際象棋一竅不通的人或者對我的其他作品一概憎惡的人,也素來認為盧仁很可愛。他笨拙、邋遢、不合時宜——但正如我筆下那位溫柔的小姐(一位當之無愧的好姑娘)很快注意到的那樣,儘管盧仁皮膚灰白粗糙,深藏的天賦不為人知,但他的確有不可貌相之處。
我的俄文小說陸續出了一些英文版本(還會再出一些),在我最近為這些英文版本寫的前言中已經形成了一條規則,那就是對維也納學派說幾句鼓勵的話。手頭這篇前言也不會例外。我希望,精神分析學家和接受精神分析的人都能欣賞盧仁精神崩潰後接受治療的具體方法(比如暗示療法,即暗示棋手把自己的“後”看成媽媽,把對方的“王”看成爸爸)。佛洛德學派的小後生將開鎖的玩具裝置當成瞭解讀小說的真正鑰匙,他們毫無疑問會繼續把我的父母、我的情人和一連串的我自己漫畫化,並將我筆下的人物和這些漫畫形象等同起來。為了讓這些偵探進展順利,我不如現在就承認,我把我的法語女家教、我的袖珍象棋、我的好脾氣和我在自家有圍牆的花園裡拾到的桃核統統賦予了我筆下的盧仁。
弗•納博科夫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于蒙特勒
這部小說的俄文書名是Zashchita Luzhina,意思是“盧仁防守”,指的是國際象棋中的一種防守技巧,這種技巧可以說是我在這部小說中創造的主人公盧仁大師發明的。盧仁這個名字的發音,如果把“u”拖長一些發成“oo”,就和“illusion”一詞同韻。早在一九二九年春,我就開始寫這部小說了。當時我在法國東比利牛斯省的一個溫泉小鎮勒布魯療養,常在那一帶捕捉蝴蝶。同年在柏林完成創作。當時的情景我記得特別清晰,長滿荊豆和冬青的山間有一塊斜面岩石,這部小說的主題構思最初就是在那兒形成的。假如當時認真地多想想的話,說不定會有進一步的奇思妙想。
Zashchita Luzhina刊登在俄文流亡者季刊《現代紀事》(巴黎)上,用的是我的筆名“弗•西林”,之後立即由流亡者主辦的斯洛弗出版社出版(柏林,一九三○年)。紙面平裝本,二百三十四頁,長二十一釐米,寬十四釐米,純黑色的護封,燙金書名。這個版本現在很難見到,可能會越來越少。
可憐的盧仁不得不等待三十五年才出了一個英文本。不錯,三十年代後期有個美國出版商對該書表示過興趣,刮了一陣要出英文本的風。但是後來證明,這位出版商原是那種夢想控制作家藝術靈感的人。他建議我用音樂取代象棋,把盧仁寫成一個發狂的小提琴家,這樣我們短暫的合作也就草草收場了。
今天重讀這部小說,重溫其故事情節,我頗有點安德森[注:Karl Ernst Adolf Anderssen (1818—1879),德國著名國際象棋棋手,號稱無冕之王。一八五一年在倫敦執白對萊昂內爾•基耶塞裡茨基,中局連棄雙車取勝,後世將此局譽為“安德森的不朽之局”。基耶塞裡茨基(Lionel Adalhert Bagration Felix Kieseritsky, 1806—1853)為愛沙尼亞著名國際象棋棋手,一八三九年赴法國教授象棋並以下收費棋謀生。]回顧他那盤得意棋局的感覺。他向時運不濟而又高傲的基耶塞裡茨基連棄雙車,基耶塞裡茨基在後世無數的棋譜裡帶著永遠的疑問反復遭此棄子攻殺。我的故事不好寫,但我非常樂意利用這樣或那樣的形象和這樣或那樣的場景,為盧仁的生活構建一種致命的模式。
我寫了一座花園,寫了一次旅行,還寫了一系列的無聊瑣事,都帶著技能比賽的味道。尤其是最後幾章,用一著正規的象棋攻殺的形式,瓦解了那個可憐人最深處的一點理智。說到這裡,我想為那些為賺錢而寫評論的人省些時間和氣力。這些人看書一般都是邊看邊念,遇到一部對話不多的小說時,只要能從《前言》中撿到夠用的資訊,就別指望他們認真讀完全書。所以我不妨提醒他們注意磨砂玻璃窗意象(這個意象與盧仁的自殺有關,更確切地說是與他的“自將”有關),它要到第十一章時才首次出現。或者請他們注意我筆下這位悶悶不樂的大師回憶他下棋之旅時的感傷方式,他想起的不是淺橘紅色的行李標籤和幻燈演示片,而是不同的旅館衛生間和走廊公共盥洗室裡的瓷磚——那些呈藍白相間的方格的地面,他坐在寶座般的坐便器上,垂眼一望,想像中便出現了酣戰中的棋局;要麼是鋪在羅丹的雕塑《思想者》和房門之間的亞麻地毯上故意排得不對稱的圖案,市場上稱為“瑪瑙彩”,按著馬一步三彩格的樣式在這裡或那裡破壞著地毯灰色的底色,不然還是挺規則的方格;要麼是一些又大又光的黑黃色相間的長方形,它們的H形縱列被熱水管這條黃褐色垂直線無情地截斷;要麼是那個豪華衛生間,他從漂亮的大理石地板上認出了一個完整而朦朧的棋局,佈局和多年前一天夜裡他拳頭支著下巴沉思過的一模一樣。不過我設置的象棋效應不光出現在這些獨立的場景中,在這部引人入勝的小說的基本結構中也能找到象棋效應的連鎖反應。
於是在第四章快結束時,我在棋盤的一角走出了意想不到的一步,十六年的歲月用一段文字一筆帶過,盧仁突然長成一個邋遢的中年人,到了德國的一個旅遊勝地。讀者在一張花園小桌旁發現了他,他正用手杖指著一扇他想起來的旅館窗戶(不是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塊玻璃方格)同一個人說話。從放在鐵桌上的坤包可以斷定這是個女人,但直到第六章我們才會見著她。這時從第四章開始的往事回憶逐漸集中在盧仁已故的父親身上,第五章中專寫他的過去。寫到他時,讀者可以看出他一面回憶兒子早期的象棋經歷,一面在自己頭腦中將其程式化,好把它編造成一個青少年感傷故事。到第六章,我們轉回庫爾豪斯,發現盧仁還在擺弄那只坤包,還在同他那位讀者尚未看清的夥伴說話。這時讀者看清了她,她從他手中拿回坤包,說了老盧仁的去世,她也就成為小說佈局的要緊部分。這三個中心章節的整體部署使人想起——或者說應當使人想起——某種象棋難題,其要點不僅僅是通過這麼多步將死對方,還要有一個被稱為“逆向分析”的過程,其要求是根據當前態勢圖進行複盤研究,證明黑方剛走的這一步不可能是王車易位,或者肯定是吃了白方的過路兵。
在這篇只作初步介紹的《前言》中,沒有必要多談棋子和攻防策略方面更為複雜的問題。不過有一點必須說明,在我的所有俄語書中,《防守》包含、散發著最大的“熱情”——鑒於想像中象棋是種玄而又玄的東西,說“飽含熱情”也許不合常理。事實上,即便是那些對國際象棋一竅不通的人或者對我的其他作品一概憎惡的人,也素來認為盧仁很可愛。他笨拙、邋遢、不合時宜——但正如我筆下那位溫柔的小姐(一位當之無愧的好姑娘)很快注意到的那樣,儘管盧仁皮膚灰白粗糙,深藏的天賦不為人知,但他的確有不可貌相之處。
我的俄文小說陸續出了一些英文版本(還會再出一些),在我最近為這些英文版本寫的前言中已經形成了一條規則,那就是對維也納學派說幾句鼓勵的話。手頭這篇前言也不會例外。我希望,精神分析學家和接受精神分析的人都能欣賞盧仁精神崩潰後接受治療的具體方法(比如暗示療法,即暗示棋手把自己的“後”看成媽媽,把對方的“王”看成爸爸)。佛洛德學派的小後生將開鎖的玩具裝置當成瞭解讀小說的真正鑰匙,他們毫無疑問會繼續把我的父母、我的情人和一連串的我自己漫畫化,並將我筆下的人物和這些漫畫形象等同起來。為了讓這些偵探進展順利,我不如現在就承認,我把我的法語女家教、我的袖珍象棋、我的好脾氣和我在自家有圍牆的花園裡拾到的桃核統統賦予了我筆下的盧仁。
弗•納博科夫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于蒙特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