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納博科夫精選集Ⅱ:瑪麗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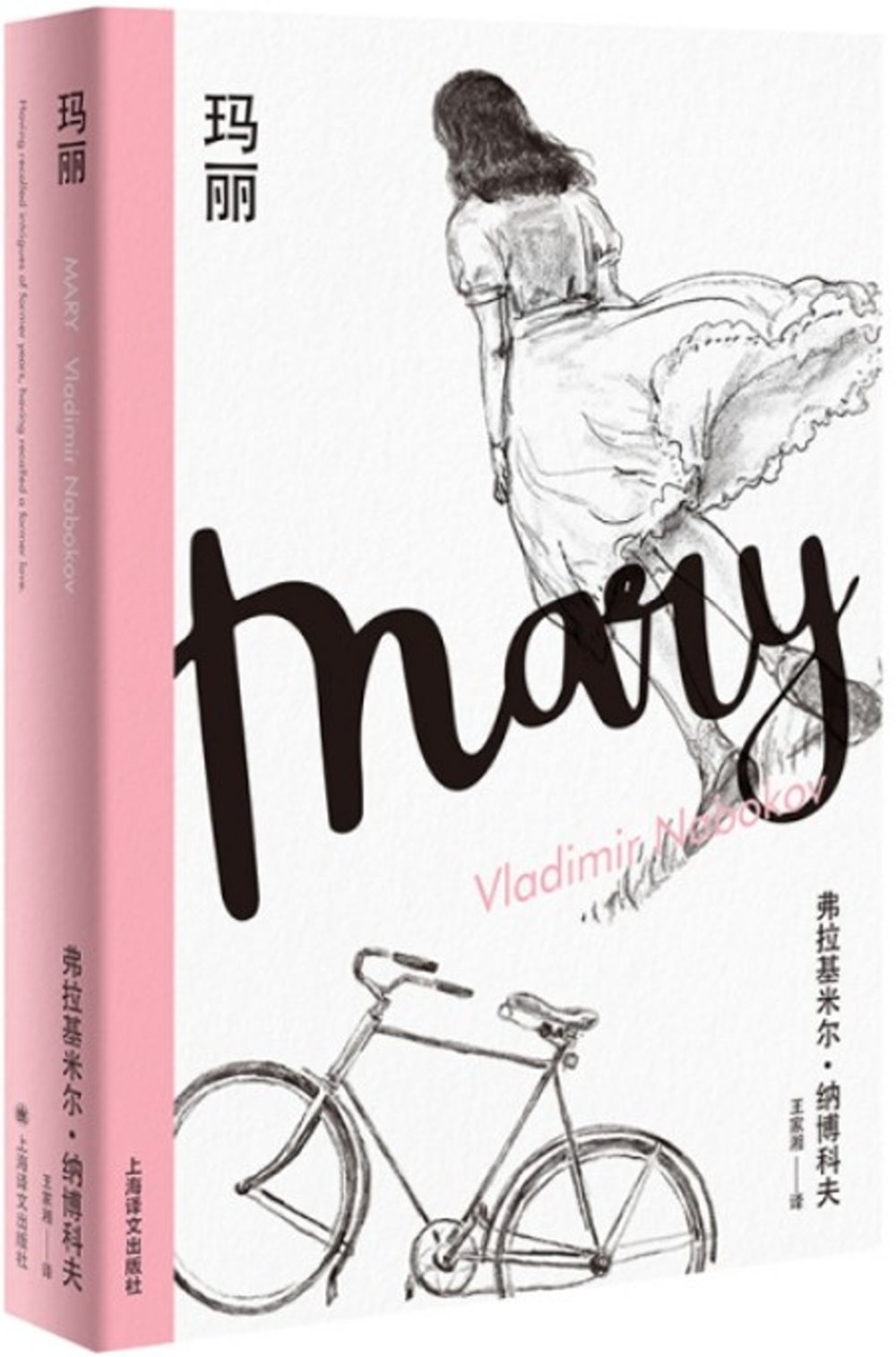 |
納博科夫精選集Ⅱ:瑪麗 作者:(美)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8-01 語言:簡體中文 規格:平裝 / 146頁 / 32k/ 13 x 19 x 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納博科夫精選集Ⅱ:瑪麗
內容簡介
《瑪麗》是二十世紀公認的小說大師納博科夫第一部長篇小說,對作者本人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由於俄國非同一般地遙遠,由於思鄉在人的一生中始終是你癡迷的伴侶……我承認自己對這部處女作在情感上的強烈依戀,絲毫不為之感到困窘。”柏林的俄國軍官加甯從鄰居的一張照片中偶然發現,鄰居正在等待的妻子瑪麗,原來是他中學時代的初戀情人;而後的幾天裡,加寧不斷追憶與戀人度過的美好往昔,於是將鄰居的鬧鐘撥慢,代替他去接瑪麗,期望重敘舊情……作者以極敏銳的感受力和細膩筆觸,將對初戀和故國的懷念展現到了極致。俄羅斯的廣袤原野、秋陽、冷雨、白樺、冬雪,在記憶的明亮迷宮中映照著往日時光。
作者介紹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1899-1977)
納博科夫是二十世紀公認的傑出小說家和文體家。 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納博科夫出生於聖彼德堡。布爾什維克革命期間,納博科夫隨全家於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國。他在劍橋三一學院攻讀法國和俄羅斯文學後,開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學生涯。 一九四〇年,納博科夫移居美國,在威爾斯利、斯坦福、康奈爾和哈佛大學執教,以小說家、詩人、批評家和翻譯家的身份享譽文壇,著有《庶出的標誌》《洛麗塔》《普寧》和《微暗的火》等長篇小說。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納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麗塔》由巴黎奧林匹亞出版社出版並引發爭議。 一九六一年,納博科夫遷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
納博科夫是二十世紀公認的傑出小說家和文體家。 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納博科夫出生於聖彼德堡。布爾什維克革命期間,納博科夫隨全家於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國。他在劍橋三一學院攻讀法國和俄羅斯文學後,開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學生涯。 一九四〇年,納博科夫移居美國,在威爾斯利、斯坦福、康奈爾和哈佛大學執教,以小說家、詩人、批評家和翻譯家的身份享譽文壇,著有《庶出的標誌》《洛麗塔》《普寧》和《微暗的火》等長篇小說。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納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麗塔》由巴黎奧林匹亞出版社出版並引發爭議。 一九六一年,納博科夫遷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
序
前言
眼前這部小說的俄文書名《瑪申卡》(Mashenka)——“瑪麗亞”(Maria)的次派生昵稱——幾乎無法合理地音譯出來(重音在第一個帶“a”的、讀音和在“ask”中的“a”一樣的音節上,再加上一個像在“mignon”裡的讀音齶音化的“n”)。在尋找一個適當的替代名(Mariette?抑或May?)的時候,我決定用《瑪麗》(Mary),這個名字似乎和俄文書名所具有的自然純真最相匹配。
《瑪申卡》是我的第一部小說。我是在柏林開始寫這本書的,那是一九二五年春我結婚後不久,到次年年初完成,由一家流亡者圖書公司出版(斯洛弗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六)。兩年後出了德文版(烏爾施泰因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八),我沒有讀過。除此之外,在長達四十五年之久令人難忘的時間裡,沒有再出現譯本。
眾所周知,初次進行創作的人具有把自己的經歷寫進作品的強烈傾向,他把自己或者一個替代者放進他的第一部小說中,這樣做與其說是由於現成題材的吸引力,不如說是為了擺脫自我後可以去輕裝從事更美好的事情。這是我接受的極少數的一般規則之一。我的《說吧,記憶》(始於一九四○年代)的讀者不可能不注意到,我的回憶和加寧的回憶之間有著某些相同之處。他的瑪麗和我的塔瑪拉是孿生姐妹,都有祖傳的林陰道,奧列傑日河流淌在兩本書中,今天的羅日斯特維諾的宅子的照片——非常漂亮地翻印在企鵝版(《說吧,記憶》,一九六九)的封面上——簡直就是小說中“沃斯克列辛斯克”那座有廊柱的宅子的照片。當我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後寫自傳第十二章的時候,並沒有查看《瑪申卡》;而現在當我查看了以後,這個事實讓我著迷:儘管有添加上去的虛構成分(例如和村子裡的小流氓打架,或在無名小鎮螢火蟲間的幽會),在浪漫化了的作品中,比在自傳作者的一絲不苟的忠實敘述中,包含著更為濃烈的個人現實的精華。起初,我不明白怎麼可能這樣:在很不容易地安排情節和誇耀地虛構人物(甚至很笨拙地讓兩個人物出現在瑪麗的信裡)的同時,怎麼還能保留住自己的經歷中那激動人心之處,以及那悅人的氣氛;我感到特別難以相信的是,文學中的模仿竟能和純粹的真實相爭。但是解釋起來其實很簡單:和《說吧,記憶》裡的我相比,加寧距離他的過去,比我要近三倍。
由於俄國非同一般地遙遠,由於思鄉在人的一生中始終是你癡迷的伴侶,我已習慣於在公眾場合忍受這個伴侶的令人斷腸的怪癖,我承認自己對這部處女作在情感上的強烈依戀,絲毫不為之感到困窘。它的瑕疵是無知和缺乏經驗的產物,任何一個評論家都能夠很容易地開著玩笑就列出表來,但是對我(在這個案件和法庭上的惟一法官)來說,裡面的幾個場景抵消了所有的瑕疵(養病,穀倉音樂會,划船);如果我當時想到了的話,就會把這些場景完整地移到後來的作品中去。與葛籣尼先生的合作之初我就意識到,我們的翻譯應該忠實于原先的文本,就和翻譯不是我的文本時我會堅持的那樣忠實。我在比如像把俄文原著英譯成為King, Queen, Knave(《王,後,傑克》)這樣一本書的時候所使用的輕浮專橫式修改翻新,在這裡是無法想像的。我認為惟一需要作出調整的,僅限於在那麼三四段中暗指俄國慣常事務的簡短的詞語(對於同為流亡者的人是很清楚的,但對於外國讀者是無法理解的),以及把加寧按儒略曆計算的日期改為按通用的西曆計算(比如他的七月底是我們八月的第二周,等等)。
我必須以下面的囑咐來結束這篇序言。正如我在《時尚》的一次採訪(一九七○年)中回答艾倫.•.塔爾梅提出的問題時所說:“一個作家的傳記中最精彩的部分不是他的異乎尋常的經歷的記錄,而是具有他的風格的故事。只有從這個角度,人們才能恰當地評價我的第一個女主人公和最近的阿達之間的關係,如果有關係的話。”我不妨說,她們之間沒有任何關係。我另外的話和仍舊在某些人士中受到吹捧的一個偽信條有關。儘管一個傻瓜會爭辯說orange是organe的夢幻般的變換字母順序的變音詞[注:orange這個英文字義為“橘子”,而organe是法文字,是“器官”的意思,婉意為“陰莖”],我還是勸維也納代表團[注:Viennese delegation,指佛洛德精神分析學派理論的追隨者;佛洛德是奧地利人]的成員們,不要把寶貴的時間花費在分析本書第四章結尾處克拉拉做的夢上。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一九七○年一月九日
眼前這部小說的俄文書名《瑪申卡》(Mashenka)——“瑪麗亞”(Maria)的次派生昵稱——幾乎無法合理地音譯出來(重音在第一個帶“a”的、讀音和在“ask”中的“a”一樣的音節上,再加上一個像在“mignon”裡的讀音齶音化的“n”)。在尋找一個適當的替代名(Mariette?抑或May?)的時候,我決定用《瑪麗》(Mary),這個名字似乎和俄文書名所具有的自然純真最相匹配。
《瑪申卡》是我的第一部小說。我是在柏林開始寫這本書的,那是一九二五年春我結婚後不久,到次年年初完成,由一家流亡者圖書公司出版(斯洛弗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六)。兩年後出了德文版(烏爾施泰因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八),我沒有讀過。除此之外,在長達四十五年之久令人難忘的時間裡,沒有再出現譯本。
眾所周知,初次進行創作的人具有把自己的經歷寫進作品的強烈傾向,他把自己或者一個替代者放進他的第一部小說中,這樣做與其說是由於現成題材的吸引力,不如說是為了擺脫自我後可以去輕裝從事更美好的事情。這是我接受的極少數的一般規則之一。我的《說吧,記憶》(始於一九四○年代)的讀者不可能不注意到,我的回憶和加寧的回憶之間有著某些相同之處。他的瑪麗和我的塔瑪拉是孿生姐妹,都有祖傳的林陰道,奧列傑日河流淌在兩本書中,今天的羅日斯特維諾的宅子的照片——非常漂亮地翻印在企鵝版(《說吧,記憶》,一九六九)的封面上——簡直就是小說中“沃斯克列辛斯克”那座有廊柱的宅子的照片。當我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後寫自傳第十二章的時候,並沒有查看《瑪申卡》;而現在當我查看了以後,這個事實讓我著迷:儘管有添加上去的虛構成分(例如和村子裡的小流氓打架,或在無名小鎮螢火蟲間的幽會),在浪漫化了的作品中,比在自傳作者的一絲不苟的忠實敘述中,包含著更為濃烈的個人現實的精華。起初,我不明白怎麼可能這樣:在很不容易地安排情節和誇耀地虛構人物(甚至很笨拙地讓兩個人物出現在瑪麗的信裡)的同時,怎麼還能保留住自己的經歷中那激動人心之處,以及那悅人的氣氛;我感到特別難以相信的是,文學中的模仿竟能和純粹的真實相爭。但是解釋起來其實很簡單:和《說吧,記憶》裡的我相比,加寧距離他的過去,比我要近三倍。
由於俄國非同一般地遙遠,由於思鄉在人的一生中始終是你癡迷的伴侶,我已習慣於在公眾場合忍受這個伴侶的令人斷腸的怪癖,我承認自己對這部處女作在情感上的強烈依戀,絲毫不為之感到困窘。它的瑕疵是無知和缺乏經驗的產物,任何一個評論家都能夠很容易地開著玩笑就列出表來,但是對我(在這個案件和法庭上的惟一法官)來說,裡面的幾個場景抵消了所有的瑕疵(養病,穀倉音樂會,划船);如果我當時想到了的話,就會把這些場景完整地移到後來的作品中去。與葛籣尼先生的合作之初我就意識到,我們的翻譯應該忠實于原先的文本,就和翻譯不是我的文本時我會堅持的那樣忠實。我在比如像把俄文原著英譯成為King, Queen, Knave(《王,後,傑克》)這樣一本書的時候所使用的輕浮專橫式修改翻新,在這裡是無法想像的。我認為惟一需要作出調整的,僅限於在那麼三四段中暗指俄國慣常事務的簡短的詞語(對於同為流亡者的人是很清楚的,但對於外國讀者是無法理解的),以及把加寧按儒略曆計算的日期改為按通用的西曆計算(比如他的七月底是我們八月的第二周,等等)。
我必須以下面的囑咐來結束這篇序言。正如我在《時尚》的一次採訪(一九七○年)中回答艾倫.•.塔爾梅提出的問題時所說:“一個作家的傳記中最精彩的部分不是他的異乎尋常的經歷的記錄,而是具有他的風格的故事。只有從這個角度,人們才能恰當地評價我的第一個女主人公和最近的阿達之間的關係,如果有關係的話。”我不妨說,她們之間沒有任何關係。我另外的話和仍舊在某些人士中受到吹捧的一個偽信條有關。儘管一個傻瓜會爭辯說orange是organe的夢幻般的變換字母順序的變音詞[注:orange這個英文字義為“橘子”,而organe是法文字,是“器官”的意思,婉意為“陰莖”],我還是勸維也納代表團[注:Viennese delegation,指佛洛德精神分析學派理論的追隨者;佛洛德是奧地利人]的成員們,不要把寶貴的時間花費在分析本書第四章結尾處克拉拉做的夢上。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一九七○年一月九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