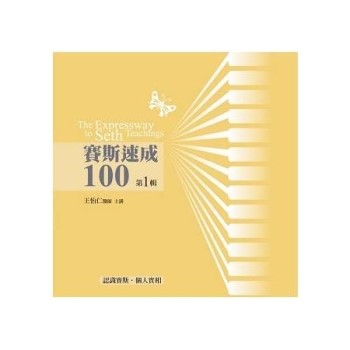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納博科夫精選集Ⅱ:眼睛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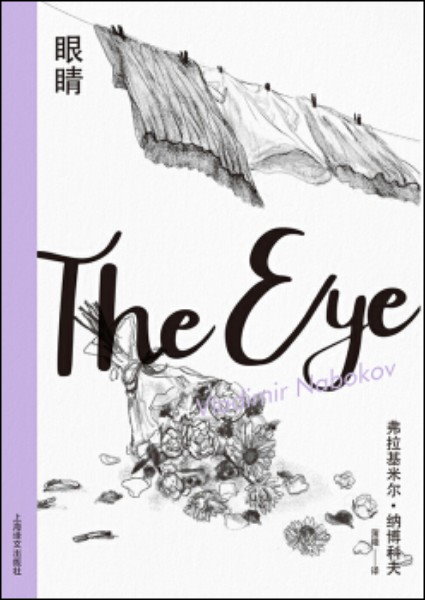 |
納博科夫精選集Ⅱ:眼睛 作者:(美)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8-01 語言:簡體中文 規格:平裝 / 110頁 / 32k/ 13 x 19 x 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納博科夫精選集Ⅱ:眼睛
內容簡介
《眼睛》是二十世紀公認的小說大師納博科夫的長篇代表作,戲擬偵探小說的筆法,講述了主人公斯穆羅夫的一生。斯穆羅夫以觀察、刺探、審視自己和別人為樂,由於他的身份特殊,只是通過別人的眼睛來看自己、觀察別人,並且保護自己的身份不被識破。而他的存在永遠只取決於別人頭腦中的反映:一個騙子,一個殘暴的軍官,一個敏感的小夥子,一個體面的紳士,或是一個愛而不得的可憐人。作者以雨滴般晶瑩的密碼文字編織出奇妙的多重世界,將讀者帶入敘事迷宮,追蹤斯穆羅夫的真實身份,分析背後那位神秘的敘事者的意圖,並從中體驗解謎探案般的快感——“不做別的,只做一隻略帶玻璃色的,有點兒充血的,一眨也不眨的大眼睛”。
作者介紹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1899-1977)
納博科夫是二十世紀公認的傑出小說家和文體家。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納博科夫出生於聖彼德堡。布爾什維克革命期間,納博科夫隨全家於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國。他在劍橋三一學院攻讀法國和俄羅斯文學後,開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學生涯。一九四〇年,納博科夫移居美國,在威爾斯利、斯坦福、康奈爾和哈佛大學執教,以小說家、詩人、批評家和翻譯家的身份享譽文壇,著有《庶出的標誌》《洛麗塔》《普寧》和《微暗的火》等長篇小說。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納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麗塔》由巴黎奧林匹亞出版社出版並引發爭議。一九六一年,納博科夫遷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
納博科夫是二十世紀公認的傑出小說家和文體家。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納博科夫出生於聖彼德堡。布爾什維克革命期間,納博科夫隨全家於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國。他在劍橋三一學院攻讀法國和俄羅斯文學後,開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學生涯。一九四〇年,納博科夫移居美國,在威爾斯利、斯坦福、康奈爾和哈佛大學執教,以小說家、詩人、批評家和翻譯家的身份享譽文壇,著有《庶出的標誌》《洛麗塔》《普寧》和《微暗的火》等長篇小說。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納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麗塔》由巴黎奧林匹亞出版社出版並引發爭議。一九六一年,納博科夫遷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
序
前言
這本小長篇小說的俄文題目是SOGLYADATAY(按傳統音譯),按發音念是“Sugly-dart-eye” [注:英語dart的意思是“飛鏢”、“刺人的眼光”;eye的意思是“眼睛”],重音在倒數第二個音節上。這是一個古代軍事術語,意思是“間諜”或“坐探”,但兩者都沒有俄語詞靈活多變的引申意義。盤弄過“密使”和“角鬥士”之後,我放棄了音義兼顧的努力,不復所求,隨順了這個長詞幹末尾的“eye”。故事就是用這個題目在一九六五年年初數月的《花花公子》上連載三期,順利問世的。
原作一九三○年寫于柏林——我和妻子租了安靜的盧波爾德街上一戶德國人家的兩間屋子——當年年底發表在巴黎的俄文流亡者評論雜誌“SOVREMENNYYA ZAPISKI”(《現代紀事》)上。書中的人都是我在文學青年時代情有獨鍾的人物:生活在柏林、巴黎或倫敦的俄國流亡者。其實,他們也可以是生活在那不勒斯的挪威人或安布裡奇的安布拉基亞人[注:安布裡奇為美國地名,安布拉基亞為希臘歷史地名]:我向來對社會問題漠不關心,純粹是利用手邊的素材,就如同一個滔滔不絕的食客在桌布上畫一幅街頭素描或者把一粒麵包屑和兩隻橄欖在功能表和鹽瓶中間擺成一個陣圖一樣。對於社區生活、對於歷史侵擾的這種漠不關心有一個有趣結果,那便是:被漫不經心捲入藝術焦點的社會群體具有了虛假的固定態勢;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它就被那名流亡作家和他的流亡讀者視為理所當然了。一九三○年的伊萬•伊萬諾維奇和列夫•奧西波維奇[注:即普通俄語讀者]早就被非俄語讀者所取代,後者今天不得不想像一個他們一無所知的社會,因而感到困惑和氣惱;因為我並不反對一再重複說,自從近半個世紀前蘇維埃宣傳誤導外國輿論造成了對俄國移民(這樁歷史事件仍然等待著自己的編年史家)的重要性的無知或貶損以來,自由的毀滅者已經把大量的篇幅從歷史中撕掉了。
本故事的時間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俄國內戰已經結束四個年頭了。列寧剛死,但他的專政勢力繼續強勁。二十個德國馬克頂不上五個美元。書中旅居柏林的人從貧民到富商三六九等。富商的例子有瑪蒂爾達夢魘般的丈夫卡什馬林(顯然是從南線經君士坦丁堡逃離俄國的),葉甫蓋妮亞和萬尼亞的父親,一位年長的紳士(他有遠見卓識,領導著一家德國公司的倫敦分公司,還養著一名舞女)。卡什馬林可能就是英國人所謂的“中產階級”,然而孔雀街五號的兩位小姐顯然屬於俄國貴族,不管有沒有頭銜,但這種身份並不妨礙她們平庸的讀書品位。葉甫蓋妮亞的胖臉丈夫在一家柏林的銀行工作,他的名字今天聽起來十分滑稽。穆欣上校,一本正經,叫人噁心,一九一九年在鄧尼金手下打仗,一九二○年又受弗蘭格爾指揮,他能講四國語言,裝出一副冷靜、世故的派頭,很可能會在他未來岳父引導他進入的輕鬆工作中大顯身手。善良的羅曼•波戈丹諾維奇是個波羅的海人,習染的是德國而不是俄國文化。性情乖戾的猶太人魏因施托克,和平主義者女醫生瑪麗雅娜•尼古拉耶夫娜,還有無階級歸屬的敘事人自己,都是五花八門的俄國知識份子的代表。有一種讀者(像本人一樣)對諸如從馬紮爾語或漢語翻譯過來的那種描寫不熟悉的環境裡的虛幻人物的小說戰戰兢兢,對於他們,這些指點應該使閱讀變得容易一些。
眾所周知(用一句有名的俄國成語),我的書不僅受惠于社會意義的缺失,而且也得益於對神話的杜絕:佛洛德的門徒對它們趨之若鶩,興沖沖、癢抓抓地趕來,到了跟前,停下來,聞一聞,卻又畏縮起來。另一方面,一位嚴肅的心理學家可以透過我雨滴般晶瑩的密碼文字分辨出一個靈魂化解的世界,在那裡可憐的斯穆羅夫的存在只取決於他在別人頭腦裡的反映,而他們的頭腦接著也像他的一樣,被置於同樣離奇的鏡子似的窘境中。故事的結構戲擬偵探小說的結構,但說實在的,作者否認有任何玩弄、迷惑、愚弄或者欺騙讀者的意圖。其實,只有立即看懂的讀者才會從《眼睛》中獲得真正的滿足。即便最易輕信的讀者,讀這篇靈動閃爍的故事時要認識斯穆羅夫為何許人,也不可能費很長時間。我用一位英國老太太,兩名研究生,一位冰球教練,一位醫生,一位鄰居的十二歲的孩子做試驗。孩子最快,鄰居最慢。
《眼睛》的主題是實施一項調查研究,它引導主人公通過許許多多的鏡子,最後以一對形象的重合告終。三十五年前我以某種神秘模式整合敘事人追索的不同階段,我不知道我從中得到的強烈的快感是否會為現代讀者分享,然而,無論如何,強調的不是神秘,而是模式。我相信,儘管時光流轉,書海更迭,一種語言的海市蜃樓變成了另一種語言的綠洲,然而追蹤斯穆羅夫依然是件精彩的活動。情節不會在讀者頭腦裡——如果我把那頭腦研讀得正確的話——簡化為一個慘痛的愛情故事:其中有一顆痛苦扭動的心不僅遭受棄絕,而且受到羞辱和懲罰。想像的力量終歸是善的力量,這些力量依然穩穩地駐留在斯穆羅夫一邊,而事實證明備受煎熬的愛的苦澀,就像它最銷魂的回報一樣,令人陶醉,催人奮起。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九日 蒙特勒
這本小長篇小說的俄文題目是SOGLYADATAY(按傳統音譯),按發音念是“Sugly-dart-eye” [注:英語dart的意思是“飛鏢”、“刺人的眼光”;eye的意思是“眼睛”],重音在倒數第二個音節上。這是一個古代軍事術語,意思是“間諜”或“坐探”,但兩者都沒有俄語詞靈活多變的引申意義。盤弄過“密使”和“角鬥士”之後,我放棄了音義兼顧的努力,不復所求,隨順了這個長詞幹末尾的“eye”。故事就是用這個題目在一九六五年年初數月的《花花公子》上連載三期,順利問世的。
原作一九三○年寫于柏林——我和妻子租了安靜的盧波爾德街上一戶德國人家的兩間屋子——當年年底發表在巴黎的俄文流亡者評論雜誌“SOVREMENNYYA ZAPISKI”(《現代紀事》)上。書中的人都是我在文學青年時代情有獨鍾的人物:生活在柏林、巴黎或倫敦的俄國流亡者。其實,他們也可以是生活在那不勒斯的挪威人或安布裡奇的安布拉基亞人[注:安布裡奇為美國地名,安布拉基亞為希臘歷史地名]:我向來對社會問題漠不關心,純粹是利用手邊的素材,就如同一個滔滔不絕的食客在桌布上畫一幅街頭素描或者把一粒麵包屑和兩隻橄欖在功能表和鹽瓶中間擺成一個陣圖一樣。對於社區生活、對於歷史侵擾的這種漠不關心有一個有趣結果,那便是:被漫不經心捲入藝術焦點的社會群體具有了虛假的固定態勢;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它就被那名流亡作家和他的流亡讀者視為理所當然了。一九三○年的伊萬•伊萬諾維奇和列夫•奧西波維奇[注:即普通俄語讀者]早就被非俄語讀者所取代,後者今天不得不想像一個他們一無所知的社會,因而感到困惑和氣惱;因為我並不反對一再重複說,自從近半個世紀前蘇維埃宣傳誤導外國輿論造成了對俄國移民(這樁歷史事件仍然等待著自己的編年史家)的重要性的無知或貶損以來,自由的毀滅者已經把大量的篇幅從歷史中撕掉了。
本故事的時間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俄國內戰已經結束四個年頭了。列寧剛死,但他的專政勢力繼續強勁。二十個德國馬克頂不上五個美元。書中旅居柏林的人從貧民到富商三六九等。富商的例子有瑪蒂爾達夢魘般的丈夫卡什馬林(顯然是從南線經君士坦丁堡逃離俄國的),葉甫蓋妮亞和萬尼亞的父親,一位年長的紳士(他有遠見卓識,領導著一家德國公司的倫敦分公司,還養著一名舞女)。卡什馬林可能就是英國人所謂的“中產階級”,然而孔雀街五號的兩位小姐顯然屬於俄國貴族,不管有沒有頭銜,但這種身份並不妨礙她們平庸的讀書品位。葉甫蓋妮亞的胖臉丈夫在一家柏林的銀行工作,他的名字今天聽起來十分滑稽。穆欣上校,一本正經,叫人噁心,一九一九年在鄧尼金手下打仗,一九二○年又受弗蘭格爾指揮,他能講四國語言,裝出一副冷靜、世故的派頭,很可能會在他未來岳父引導他進入的輕鬆工作中大顯身手。善良的羅曼•波戈丹諾維奇是個波羅的海人,習染的是德國而不是俄國文化。性情乖戾的猶太人魏因施托克,和平主義者女醫生瑪麗雅娜•尼古拉耶夫娜,還有無階級歸屬的敘事人自己,都是五花八門的俄國知識份子的代表。有一種讀者(像本人一樣)對諸如從馬紮爾語或漢語翻譯過來的那種描寫不熟悉的環境裡的虛幻人物的小說戰戰兢兢,對於他們,這些指點應該使閱讀變得容易一些。
眾所周知(用一句有名的俄國成語),我的書不僅受惠于社會意義的缺失,而且也得益於對神話的杜絕:佛洛德的門徒對它們趨之若鶩,興沖沖、癢抓抓地趕來,到了跟前,停下來,聞一聞,卻又畏縮起來。另一方面,一位嚴肅的心理學家可以透過我雨滴般晶瑩的密碼文字分辨出一個靈魂化解的世界,在那裡可憐的斯穆羅夫的存在只取決於他在別人頭腦裡的反映,而他們的頭腦接著也像他的一樣,被置於同樣離奇的鏡子似的窘境中。故事的結構戲擬偵探小說的結構,但說實在的,作者否認有任何玩弄、迷惑、愚弄或者欺騙讀者的意圖。其實,只有立即看懂的讀者才會從《眼睛》中獲得真正的滿足。即便最易輕信的讀者,讀這篇靈動閃爍的故事時要認識斯穆羅夫為何許人,也不可能費很長時間。我用一位英國老太太,兩名研究生,一位冰球教練,一位醫生,一位鄰居的十二歲的孩子做試驗。孩子最快,鄰居最慢。
《眼睛》的主題是實施一項調查研究,它引導主人公通過許許多多的鏡子,最後以一對形象的重合告終。三十五年前我以某種神秘模式整合敘事人追索的不同階段,我不知道我從中得到的強烈的快感是否會為現代讀者分享,然而,無論如何,強調的不是神秘,而是模式。我相信,儘管時光流轉,書海更迭,一種語言的海市蜃樓變成了另一種語言的綠洲,然而追蹤斯穆羅夫依然是件精彩的活動。情節不會在讀者頭腦裡——如果我把那頭腦研讀得正確的話——簡化為一個慘痛的愛情故事:其中有一顆痛苦扭動的心不僅遭受棄絕,而且受到羞辱和懲罰。想像的力量終歸是善的力量,這些力量依然穩穩地駐留在斯穆羅夫一邊,而事實證明備受煎熬的愛的苦澀,就像它最銷魂的回報一樣,令人陶醉,催人奮起。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九日 蒙特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