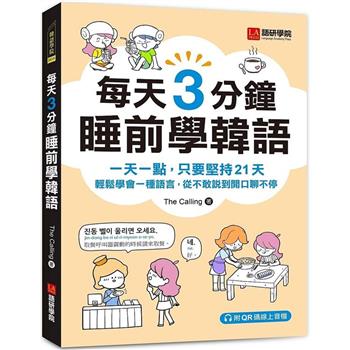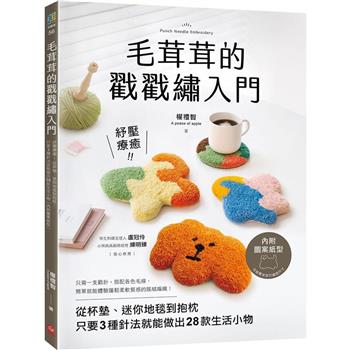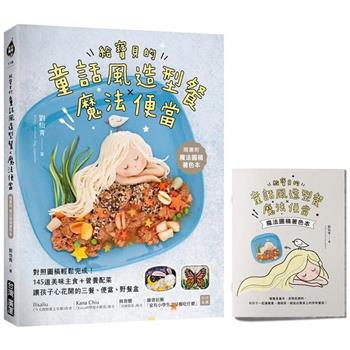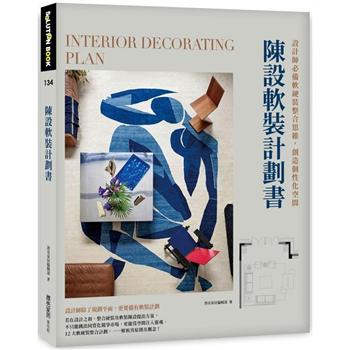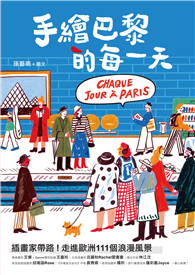一本書讀懂日本人的審美意識和文化心理。
日本國寶藝術史家高階秀爾在《日本人眼中的美》這本經典作品中,以繪畫、和歌、音樂、文字、書法、美術館、火車站、機器人、旅行、明信片、橋、富士山、鳥居、俳句等各個領域的日常事物和藝術作品為切入點,圖文結合,具體細緻而又系統深入地講述了日本的文化、日本的藝術特質,以及日本人的審美意識,讓人受益匪淺,堪稱名作。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日本人眼中的美的圖書 |
 |
日本人眼中的美 作者:(日)高階秀爾 出版社:湖南美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0-01 語言:簡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18頁 / 21.6 x 15.2 x 1.8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日本人眼中的美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高階秀爾
日本藝術史大家。1932年生於東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曾留學巴黎大學附屬美術研究所,主要從事日本和西方美術研究,致力於為日本民眾普及藝術知識。曾任日本國立西洋美術館館長,現任大原美術館館長。
因其在國民藝術普及上的卓越貢獻,分別在2000年獲得日本政府頒發的紫綬褒章,2012年獲得日本天皇親自頒發的文化獎——日本文化勳章。
著有《日本人眼中的美》《看名畫的眼睛》《名畫中的女人》《名畫中的小奧秘》等,並翻譯過肯內特·W·克拉克等人的作品。
日本藝術史大家。1932年生於東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曾留學巴黎大學附屬美術研究所,主要從事日本和西方美術研究,致力於為日本民眾普及藝術知識。曾任日本國立西洋美術館館長,現任大原美術館館長。
因其在國民藝術普及上的卓越貢獻,分別在2000年獲得日本政府頒發的紫綬褒章,2012年獲得日本天皇親自頒發的文化獎——日本文化勳章。
著有《日本人眼中的美》《看名畫的眼睛》《名畫中的女人》《名畫中的小奧秘》等,並翻譯過肯內特·W·克拉克等人的作品。
序
那是和法國友人一起乘坐新幹線去京都途中的事。那天,天氣倒是晴和,但富士山周邊卻霧靄重重。從車上完全看不到富士山的風姿。初訪日本的友人,半開玩笑地說:“是不是富士山根本就不存在啊?”對於他這句突如其來的玩笑,我一時不知如何應對,只好說:“她只是非常任性,變幻無常罷了。”聽了我的話,友人的反應很有趣。他像是非常驚訝,反問我:“富士山難道是女性嗎?”被他這麼一問,我才第一次意識到,法語中富士山叫 “le Mont Fuji”,和“le Mont Blanc(勃朗峰)”“le Mont Saint Michel(聖蜜雪兒山)”一樣都是陽性名詞。我在說法語時,用的也是“le Mont Fuji”,但說起對富士山的印象,腦海中浮現出的,總是一個優雅的女子形象。
最早,以信仰富士山成立的淺間神社祭祀的是富士山神(山之神就是女神),隨後演變為祭祀木花開耶姬,其祭祀之禮延續至今。加之輝夜姬的故事、羽衣傳說等,種種聯想在不知不覺間令人勾勒出了富士山的這種女性形象。在為數眾多的富士山繪畫中,都曾繪有優雅豔麗的天女姿態。
在歐洲,故事則全然不同。自古希臘以來,“山神”就與雷神、風神、河流之神一樣,被視為男性形象。在各種繪畫作品中,也主要被描繪成孔武有力的男性姿態。友人詫異于我將富士山稱為“她”,恐怕就是由此造成的吧。
人無法直接看到自己的臉。只有面對鏡子,才能捕捉到臉上的特徵。鏡中的姿態,既是本人,也是從外部、他人的視角觀察到的自己。美術(建築、繪畫、工藝)、文學(故事、詩歌、戲劇) 等藝術表現形式,也只有通過接受異域文化(比如西歐文化)的視角,再進行對比,才能使自身的特質更加明朗。
本書收集的各篇文章,即為從此類亦可被稱為複眼的視角出發闡述的日本文化論。
最早,以信仰富士山成立的淺間神社祭祀的是富士山神(山之神就是女神),隨後演變為祭祀木花開耶姬,其祭祀之禮延續至今。加之輝夜姬的故事、羽衣傳說等,種種聯想在不知不覺間令人勾勒出了富士山的這種女性形象。在為數眾多的富士山繪畫中,都曾繪有優雅豔麗的天女姿態。
在歐洲,故事則全然不同。自古希臘以來,“山神”就與雷神、風神、河流之神一樣,被視為男性形象。在各種繪畫作品中,也主要被描繪成孔武有力的男性姿態。友人詫異于我將富士山稱為“她”,恐怕就是由此造成的吧。
人無法直接看到自己的臉。只有面對鏡子,才能捕捉到臉上的特徵。鏡中的姿態,既是本人,也是從外部、他人的視角觀察到的自己。美術(建築、繪畫、工藝)、文學(故事、詩歌、戲劇) 等藝術表現形式,也只有通過接受異域文化(比如西歐文化)的視角,再進行對比,才能使自身的特質更加明朗。
本書收集的各篇文章,即為從此類亦可被稱為複眼的視角出發闡述的日本文化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