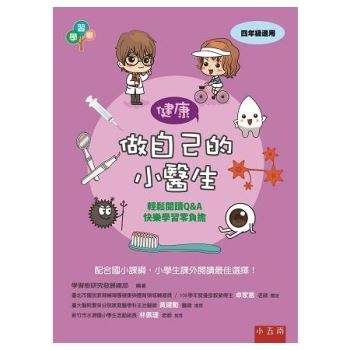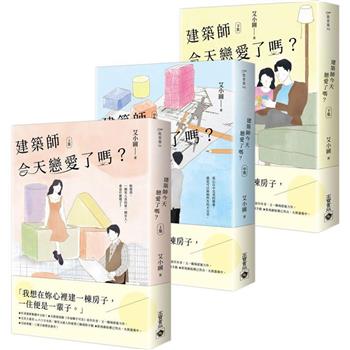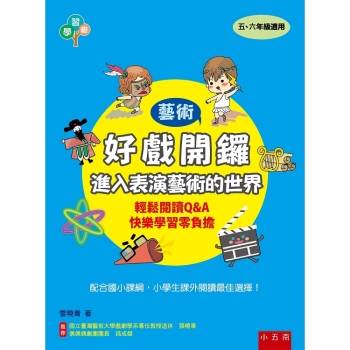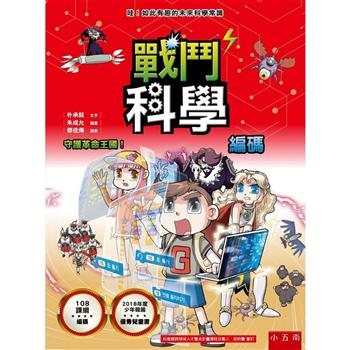畫界的朋友暗示我:線條是中國畫的靈魂,突出線條的作用,方能求得畫面的精神。這大概是對我在畫面中過多地渲染、營造氛圍的批評。在朋友看來,畫面中過多地尋求光色作用,會減弱中國畫的特性,影響東方精神的體現。
另一些經常一起談論莫内、塞尚、莫蘭迪的畫友又強調另外一種因素,即物體的特性與環境的作用,如何讓感官擺脫形態的束縛,重新找出一種內在的,與環境、光色交融的形態。若順著這種思路,似乎我又太重視細節的真實性而顯得過於謹慎。從兩方面來看,我都是不夠徹底的。正如我在觀察梅花時的態度,徘徊在兩種審美感覺中,受著這兩種美感的吸引。既然有著這種感受,就沒有必要為了某種傾向而有所排斥,關鍵是如何經過心靈調和將這些美感完整地、和諧地表達出來。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既徹底地忠實於我所求的知識,又忠實於真實的感受。
我嘮嘮叨叨了一大堆梅花的事,是想說明我的一切創作行為必須要有一個依據,那便是一個存在著的客體。直到現在我依然不能脫離客觀物象作畫,所以我任何一幅畫的構成,都依賴寫生,如果離開了物件,我幾乎就無處下筆,心中十分不踏實。我時常自嘲手笨,然而有時也會慶倖這種手笨,使自己因禍得福。正是因為這種手笨,我始終親近著自然,雖然這種親近包含著實用的目的,但逐漸也產生了擴展的效果,這就是由物的形、色以及環境的作用影響了情緒。反過來,屬於內心的一種情緒又投射到草木之間。這大概便是“物我交融”吧!
基於上述原因,我的畫面的細節是貼近自然的,相對而言,構築的整體卻有著情緒化的因素,或者是屬於理想的。當然,這種理想是由自然所引申的。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江宏偉畫二十四節氣(上)的圖書 |
 |
江宏偉畫二十四節氣(上) 作者:江宏偉 出版社:安徽美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7-01 語言:簡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9頁 / 8k菊/ 21 x 29.7 x 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2-2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江宏偉畫二十四節氣(上)
內容簡介
序
(一)
畫界的朋友暗示我:線條是中國畫的靈魂,突出線條的作用,方能求得畫面的精神。這大概是對我在畫面中過多地渲染、營造氛圍的批評。在朋友看來,畫面中過多地尋求光色作用,會減弱中國畫的特性,影響東方精神的體現。
另一些經常一起談論莫内、塞尚、莫蘭迪的畫友又強調另外一種因素,即物體的特性與環境的作用,如何讓感官擺脫形態的束縛,重新找出一種內在的,與環境、光色交融的形態。若順著這種思路,似乎我又太重視細節的真實性而顯得過於謹慎。從兩方面來看,我都是不夠徹底的。正如我在觀察梅花時的態度,徘徊在兩種審美感覺中,受著這兩種美感的吸引。既然有著這種感受,就沒有必要為了某種傾向而有所排斥,關鍵是如何經過心靈調和將這些美感完整地、和諧地表達出來。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既徹底地忠實於我所求的知識,又忠實於真實的感受。
我嘮嘮叨叨了一大堆梅花的事,是想說明我的一切創作行為必須要有一個依據,那便是一個存在著的客體。直到現在我依然不能脫離客觀物象作畫,所以我任何一幅畫的構成,都依賴寫生,如果離開了物件,我幾乎就無處下筆,心中十分不踏實。我時常自嘲手笨,然而有時也會慶倖這種手笨,使自己因禍得福。正是因為這種手笨,我始終親近著自然,雖然這種親近包含著實用的目的,但逐漸也產生了擴展的效果,這就是由物的形、色以及環境的作用影響了情緒。反過來,屬於內心的一種情緒又投射到草木之間。這大概便是“物我交融”吧!
基於上述原因,我的畫面的細節是貼近自然的,相對而言,構築的整體卻有著情緒化的因素,或者是屬於理想的。當然,這種理想是由自然所引申的。
(二)
一小時過去了,一天一天過去了,四尺宣紙上漸漸佈滿了枝條花影。而含苞的花蕾也一朵朵地綻放,綻放後又開始飄落,成團的花簇疏落了。桌面和紙面上遺下片片碎瓣,輕輕地用排筆將落英掃成一堆,咀嚼兩句“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心中居然有了些婉約的滋味。
(三)
我將毛筆蘸上些胭脂、花青、藤黃,用水調和,水色滲化。手捏著兩支筆,含色的一支點染在素紙上,浸水的一支順色暈化,紙面印出了色痕,逐漸幻化出心中物,營造成畫面。
兩支筆桿交替時撣擊出清脆的聲音,似時鐘般滴答。我在這樣的狀態下度過了二十多年,似乎還將持續下去。
如此的生活有點單調,久了也習慣了。在這單調之中,我很平靜,平靜的心中,映著花開花落。
所以我不單調,只是有些惆悵。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
我的惆悵,不是對命運的淒怨,而是對時序變遷的一種無奈。年年歲歲人不同,而自然依然如舊。隨著歲月的流逝,日漸增添了對草木枯榮的感觸。平日對花的寫照,如對故人又如自寫。
我將這種感觸消融進一張張素潔的紙中,仿佛也消融了韶華,在消融中我得到了一絲慰藉。至少我留住了我體驗到的一份心光,這份心光屬於自然界,屬於我,屬於我與自然界的融合。
(四)
追憶之所以讓我們眷戀是因為距離,距離將往事披上朦朧的色彩,篩去一些雜質,留下了美好。當我們所處某地、所處某景,我們並不覺得珍惜,一旦事過境遷,就會特別流連。所以我在對物寫生時會泛起一種遙遠的情懷,在渲染製作中又會將這種遙遠加以追憶。
畫界的朋友暗示我:線條是中國畫的靈魂,突出線條的作用,方能求得畫面的精神。這大概是對我在畫面中過多地渲染、營造氛圍的批評。在朋友看來,畫面中過多地尋求光色作用,會減弱中國畫的特性,影響東方精神的體現。
另一些經常一起談論莫内、塞尚、莫蘭迪的畫友又強調另外一種因素,即物體的特性與環境的作用,如何讓感官擺脫形態的束縛,重新找出一種內在的,與環境、光色交融的形態。若順著這種思路,似乎我又太重視細節的真實性而顯得過於謹慎。從兩方面來看,我都是不夠徹底的。正如我在觀察梅花時的態度,徘徊在兩種審美感覺中,受著這兩種美感的吸引。既然有著這種感受,就沒有必要為了某種傾向而有所排斥,關鍵是如何經過心靈調和將這些美感完整地、和諧地表達出來。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既徹底地忠實於我所求的知識,又忠實於真實的感受。
我嘮嘮叨叨了一大堆梅花的事,是想說明我的一切創作行為必須要有一個依據,那便是一個存在著的客體。直到現在我依然不能脫離客觀物象作畫,所以我任何一幅畫的構成,都依賴寫生,如果離開了物件,我幾乎就無處下筆,心中十分不踏實。我時常自嘲手笨,然而有時也會慶倖這種手笨,使自己因禍得福。正是因為這種手笨,我始終親近著自然,雖然這種親近包含著實用的目的,但逐漸也產生了擴展的效果,這就是由物的形、色以及環境的作用影響了情緒。反過來,屬於內心的一種情緒又投射到草木之間。這大概便是“物我交融”吧!
基於上述原因,我的畫面的細節是貼近自然的,相對而言,構築的整體卻有著情緒化的因素,或者是屬於理想的。當然,這種理想是由自然所引申的。
(二)
一小時過去了,一天一天過去了,四尺宣紙上漸漸佈滿了枝條花影。而含苞的花蕾也一朵朵地綻放,綻放後又開始飄落,成團的花簇疏落了。桌面和紙面上遺下片片碎瓣,輕輕地用排筆將落英掃成一堆,咀嚼兩句“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心中居然有了些婉約的滋味。
(三)
我將毛筆蘸上些胭脂、花青、藤黃,用水調和,水色滲化。手捏著兩支筆,含色的一支點染在素紙上,浸水的一支順色暈化,紙面印出了色痕,逐漸幻化出心中物,營造成畫面。
兩支筆桿交替時撣擊出清脆的聲音,似時鐘般滴答。我在這樣的狀態下度過了二十多年,似乎還將持續下去。
如此的生活有點單調,久了也習慣了。在這單調之中,我很平靜,平靜的心中,映著花開花落。
所以我不單調,只是有些惆悵。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
我的惆悵,不是對命運的淒怨,而是對時序變遷的一種無奈。年年歲歲人不同,而自然依然如舊。隨著歲月的流逝,日漸增添了對草木枯榮的感觸。平日對花的寫照,如對故人又如自寫。
我將這種感觸消融進一張張素潔的紙中,仿佛也消融了韶華,在消融中我得到了一絲慰藉。至少我留住了我體驗到的一份心光,這份心光屬於自然界,屬於我,屬於我與自然界的融合。
(四)
追憶之所以讓我們眷戀是因為距離,距離將往事披上朦朧的色彩,篩去一些雜質,留下了美好。當我們所處某地、所處某景,我們並不覺得珍惜,一旦事過境遷,就會特別流連。所以我在對物寫生時會泛起一種遙遠的情懷,在渲染製作中又會將這種遙遠加以追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