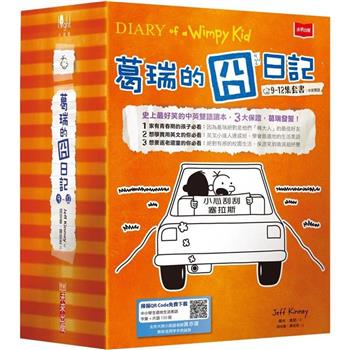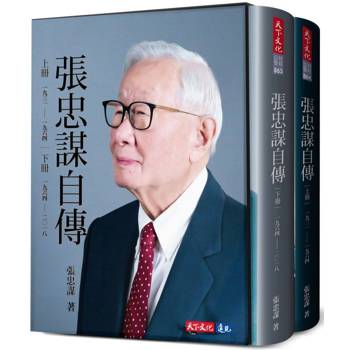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尤利西斯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54 |
二手中文書 |
$ 288 |
首頁 |
$ 303 |
其他地區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尤利西斯
內容簡介
《尤利西斯》是愛爾蘭意識流文學作家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于1922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小說以時間為順序,描述了主人公,苦悶彷徨的都柏林小市民,廣告推銷員利奧波德•布盧姆(Leopold Bloom)于1904年6月16日一晝夜之內在都柏林的種種日常經歷。喬伊斯將布盧姆在都柏林街頭的一日游蕩比作奧德修斯的海外十年漂泊,同時刻畫了他不忠誠的妻子摩莉以及斯蒂芬尋找精神上的父親的心理。小說大量運用細節描寫和意識流手法構建了一個交錯凌亂的時空,語言上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風格。本書是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並被譽為20世紀一百部最佳英文小說之首,每年的6月16日已經被紀念為“布盧姆日”。
目錄
半世紀文學姻緣的結晶(最新修訂本序)
叛逆‧開拓‧創新
—序《尤利西斯》中譯本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二部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三部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附錄一︰
《尤利西斯》與《奧德修紀》(對照)
附錄二︰
詹姆斯‧喬伊斯大事記
譯後記
叛逆‧開拓‧創新
—序《尤利西斯》中譯本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二部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三部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附錄一︰
《尤利西斯》與《奧德修紀》(對照)
附錄二︰
詹姆斯‧喬伊斯大事記
譯後記
序
今天(二OO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是老伴蕭乾的九十五歲誕辰。盡管他已在六年前的二月十一日去世,卻永遠活在喜愛他的著作和翻譯的讀者心里,也活在跟他相濡以沫達四十五年之久的我心里。
自從一九九O年八月著手合譯《尤利西斯》以來,蕭乾和我就和這部意識流頂峰之作結下了不解之緣。
蕭乾說過︰“我認為好的翻譯,譯者必須喜歡—甚至愛上了原作,再動筆,才能出好作品。”(見《譯林》1999年第1期《翻譯漫淡》—翻譯這門學問或藝術創造是沒有止境的)。
早在四十年代初,剛過而立之年的蕭乾曾從英國倫敦給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的胡適寫信道︰
“這本小說(指《尤利西斯》)如有人譯出,對我國創作技巧勢必大有影響,惜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
當時蕭乾做夢也沒想到,五十年後他會在譯林出版社社長李景端先生的鼓勵和全體同志的協助下,和我一道把這部意識流開山之作合譯出來。
現在來談談我們當初譯《尤利西斯》的動機。
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六年,我曾兩次陪蕭乾重訪劍橋。一九八四年那次,我們還到蕭乾四十年代在王家學院攻讀碩士學位時的導師喬治‧瑞蘭的寓所去小敘。瑞蘭還是位莎士比專家,我們見到他時,他已八十四歲,仍兼任著藝術劇院院長。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六月,剛過而立之年的蕭乾就在這間寬敞舒適的書房里,定期與導師討論自己的研究成果。只消把關于勞倫斯、吳爾芙、福斯特和喬伊斯的十幾篇小論文串起來,就是一篇碩士論文。然而,在《大公報》老板胡霖的勸告下,蕭乾放棄了即將到手的學位,走上戰地記者的崗位。他當時想的是︰歐戰這樣的人類大事,並不等人。現在不投進去,以後可無法彌補。至于研究工作,只要把這些書籍、筆記、日記、卡片保存好,將來年老力衰,跑不動了,照樣可以整理成文章。他哪里想得到,神州大地上竟會發生旨在毀滅文化的浩劫,使他畢生的心血化為灰燼呢?
一九七九年八月底蕭乾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主持人保羅‧安格爾、聶華苓邀請,赴美參加三十年來海峽兩岸以及中美作家之間首次交流活動。次年一月,經香港回京後,他對自己的健康狀況信心倍增。遂在一九八一年初,不顧四位大夫的勸阻,動了摘取左腎結石手術。手術後尿道不通,八個月後又做一次全身麻醉大手術,割除了左腎。從此元氣大傷。一九八五年,公余的右腎已告中等損傷。一九九O年六月,腎功能就只剩下常人的四分之一了。當年八月,譯林出版社主長李景端先生上門來約我們翻譯《尤利西斯》時,我立即想︰這正是目前情況下最適宜蕭乾做的工作了。創作我幫不上忙,翻譯呢,只要我把初稿譯好,把嚴“信”這個關,以他深厚的中英文功底,神來之筆,做到“達、雅”,可以說是駕輕就熟。與其從早到晚為病情憂慮,不如做一項有價值的工作,說不定對身心還有益處。大功告成之日,就意味著給他四十年代功虧一簣的意識流研究工作畫個圓滿的句號。我們正譯得熱火朝天時,收到了蕭乾的英國恩師瑞蘭寫來的信,鼓勵道︰“你們在翻譯《尤利西斯》,使我大為吃驚,欽佩得話都說不出來。多大的挑戰。衷心祝願你們取得全面的成功。”(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大功告成後,年屆九十三歲的導師給他這個八十五歲的昔日高足來函褒獎︰“親愛的了不起的乾︰你們的《尤利西斯》一定是本世紀最出色的翻譯。多大的成就!我渴望了解學生們和一般市民有何反應。務請告知。”(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六日)
……
自從一九九O年八月著手合譯《尤利西斯》以來,蕭乾和我就和這部意識流頂峰之作結下了不解之緣。
蕭乾說過︰“我認為好的翻譯,譯者必須喜歡—甚至愛上了原作,再動筆,才能出好作品。”(見《譯林》1999年第1期《翻譯漫淡》—翻譯這門學問或藝術創造是沒有止境的)。
早在四十年代初,剛過而立之年的蕭乾曾從英國倫敦給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的胡適寫信道︰
“這本小說(指《尤利西斯》)如有人譯出,對我國創作技巧勢必大有影響,惜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
當時蕭乾做夢也沒想到,五十年後他會在譯林出版社社長李景端先生的鼓勵和全體同志的協助下,和我一道把這部意識流開山之作合譯出來。
現在來談談我們當初譯《尤利西斯》的動機。
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六年,我曾兩次陪蕭乾重訪劍橋。一九八四年那次,我們還到蕭乾四十年代在王家學院攻讀碩士學位時的導師喬治‧瑞蘭的寓所去小敘。瑞蘭還是位莎士比專家,我們見到他時,他已八十四歲,仍兼任著藝術劇院院長。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六月,剛過而立之年的蕭乾就在這間寬敞舒適的書房里,定期與導師討論自己的研究成果。只消把關于勞倫斯、吳爾芙、福斯特和喬伊斯的十幾篇小論文串起來,就是一篇碩士論文。然而,在《大公報》老板胡霖的勸告下,蕭乾放棄了即將到手的學位,走上戰地記者的崗位。他當時想的是︰歐戰這樣的人類大事,並不等人。現在不投進去,以後可無法彌補。至于研究工作,只要把這些書籍、筆記、日記、卡片保存好,將來年老力衰,跑不動了,照樣可以整理成文章。他哪里想得到,神州大地上竟會發生旨在毀滅文化的浩劫,使他畢生的心血化為灰燼呢?
一九七九年八月底蕭乾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主持人保羅‧安格爾、聶華苓邀請,赴美參加三十年來海峽兩岸以及中美作家之間首次交流活動。次年一月,經香港回京後,他對自己的健康狀況信心倍增。遂在一九八一年初,不顧四位大夫的勸阻,動了摘取左腎結石手術。手術後尿道不通,八個月後又做一次全身麻醉大手術,割除了左腎。從此元氣大傷。一九八五年,公余的右腎已告中等損傷。一九九O年六月,腎功能就只剩下常人的四分之一了。當年八月,譯林出版社主長李景端先生上門來約我們翻譯《尤利西斯》時,我立即想︰這正是目前情況下最適宜蕭乾做的工作了。創作我幫不上忙,翻譯呢,只要我把初稿譯好,把嚴“信”這個關,以他深厚的中英文功底,神來之筆,做到“達、雅”,可以說是駕輕就熟。與其從早到晚為病情憂慮,不如做一項有價值的工作,說不定對身心還有益處。大功告成之日,就意味著給他四十年代功虧一簣的意識流研究工作畫個圓滿的句號。我們正譯得熱火朝天時,收到了蕭乾的英國恩師瑞蘭寫來的信,鼓勵道︰“你們在翻譯《尤利西斯》,使我大為吃驚,欽佩得話都說不出來。多大的挑戰。衷心祝願你們取得全面的成功。”(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大功告成後,年屆九十三歲的導師給他這個八十五歲的昔日高足來函褒獎︰“親愛的了不起的乾︰你們的《尤利西斯》一定是本世紀最出色的翻譯。多大的成就!我渴望了解學生們和一般市民有何反應。務請告知。”(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六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