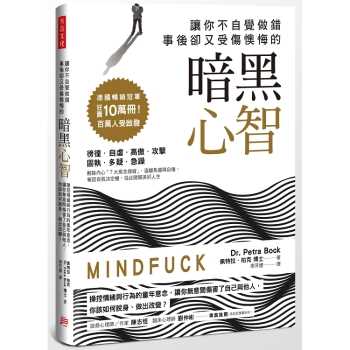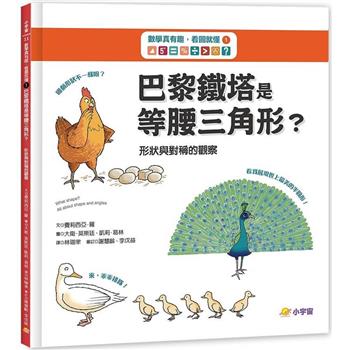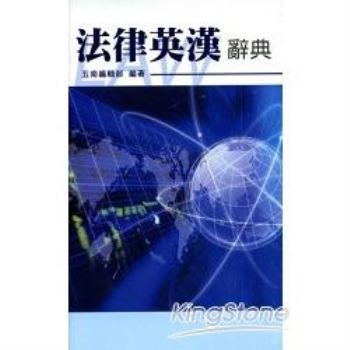有史以來戲劇一直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種藝術形式。從木偶戲到啞劇到街頭表演再到現代劇場,這種複雜的藝術借用了各種其他藝術形式,如舞蹈、文學、音樂、繪畫、雕塑和建築等,並將人類活動和人類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納入其創作。在本書中,戲劇研究專家馬文·卡爾森縱橫幾千年,帶領我們了解世界各地的各種戲劇形式是如何演化併流傳至今的。此外,他還將戲劇表演與戲劇文本加以區分,探討了兩者之間的關係,並對戲劇藝術家所扮演的各種角色做了一次引人入勝的探索。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戲劇的圖書 |
 |
戲劇 作者:(美)馬文·卡爾森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7-01 語言:簡體中文 規格:平裝 / 121頁 / 16k/ 19 x 26 x 1.3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1-1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戲劇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馬文·卡爾森 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戲劇、比較文學和中東研究方向的“西德尼·E. 科恩”講席傑出教授,曾任教于華盛頓大學和印第安那大學等高等學府。研究和教學興趣包括戲劇學與表演學理論、世界戲劇史和戲劇與表演研究。Western European Stages期刊的創刊編輯,在戲劇史、戲劇理論、戲劇文學和表演研究領域發表了大量學術論文及著作。其著作多次獲獎並被譯為多種語言,代表作包括《戲劇理論》(1993)、《鬼魂出沒的舞臺》(2001)、《表演批評》(2002)、《世界戲劇導論》(2014)等,*新著作為《擊碎哈姆雷特之鏡:戲劇與現實》(2016)。
序
對中國讀者來說,馬文·卡爾森教授這本小書最大的優點,是它的前沿性:它出版於2014年,記錄了本世紀西方學者對於“戲劇”的最新看法。這一點對於中國讀者很重要!我們現在談到話劇經典,還是80多年前的《雷雨》和60年前的《茶館》,《桑樹坪紀事》不再演了,《天下第一樓》也已問世30年,百年來的創作,能夠流傳下來的很少很少,在這種“正統”戲劇發育不良的背景之下,反叛“正統”的新戲劇實際上起點也就很低,做不出樣子來。而百年來的西方戲劇,在易蔔生、契訶夫、斯特林堡之後,有尤金·奧尼爾、田納西·威廉斯、亞瑟·米勒,在他們的背景之下,又有貝克特、尤內斯庫、品特,有彼得·布魯克、理查·謝克納、羅伯特·威爾遜、彼得·施泰因、喬治·斯特雷勒……這本小書的關鍵字是theatre、drama、performance,它的核心兩章的標題分別是“Theatreanddrama”“Theatreandperformance”,瞭解drama怎樣被theatre所“覆蓋”,performance怎樣正在試圖“脫穎而出”,就大體上可以瞭解直至本世紀世界戲劇的發展與走向。而中國戲劇在理論和實踐上,與這種發展和走向還是相當隔膜的。
本書關於“宗教和戲劇”的關係論說得非常精彩,對中國讀者也是極具啟發性的。但這應該更多是帶有作者個人色彩的論題,並不屬於書中必論的,一定要論,至少還有“政治與戲劇”同樣重要。作者是一位非常淵博的世界戲劇學者,他論說的出發點雖然立足西方,卻是以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多類型戲劇為背景的。看得出來,在東方戲劇中,作者對於日本戲劇更加熟悉。
theatre和drama,漢語都譯作“戲劇”,但在英語中,theatre作為一般的戲劇,涵蓋一切時代、一切類型的戲劇,而drama則是一種具體的戲劇類型,即成形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直到上世紀上半葉一直作為歐美主流戲劇樣式的戲劇。當theatre與drama相遇時,漢譯會非常困難,幾乎是一個死胡同。本書第三章“Theatre and drama”譯作“演劇和戲劇文本”,雖然不理想,但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作為一本極簡的介紹(Very Short Introduction),書中沒有談到drama被“覆蓋”的更深層原因。本書提到德國戲劇學者漢斯—蒂斯·雷曼1999年出版的《後戲劇劇場》和雷曼的老師彼得·斯叢狄1956年出版的《現代戲劇理論》這兩本非常重要的戲劇理論著作。根據斯叢狄和雷曼的觀點,drama對劇壇的統治以及這個統治的坍塌,歸根結底,都是由不同時代的不同世界觀所造成的。
drama是“在中世紀的世界圖景破碎之後,重新回歸自我的人借此進行了一次精神的冒險”。文藝復興時期的戲劇家們把亞里斯多德的《詩學》當作創立自己時代戲劇最重要的理論資源。在《詩學》裡,亞裡士多德完全不顧古希臘悲劇中歌隊的存在,把古希臘悲劇的情節藝術看作第一要素,並且把這個情節藝術總結為根據“可然律”“必然律”構建成的一條因果鏈。亞裡士多德認為,因為這種人類理性所建立的邏輯,“詩”(悲劇)比歷史更真實可信。黑格爾在他的《美學》中,把drama(戲劇體詩)定義為“史詩的原則和抒情詩的原則經過調解(互相轉化)的統一”,即:一方面戲劇行動必須源自主人公內心的激情與意志,另一方面戲劇主人公的內心生活必須外化為行動。因此,drama的條件是人的覺醒與自由:悲劇“需要人物已意識到個人自由獨立的原則,或是至少需要已意識到個人有自由自決的權利去對自己的動作及其後果負責”;喜劇“需要主體的自由權和駕馭世界的自覺性”。這就是歐洲文藝復興推翻中世紀信仰後所建立的現代社會的個人主義。亞里斯多德《詩學》所描述的理性主義和黑格爾“戲劇體詩”理論所描述的個人主義,就是drama的兩根世界觀支柱。
但是,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在歐洲暢行了數百年後,終於爆發了危機:歐洲人以一種更高的理性看到了自身理性的有限,他們也看到了上帝“死去”以後盛行的個人主義並不能真正帶來人類的解放。於是,“詩”比歷史更真實的信心開始破產,個人主義的信仰也遭到了懷疑。斯叢狄分析了這種後文藝復興世界觀在易蔔生、契訶夫、斯特林堡、梅特林克和豪普特曼劇作裡的存在及其對drama文體的消解與破壞。40年後,斯叢狄的學生雷曼描述了Post dramatic Theatre,一種新戲劇的成長與原則。
希望我的介紹能夠為中國讀者帶來對馬文·卡爾森教授戲劇通識讀本更深入的思考與理解,希望能夠給戲劇理論愛好者們引出延伸閱讀。
本書關於“宗教和戲劇”的關係論說得非常精彩,對中國讀者也是極具啟發性的。但這應該更多是帶有作者個人色彩的論題,並不屬於書中必論的,一定要論,至少還有“政治與戲劇”同樣重要。作者是一位非常淵博的世界戲劇學者,他論說的出發點雖然立足西方,卻是以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多類型戲劇為背景的。看得出來,在東方戲劇中,作者對於日本戲劇更加熟悉。
theatre和drama,漢語都譯作“戲劇”,但在英語中,theatre作為一般的戲劇,涵蓋一切時代、一切類型的戲劇,而drama則是一種具體的戲劇類型,即成形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直到上世紀上半葉一直作為歐美主流戲劇樣式的戲劇。當theatre與drama相遇時,漢譯會非常困難,幾乎是一個死胡同。本書第三章“Theatre and drama”譯作“演劇和戲劇文本”,雖然不理想,但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作為一本極簡的介紹(Very Short Introduction),書中沒有談到drama被“覆蓋”的更深層原因。本書提到德國戲劇學者漢斯—蒂斯·雷曼1999年出版的《後戲劇劇場》和雷曼的老師彼得·斯叢狄1956年出版的《現代戲劇理論》這兩本非常重要的戲劇理論著作。根據斯叢狄和雷曼的觀點,drama對劇壇的統治以及這個統治的坍塌,歸根結底,都是由不同時代的不同世界觀所造成的。
drama是“在中世紀的世界圖景破碎之後,重新回歸自我的人借此進行了一次精神的冒險”。文藝復興時期的戲劇家們把亞里斯多德的《詩學》當作創立自己時代戲劇最重要的理論資源。在《詩學》裡,亞裡士多德完全不顧古希臘悲劇中歌隊的存在,把古希臘悲劇的情節藝術看作第一要素,並且把這個情節藝術總結為根據“可然律”“必然律”構建成的一條因果鏈。亞裡士多德認為,因為這種人類理性所建立的邏輯,“詩”(悲劇)比歷史更真實可信。黑格爾在他的《美學》中,把drama(戲劇體詩)定義為“史詩的原則和抒情詩的原則經過調解(互相轉化)的統一”,即:一方面戲劇行動必須源自主人公內心的激情與意志,另一方面戲劇主人公的內心生活必須外化為行動。因此,drama的條件是人的覺醒與自由:悲劇“需要人物已意識到個人自由獨立的原則,或是至少需要已意識到個人有自由自決的權利去對自己的動作及其後果負責”;喜劇“需要主體的自由權和駕馭世界的自覺性”。這就是歐洲文藝復興推翻中世紀信仰後所建立的現代社會的個人主義。亞里斯多德《詩學》所描述的理性主義和黑格爾“戲劇體詩”理論所描述的個人主義,就是drama的兩根世界觀支柱。
但是,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在歐洲暢行了數百年後,終於爆發了危機:歐洲人以一種更高的理性看到了自身理性的有限,他們也看到了上帝“死去”以後盛行的個人主義並不能真正帶來人類的解放。於是,“詩”比歷史更真實的信心開始破產,個人主義的信仰也遭到了懷疑。斯叢狄分析了這種後文藝復興世界觀在易蔔生、契訶夫、斯特林堡、梅特林克和豪普特曼劇作裡的存在及其對drama文體的消解與破壞。40年後,斯叢狄的學生雷曼描述了Post dramatic Theatre,一種新戲劇的成長與原則。
希望我的介紹能夠為中國讀者帶來對馬文·卡爾森教授戲劇通識讀本更深入的思考與理解,希望能夠給戲劇理論愛好者們引出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