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醫學在成功地完成它的使命後,卻在勝利中迷茫了。”
從古希臘時期醫學的理性發端,到文藝復興與科學革命推動的醫學科學化,再到近兩百年細胞學、細菌學、免疫學、心理分析等等重大進展,醫學的進步毋庸置疑。
從起初的疾病觀之爭、性別汙名,到20世紀淪為戰爭工具,再到如今的技術化取向、衛生資源配置問題,醫學也從未遠離爭議與危機。
這是一部醫學史,也是一部疾病史、醫院史、外科史、藥物史,更是一部醫學背後的社會史與思想史。透過對歷史的回顧與對未來的展望,《劍橋醫學史》探尋醫學的本質和價值,召喚醫學的人文關懷。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劍橋醫學史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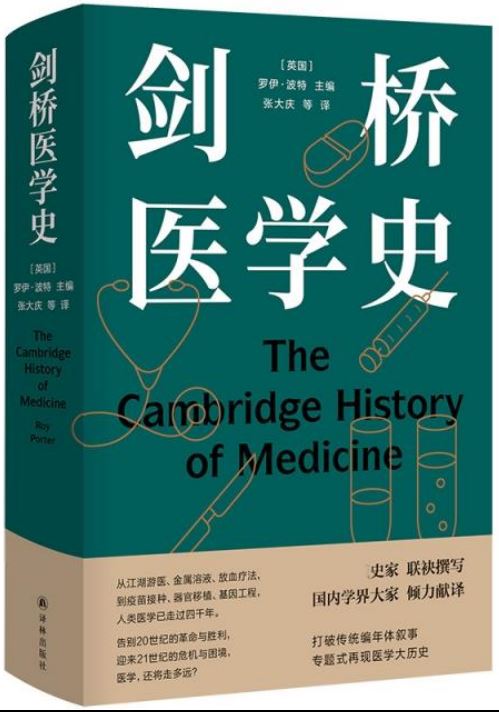 |
劍橋醫學史 作者:(英)羅伊·波特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01-01 語言:簡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93頁 / 32k/ 13 x 19 x 2.46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劍橋醫學史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羅伊·波特(RoyPorter,1946—2002)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倫敦維爾康醫學史研究所醫學社會史教授,曾任教于劍橋大學和洛杉磯加州大學。他的研究興趣廣泛,尤擅醫學史,開創性地將病患置於醫學史的重要位置,是醫學社會史和醫學文化史的先驅。編撰的著作超過百部,另有《社會的醫生:湯瑪斯·比多斯與啟蒙時代英格蘭的醫療事業》《倫敦:社會史》《人類最大的福利:人文醫學史》等。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倫敦維爾康醫學史研究所醫學社會史教授,曾任教于劍橋大學和洛杉磯加州大學。他的研究興趣廣泛,尤擅醫學史,開創性地將病患置於醫學史的重要位置,是醫學社會史和醫學文化史的先驅。編撰的著作超過百部,另有《社會的醫生:湯瑪斯·比多斯與啟蒙時代英格蘭的醫療事業》《倫敦:社會史》《人類最大的福利:人文醫學史》等。
目錄
導言
第一章 疾病史
第二章 醫學的興起
第三章 疾病是什麼?
第四章 初級保健
第五章 醫學科學
第六章 醫院與外科
第七章 藥物治療與藥物學的興起
第八章 精神疾病
第九章 醫學、社會與政府
第十章 展望未來(1996年)
增補:重新審視對未來的展望
大事年表
人類主要疾病
注釋
延伸閱讀
主題索引
醫學人物人名索引
作者簡介
譯後記
第一章 疾病史
第二章 醫學的興起
第三章 疾病是什麼?
第四章 初級保健
第五章 醫學科學
第六章 醫院與外科
第七章 藥物治療與藥物學的興起
第八章 精神疾病
第九章 醫學、社會與政府
第十章 展望未來(1996年)
增補:重新審視對未來的展望
大事年表
人類主要疾病
注釋
延伸閱讀
主題索引
醫學人物人名索引
作者簡介
譯後記
序
導論
在西方,人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如此健康、長壽,醫學的成就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如此巨大。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們也從來未像今天這樣如此強烈地對醫學產生疑惑和提出批評。無人可以否認,過去50年,醫學科學經過漫長發展後到達頂峰,無數突破性的進展挽救了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多得多的生命。醫學的進步在我們看來已是老生常談,因此應當對今天認為是理所當然,而一二百年前卻是天方夜譚的巨大變革加以總結。以下章節將詳細地討論和解釋這些進步。作為導言,這裡簡要地概括20世紀下半葉發生的最顯著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青黴素仍處於實驗室研究階段,在數年中只能定量供應。在這種抗生素“魔彈”發明之前,肺炎、腦膜炎和類似的感染依然經常致命。長期以來,結核病是發達國家最重要的死因,它被稱為“白色瘟疫”,與“黑死病”相對(因為結核病患者都皮膚蒼白)。然而,隨著卡介苗和鏈黴素於20世紀40年代問世,結核病得到有效的控制。50年代,“第1次藥物學革命”導致了廣泛的變革。新的生物藥物殺滅細菌,提高了對營養缺乏症的控制,促成了抗精神病有效藥物(如精神藥物氯丙嗪)的問世。與此同時,預防脊髓灰質炎的疫苗研發成功。
其他藥物的突破,特別是類固醇(如可的松),使人類對免疫系統有了進一步理解。通過解決排異問題,免疫抑制劑的發展為整形和移植外科開拓了廣闊的新領域。心臟病學也日益繁榮。1944年,對出生時患先天性心臟病的“藍嬰”成功地進行外科手術,是心臟外科發展的里程碑之一。此後,兒科心臟病學迅速發展。心臟直視手術可回溯到20世紀50年代,而冠狀動脈旁路手術是又一次飛躍,開始於1967年。
此時的外科正像太空旅行一樣日益受到公眾關注。外科的發展似乎永無止境。器官移植出現了,首先是腎移植。1967年,移植成為頭條新聞,克利斯蒂安·尼斯林·巴納德醫生將一位婦女的心臟縫入路易士·沃什坎斯基的體內,後者帶著這顆心臟又活了18天。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僅美國每年就要施行上百例心臟移植手術,三分之二的移植者可存活五年以上。在過去50年裡,外科不僅得到了發展,而且性質也發生了轉變。20世紀初期,外科的本質是根除:找到病灶,將其切除(往往有效,但相當粗糙)。而它的理念要複雜得多:連續不斷的修復和(也許是無止境的)替代。
除了這些干預方面的實際進步外,科學一直在為治療學做出貢獻。電子顯微鏡、內窺鏡、電腦軸向斷層掃描(CAT)、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ET)、磁共振成像(MRI)、鐳射、示蹤儀以及超聲診斷儀等,引發了醫學診斷能力的一場革命。鐳射帶來了顯微外科。鐵肺、腎透析機、心肺機和起搏器等都在醫學的軍械庫中佔據了一席之地。與此同時,基礎科學研究已改變了人們對機體及其與疾病鬥爭的理解。特別是在法蘭西斯·克裡克和詹姆斯·沃特森於1953年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破解遺傳密碼之後,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迅速發展,遺傳篩選和遺傳工程已取得了巨大進步。與此同時,腦化學開拓了醫學的新領域:內啡肽研究揭示了疼痛的奧秘;左旋多巴等神經遞質的合成機理為帕金森病和其他中樞神經系統的紊亂提供了治療方案。臨床醫學—將科學方法應用於實際疾病經驗—終於得到了承認,不再是“灰姑娘”,這部分應歸功於從20世紀40年代中期發展起來的隨機臨床試驗。
簡而言之,有兩個事實強有力地證明了醫學日益重要的意義(雖然這兩個事實可能相互矛盾)。第1個事實是,世界人口在過去50年翻了一番(從1950年的25億增至2000年的62.5億),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新的醫學干預和預防措施。第二個事實是,避孕藥的問世,至少在理論上為安全、簡便地控制人口增長鋪平了道路。這些發展是眾所周知的,但是耳熟能詳並不影響其成就。人類歷史上曾發生過多次革命—農業的形成、城市的發展、印刷術、17世紀偉大的科學進步以及工業革命等。但是,直到20世紀下半葉,醫學革命才出現,帶來了重大的治療學革新—如果我們將大規模征服威脅生命的疾病的可靠能力作為衡量標準的話。富裕國家的人們健康而長壽,貧窮國家人口稠密,都證實了這一點。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將醫學的這些變化置於其歷史背景中來理解。我們將追溯從古希臘開始的悠久傳統,在古希臘,人類第1次將醫學建立在理性和科學的基礎之上。我們將考察由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激發的轉變,它顯示出物理學和化學的成就對醫學的推動。我們也將展示19世紀的醫學科學在公共衛生、細胞學、細菌學、寄生蟲學、抗菌術和麻醉外科等方面取得的進展,以及20世紀早期在X射線、免疫學、對激素和維生素的理解、化學治療乃至心理分析方面取得的重大進展。
……要理解這些問題的根源(在美國問題格外嚴重,但其他地方也差不多),我們需要從歷史變遷的角度來考察這些基本要素。這是以下體系必然會有的問題:其中,醫療機構不斷擴張,面對自己創造出來的越來越健康的人群,被驅使著將日常生活事件醫學化(例如更年期),將風險轉化為疾病,用花哨的程式去治療微不足道的身體不適。醫生和“消費者”都日益鎖定在一種幻想之中,將焦慮的產生與雄心勃勃的“能做,必須做”的技術完美主義結合在一起:每個人的體內都存在著問題,每個人都能被治癒。醫學的成功可能正在創造一個弗蘭肯斯坦式的怪物,即現代醫學的批評者伊萬·伊裡奇所稱的“生活醫學化”。指出醫學的這些困境,並不是為了發洩對醫學的怨恨—一種對醫學成功的粗野報復,而僅僅是對醫學力量的認識,這種力量的增長並不完全是無責任的,而是不斷消解目標。儘管此時可能正值醫學的榮光時刻,但也可能是困境的發端。
……正如本書所述故事表明的那樣,我們今天正生活在醫學的重要時期,但這也是充滿懷疑的時期。在過去兩百年裡,特別是在近幾十年,醫學已越來越強大,也越來越成功。然而,面對醫學可能走向何處等諸多問題,社會上存在著深刻的個人焦慮和公眾爭論。透過本書所提供的歷史視角,悖論(越健康長壽,對醫學就越焦慮)即便不能被解決,至少也可以被理解。
在西方,人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如此健康、長壽,醫學的成就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如此巨大。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們也從來未像今天這樣如此強烈地對醫學產生疑惑和提出批評。無人可以否認,過去50年,醫學科學經過漫長發展後到達頂峰,無數突破性的進展挽救了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多得多的生命。醫學的進步在我們看來已是老生常談,因此應當對今天認為是理所當然,而一二百年前卻是天方夜譚的巨大變革加以總結。以下章節將詳細地討論和解釋這些進步。作為導言,這裡簡要地概括20世紀下半葉發生的最顯著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青黴素仍處於實驗室研究階段,在數年中只能定量供應。在這種抗生素“魔彈”發明之前,肺炎、腦膜炎和類似的感染依然經常致命。長期以來,結核病是發達國家最重要的死因,它被稱為“白色瘟疫”,與“黑死病”相對(因為結核病患者都皮膚蒼白)。然而,隨著卡介苗和鏈黴素於20世紀40年代問世,結核病得到有效的控制。50年代,“第1次藥物學革命”導致了廣泛的變革。新的生物藥物殺滅細菌,提高了對營養缺乏症的控制,促成了抗精神病有效藥物(如精神藥物氯丙嗪)的問世。與此同時,預防脊髓灰質炎的疫苗研發成功。
其他藥物的突破,特別是類固醇(如可的松),使人類對免疫系統有了進一步理解。通過解決排異問題,免疫抑制劑的發展為整形和移植外科開拓了廣闊的新領域。心臟病學也日益繁榮。1944年,對出生時患先天性心臟病的“藍嬰”成功地進行外科手術,是心臟外科發展的里程碑之一。此後,兒科心臟病學迅速發展。心臟直視手術可回溯到20世紀50年代,而冠狀動脈旁路手術是又一次飛躍,開始於1967年。
此時的外科正像太空旅行一樣日益受到公眾關注。外科的發展似乎永無止境。器官移植出現了,首先是腎移植。1967年,移植成為頭條新聞,克利斯蒂安·尼斯林·巴納德醫生將一位婦女的心臟縫入路易士·沃什坎斯基的體內,後者帶著這顆心臟又活了18天。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僅美國每年就要施行上百例心臟移植手術,三分之二的移植者可存活五年以上。在過去50年裡,外科不僅得到了發展,而且性質也發生了轉變。20世紀初期,外科的本質是根除:找到病灶,將其切除(往往有效,但相當粗糙)。而它的理念要複雜得多:連續不斷的修復和(也許是無止境的)替代。
除了這些干預方面的實際進步外,科學一直在為治療學做出貢獻。電子顯微鏡、內窺鏡、電腦軸向斷層掃描(CAT)、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ET)、磁共振成像(MRI)、鐳射、示蹤儀以及超聲診斷儀等,引發了醫學診斷能力的一場革命。鐳射帶來了顯微外科。鐵肺、腎透析機、心肺機和起搏器等都在醫學的軍械庫中佔據了一席之地。與此同時,基礎科學研究已改變了人們對機體及其與疾病鬥爭的理解。特別是在法蘭西斯·克裡克和詹姆斯·沃特森於1953年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破解遺傳密碼之後,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迅速發展,遺傳篩選和遺傳工程已取得了巨大進步。與此同時,腦化學開拓了醫學的新領域:內啡肽研究揭示了疼痛的奧秘;左旋多巴等神經遞質的合成機理為帕金森病和其他中樞神經系統的紊亂提供了治療方案。臨床醫學—將科學方法應用於實際疾病經驗—終於得到了承認,不再是“灰姑娘”,這部分應歸功於從20世紀40年代中期發展起來的隨機臨床試驗。
簡而言之,有兩個事實強有力地證明了醫學日益重要的意義(雖然這兩個事實可能相互矛盾)。第1個事實是,世界人口在過去50年翻了一番(從1950年的25億增至2000年的62.5億),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新的醫學干預和預防措施。第二個事實是,避孕藥的問世,至少在理論上為安全、簡便地控制人口增長鋪平了道路。這些發展是眾所周知的,但是耳熟能詳並不影響其成就。人類歷史上曾發生過多次革命—農業的形成、城市的發展、印刷術、17世紀偉大的科學進步以及工業革命等。但是,直到20世紀下半葉,醫學革命才出現,帶來了重大的治療學革新—如果我們將大規模征服威脅生命的疾病的可靠能力作為衡量標準的話。富裕國家的人們健康而長壽,貧窮國家人口稠密,都證實了這一點。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將醫學的這些變化置於其歷史背景中來理解。我們將追溯從古希臘開始的悠久傳統,在古希臘,人類第1次將醫學建立在理性和科學的基礎之上。我們將考察由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激發的轉變,它顯示出物理學和化學的成就對醫學的推動。我們也將展示19世紀的醫學科學在公共衛生、細胞學、細菌學、寄生蟲學、抗菌術和麻醉外科等方面取得的進展,以及20世紀早期在X射線、免疫學、對激素和維生素的理解、化學治療乃至心理分析方面取得的重大進展。
……要理解這些問題的根源(在美國問題格外嚴重,但其他地方也差不多),我們需要從歷史變遷的角度來考察這些基本要素。這是以下體系必然會有的問題:其中,醫療機構不斷擴張,面對自己創造出來的越來越健康的人群,被驅使著將日常生活事件醫學化(例如更年期),將風險轉化為疾病,用花哨的程式去治療微不足道的身體不適。醫生和“消費者”都日益鎖定在一種幻想之中,將焦慮的產生與雄心勃勃的“能做,必須做”的技術完美主義結合在一起:每個人的體內都存在著問題,每個人都能被治癒。醫學的成功可能正在創造一個弗蘭肯斯坦式的怪物,即現代醫學的批評者伊萬·伊裡奇所稱的“生活醫學化”。指出醫學的這些困境,並不是為了發洩對醫學的怨恨—一種對醫學成功的粗野報復,而僅僅是對醫學力量的認識,這種力量的增長並不完全是無責任的,而是不斷消解目標。儘管此時可能正值醫學的榮光時刻,但也可能是困境的發端。
……正如本書所述故事表明的那樣,我們今天正生活在醫學的重要時期,但這也是充滿懷疑的時期。在過去兩百年裡,特別是在近幾十年,醫學已越來越強大,也越來越成功。然而,面對醫學可能走向何處等諸多問題,社會上存在著深刻的個人焦慮和公眾爭論。透過本書所提供的歷史視角,悖論(越健康長壽,對醫學就越焦慮)即便不能被解決,至少也可以被理解。
|










 2025【精選作文範例】國文(作文)[速成+歷年試題](不動產經紀人)](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0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