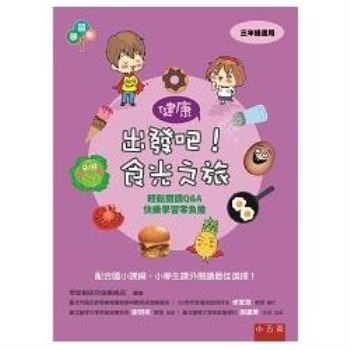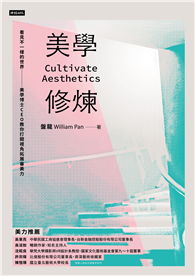《奢侈的閑情》是苗棣先生的自選隨筆集。全書分為兩輯:輯一散文篇,收錄了作者20篇文史雜論,興之所至,新論頻出;輯二的《爻》以通俗筆調寫舊典故,荒誕不經處盡顯動人。入選文章均完成於作者青年時期。在風華正茂之時,讀不着邊際的閑書,寫不着邊際的閑文,故名「奢侈的閑情」。
苗棣1951年生,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現任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早年致力於明清史研究,著有《大明亡國史:崇禎皇帝傳》《庸人治國:大太監魏忠賢與明帝國的末路》等。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從事廣播電視藝術及電視文化學方面的教學和研究。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奢侈的閑情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8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