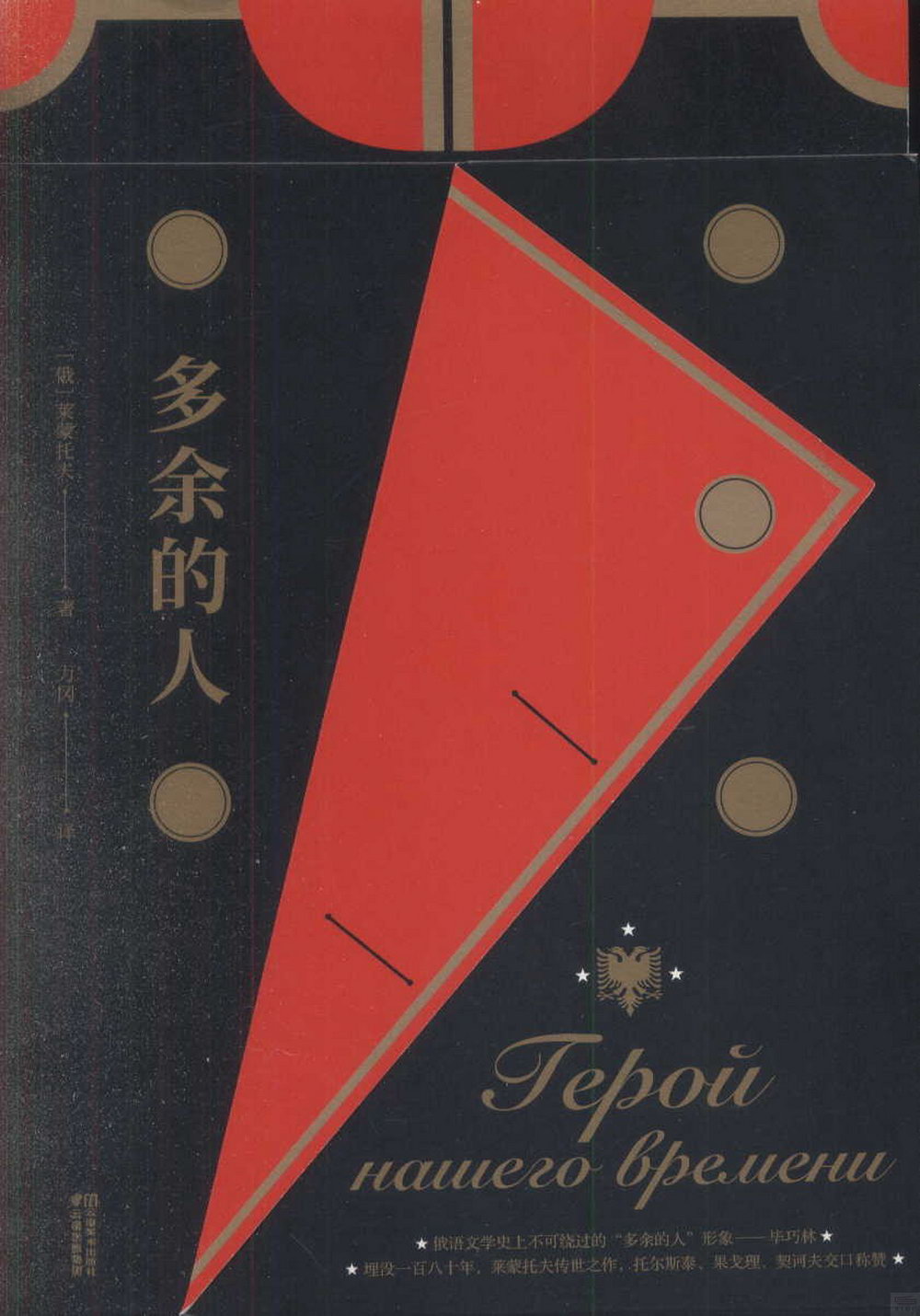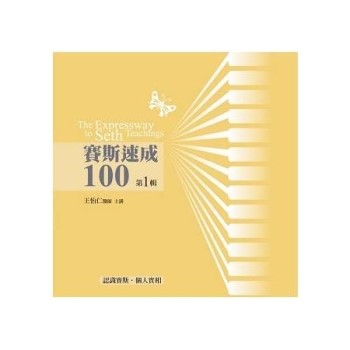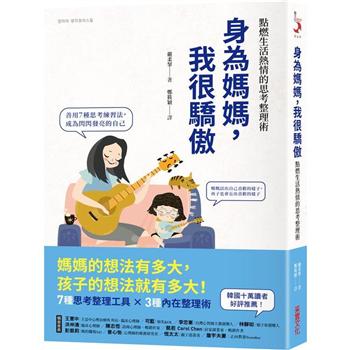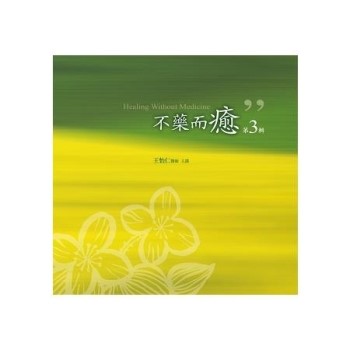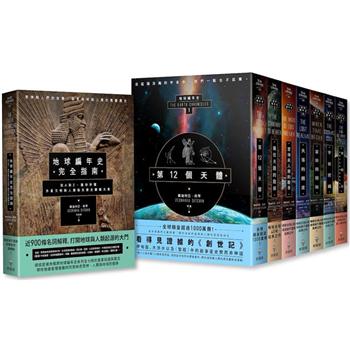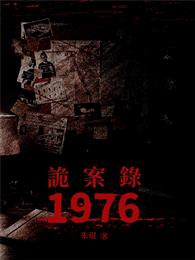求意義的人突然面對無意義的世界,首先表現出兩種心態。聽天由命地接受無意義:頹廢。慷慨激昂地反抗無意義:悲壯。還有第三種心態:厭倦。十九世紀俄國貴族精英知識分子,家有莊園與農奴,生活優裕受到良好教育。在高壓統治下,社會意識初啟蒙,他們空懷一腔熱血,不滿現實、渴望有所作為,卻又屢屢碰壁無力改變階級現狀而變得痛苦、消沉、憤世嫉俗、蔑視一切生活道德規範。
這種不肯接受又不肯反抗的厭倦情緒體現到俄國文學上,是一系列「多餘的人」形象的出現。總是在追求意義,卻總是求而不得。他們不是十惡不赦的壞人,甚至是誠實正直的。所做的任何努力,帶給別人的都是傷害。最終自己的靈魂也在這種深不可測的失落中漸漸被腐蝕掉,變得更加行屍走肉。但這種厭生慕死的心理,似乎很貼近於當下的「小確喪」。
每個時代都有這樣「多餘的人」,因為找不到活著的意義,以致於覺得自己被時代所排斥,是一個可有可不有的人。上承普希金筆下的奧涅金,萊蒙托夫筆下的畢巧林,是不可繞過的一個「多餘的人」形象,濃縮了俄國一整個時代的精神風貌。萊蒙托夫《多餘的人》,是俄國社會心理小說的開端之作,是一部遊記,也是日記、愛情歷險和懺悔錄。
作者:萊蒙托夫,普希金后俄國又一偉大詩人,別林斯基譽其為「民族詩人」生於莫斯科,自幼受到良好教育,通曉多門外語,繪畫天分奇高,考入莫斯科大學,後轉入聖彼得堡近衛軍騎兵士官學校。 因悼念普希金的《詩人之死》,名聲大噪,后被當局多次流放,27歲時,因病移居療養院,與退伍少校決鬥而死。生前僅出版唯一一部詩集和長篇小說《多餘的人》(曾名《當代英雄》),一生經歷與筆下的畢巧林,出奇相似。
譯者:力岡,原名王桂榮,俄蘇文學翻譯家,畢業於哈爾濱外國語專門學校俄語專業,後分配至安徽師範大學任教。在生命最後20年裡,翻譯了近700萬字的俄蘇文學作品,代表譯作:《靜靜的頓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日瓦戈醫生》《白輪船》《多餘的人》《獵人筆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