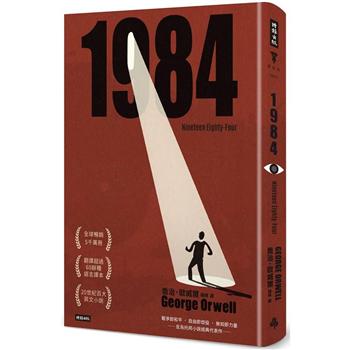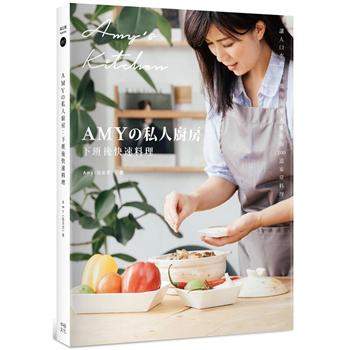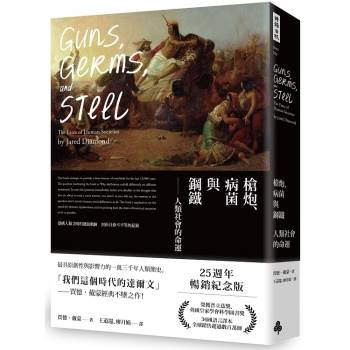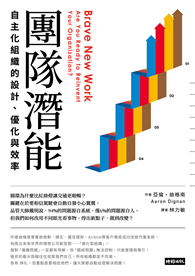《蘇格拉底的第二次審判》是阿蘭·巴迪歐以六幕荒誕戲劇形式呈現的一部哲思著作。
眾所周知,西元前399年,年已七十的蘇格拉底因褻瀆神祇、引進新神論和腐蝕青年思想等罪名被指控,並被判處死刑。按此線索,巴迪歐虛構了蘇格拉底的第二次審判,並將這次審判的時間設置在當代。它的戲劇前提是蘇格拉底並沒有死,他仍在當代扮演著自己的角色。施展著自己的影響力。同時,色諾芬、阿裡斯托芬、柏拉圖等見證人也紛紛在戲劇的魔力下來到當下,並對這次審判進行討論。而這一切,以《革命報》編委會討論第二天報紙頭條要刊登的內容為發端。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蘇格拉底的第二次審判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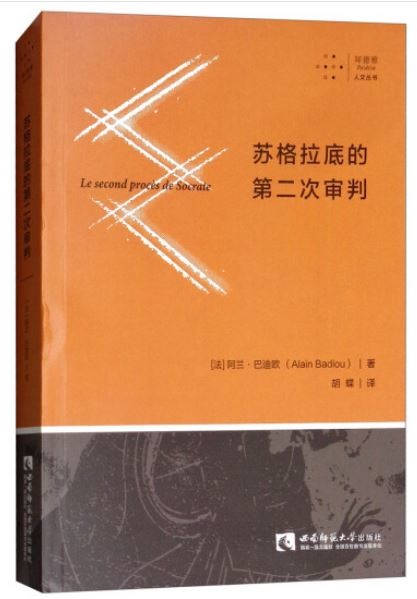 |
蘇格拉底的第二次審判 作者:(法)阿蘭·巴迪歐 出版社: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7-01 語言:簡體中文 規格:平裝 / 189頁 / 32k/ 13 x 19 x 0.95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1-1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蘇格拉底的第二次審判
內容簡介
序
巴迪歐的哲學有四個前提,分別是:科學、藝術、政治和愛。而在藝術這個前提之下,巴迪歐認為有兩種藝術形式,比起其他的,更能夠觸及真理。這兩種藝術就是詩歌和戲劇。巴迪歐對詩歌的摯愛,不用過多贅述,他用他那充滿熱情的文章謳歌著馬拉美、蘭波、佩索阿、聖-瓊·佩斯、策蘭、曼德爾斯塔姆、瓦萊裡,而他們的詩歌,如曼德爾斯塔姆的《世紀》、聖-瓊·佩斯的《遠征》、馬拉美的《骰子—擲》、蘭波的《地獄一季》,都成為巴迪歐作品中被反復徵引的對象。而戲劇,也與巴迪歐的人生經歷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從小時候演出莫里哀的《斯卡班的詭計》開始,到他創作了大量自己的戲劇,從“艾哈邁德四部曲”到新近出版的《蘇格拉底的第二次審判》,巴迪歐都展現了戲劇方面的才華。不僅如此,莫里哀、高乃依、瓦格納、皮蘭德婁、易蔔生、克羅岱爾、布萊希特、貝克特等劇作家也是他所津津樂道的物件,戲劇是巴迪歐所認為的“真正的藝術”,它可以通過其獨特的形式,讓真正的觀念在戲劇中道成肉身。
一、“戲劇”與戲劇
在巴迪歐以尼采式格言體完成的作品《戲劇狂想曲》(Rhapsodie pour le theatre)的開頭,他給出了一個十分有意思的區分:“正如其他所有人都會看到的,將世界分成有戲劇的社會和無戲劇的社會,是一個不錯的區分。”為什麼是戲劇?為什麼用有無戲劇來區分今天的社會?在電影和網路視頻已經遍及我們日常生活各個角落的今天,巴迪歐仍然將戲劇作為我們社會的一個重要尺度,是否有老堂吉訶德用長槍挑戰風車的嫌疑?問題恰恰相反,巴迪歐並不是在一個線性歷史軸上來談論戲劇與電影的關係,事實上,藝術史的發展不儘然是用電影來取代傳統的戲劇,戲劇的存在也不僅僅滿足於為人們敘述了一個情節、一個故事、一段傳奇,而是讓某種不曾發生的東西,在舞臺上,以不斷重複的方式發生。的確,今天也有戲劇,但在巴迪歐看來,這種戲劇更多是帶引號的戲劇,這種以不斷重複既定情節,不斷滿足于讓觀眾陷入猥瑣的歡笑或低廉的眼淚之中的“戲劇”,與電影更具震撼力的視覺傳播和蒙太奇式的敘事方式相比,的確沒有任何優勢。這樣,巴迪歐用作區分的戲劇,絕對不是這種以重複既有秩序為基礎的“戲劇”,而是另一種戲劇,一種可以承載當代哲學和政治觀念的戲劇。不過,在理解巴迪歐的不帶引號的戲劇之前,我們必須理解他如何來闡述他對戲劇的理解。
……
你們的那種主體,永遠不可能通過構築穩固的家園來實現。老房子僅僅是傳統,你們經歷的遊蕩是一個新的方向。那麼,在你們自己的位置上,有一個新的象徵秩序。真正的家園是當思想和行動的冒險讓你遠離家園,並幾乎要忘卻家園的時候,你們可以回歸的地方。你們所待的家園永遠只是一座自願待在那裡的監獄。當生活中某種重大事情發生,仿佛將你們連根拔起,讓你們啟程遠離故土,走向你們真正的生活。遠征是一個觀念,你們迷失了方向,但你們走向你們自己,在迷失方向和背井離鄉中找到了你們真正的自我,找到全部的人性,創造一個平等主義的象徵秩序的階段。
一、“戲劇”與戲劇
在巴迪歐以尼采式格言體完成的作品《戲劇狂想曲》(Rhapsodie pour le theatre)的開頭,他給出了一個十分有意思的區分:“正如其他所有人都會看到的,將世界分成有戲劇的社會和無戲劇的社會,是一個不錯的區分。”為什麼是戲劇?為什麼用有無戲劇來區分今天的社會?在電影和網路視頻已經遍及我們日常生活各個角落的今天,巴迪歐仍然將戲劇作為我們社會的一個重要尺度,是否有老堂吉訶德用長槍挑戰風車的嫌疑?問題恰恰相反,巴迪歐並不是在一個線性歷史軸上來談論戲劇與電影的關係,事實上,藝術史的發展不儘然是用電影來取代傳統的戲劇,戲劇的存在也不僅僅滿足於為人們敘述了一個情節、一個故事、一段傳奇,而是讓某種不曾發生的東西,在舞臺上,以不斷重複的方式發生。的確,今天也有戲劇,但在巴迪歐看來,這種戲劇更多是帶引號的戲劇,這種以不斷重複既定情節,不斷滿足于讓觀眾陷入猥瑣的歡笑或低廉的眼淚之中的“戲劇”,與電影更具震撼力的視覺傳播和蒙太奇式的敘事方式相比,的確沒有任何優勢。這樣,巴迪歐用作區分的戲劇,絕對不是這種以重複既有秩序為基礎的“戲劇”,而是另一種戲劇,一種可以承載當代哲學和政治觀念的戲劇。不過,在理解巴迪歐的不帶引號的戲劇之前,我們必須理解他如何來闡述他對戲劇的理解。
……
你們的那種主體,永遠不可能通過構築穩固的家園來實現。老房子僅僅是傳統,你們經歷的遊蕩是一個新的方向。那麼,在你們自己的位置上,有一個新的象徵秩序。真正的家園是當思想和行動的冒險讓你遠離家園,並幾乎要忘卻家園的時候,你們可以回歸的地方。你們所待的家園永遠只是一座自願待在那裡的監獄。當生活中某種重大事情發生,仿佛將你們連根拔起,讓你們啟程遠離故土,走向你們真正的生活。遠征是一個觀念,你們迷失了方向,但你們走向你們自己,在迷失方向和背井離鄉中找到了你們真正的自我,找到全部的人性,創造一個平等主義的象徵秩序的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