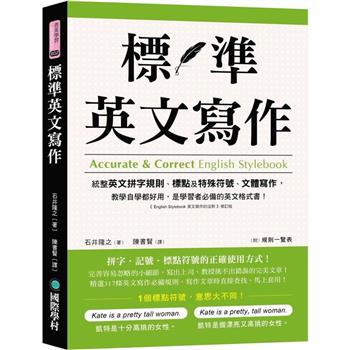浦契尼的《圖蘭朵》每一幕之架構均不同。第一幕之劇情僅自宣旨、故人異地重逢至異國王子報名猜謎為止,和其他的《圖蘭朵》歌劇相較,要簡單得多。然而浦契尼卻不以直線的方式鋪陳,而係以其相當擅長的多層次架構來寫作:以宣旨官宣布解謎不成的波斯 王子將被砍頭,群眾期待行刑、等圖蘭朵現身的群眾場景為背景,在這背景之前演出帖木兒和卡拉富父子異地重逢的劇情,並且輕描淡寫地交待帖木兒身旁侍女柳兒的愛屋及烏之忠心行為。重逢的喜悅亦未被多加著墨,緊接著就是行刑場景,圖蘭朵遠遠地現身,卡拉富愛上她,決定冒死解謎。就場景分配而言,獨唱角色和合唱群眾交互出現在前景,圖蘭朵則不論是否在舞台上,都一直是個很大的陰影,盤踞在後景。然而,在如此的激動中,浦契尼亦適當地建立抒情的暫停段落,卡拉富和柳兒的獨唱將各方激情暫時延宕,之後,又是另一波的激直推到第一幕之浩瀚結束。
如此的多層次架構僅能透過音樂戲劇結構之分析方能理解,在直線進行的宣旨場景之後,合唱團的雜沓段落裡,唱出柳兒請求幫忙的呼聲,而帶人故人異地重逢之場景,而這個過程有一大部分系和劊子手僕人上場之音樂重疊,最後在柳兒的樂句“因為有一天,在宮裡,你曾對我一笑”〈Perche un di nella reg—gia,mi hai sorfiso〉甫落,聲音尚未盡之時,重逢場景就被合唱蓋過去,而告結束。譜例十九為父子重逢後,帖木兒對兒子敘述兩人失散後的遭遇,樂團里之中低音木管樂器和中低音弦樂器支撐著他的敘述,打擊樂器則伴隨著劊子手僕人之上場,在音樂上即形成兩個場景重疊的效果。 不僅在劇本里,在音樂中,浦契尼的《圖蘭朵》亦使用了相當多的中國旋律作為素材。在決定以《圖蘭朵》作為下一個創作目標後,浦契尼即積極地在找尋中國音樂。根據阿搭彌的回憶,1920年8月,浦契尼在一位曾經出使中國的朋友法西尼公爵〈Barone Fassini〉家,聽到一個這位朋友由中國帶回來的音樂盒,其中的音樂後來被用來作為三位大臣的音樂。【Adami Puccim,op.cit.,176;1920年8月15日,浦契尼自BoSni di Lneea,亦即法西尼住處發信給史納柏,亦提到此事,Sch 54,尤其是第87頁之註腳7。】雖然有這麼清楚的提示,但直到70年代裡,美籍旅意音樂學者魏弗〈Winiam Weaver〉左羅馬找到法西尼夫人,她還保有這個已多年未用的音樂盒之後,才證實了這個音樂盒的確是浦契尼的中國旋律來源之一。 …… 插圖…… 書摘2 卜松尼更對觀眾本身之理解能力提出思考: 我還要確定的是,歌劇作為音樂創作應一直由一系列短小完整的曲子組成,並且不應有其他的形式。對由一條線不間斷地編織、連續進行三到四小時的情形,無論是人類的構思或是接受力,都是不夠的。 所以,對歌劇而言,關鍵字是一個難以估計的工具,因為對觀眾而言,面對的是同時觀看、思考和諦聽的工作,一位平常的觀眾〈粗言之,觀眾大部分都是如此〉一次只能做到三樣中的一樣。因此,對位之情形要依所要求的注意力簡單化,當劇情最重要時〈例如決鬥〉,文字與音樂就退居一旁;當一個思想被傳達時,音樂與劇情要留在背景中;當音樂發展其線條時,劇情和文字就得謙卑。歌劇畢竟是集觀看、詩文與音樂於一體的,在其中聲音的和畫面的作用完成的個性,使得它與沒有舞台和沒有音樂亦能存在之話劇戲劇,有著清楚的差異。就因為此,詩文的限制是其條件。 將這些對歌劇的討論推到《圖蘭朵》上,即可看到,在組曲裡已有的關鍵字式的劇情架構以及其音樂內容奠定了歌劇之基礎,歌劇的各曲裡,音樂、劇情和思想各有其不同之比重。在完全的歌唱形式和完全的說話形式之間,卜松尼依音樂、劇情和思想的重要程度,不時變換使用了近似說話的歌唱或讓歌唱過渡至說話等等手法。卜松尼長年地不時思考“圖蘭朵”,終於使其譜寫出歌劇之《圖蘭朵》。在創作期間的一封信,間接地顯示了《魔笛》可能有的影響: 在氣溫急速變化〈絕無僅有的經驗〉中,我再度徹底地研究了《魔笛》的總譜,作為一部令人欽佩的作品,它是——作為一整體——較次於莫扎特的其他東西的。 它在三個段落裡超越了較早的作品——序曲、三位男孩第一次上場的聲響和兩位武裝男士的神秘氣質,此外,相較大家對他的期待,旋律並不會有何差異或較不高貴,而結構上則是草稿性的。夜之後突然開始嘎嘎叫的情形,讓我想到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塔爾教授與費瑟博士的系統》〈The System of Prof.Tarr and Dr.Fether〉。但是那高度簡單地解決此種問題的方式又讓人驚訝。 我個人認為此種以對外向的偏好,創造一種冷靜安詳的藝術之拉丁美德,更為清新。【1915年12月6日,給Egon Petri,Selected Lctter, op.cit.,NO.191。】 而《魔笛》正是卜松尼歌劇美學的典範: 我只能想到唯一的一部和此理念最相近的例子,就是《魔笛》。在其中,它綜合了教育的、場面的、神聖的和娛樂的於一身,並且還加上一個束縛著的音樂,或者更清楚地說,飄浮於其上並將其綜合在一起的音樂。依我的感覺,《魔笛》“就是”歌劇,並且很驚訝地看到,它,至少在德國,竟未能成為歌劇發展的指標!……施康內德〈Emanuel Schikaneder〉懂得如何思考一個文字內容,其中有音樂,並且能將音樂挑戰出來。僅魔笛和魔鈴就是音樂的、導引聲音的元素。但是除此之外,三位女士的聲音、三位兒童的聲音是如何聰明地被置入劇本里,“奇蹟”如何吸引來音樂,“火與水的試驗” 如何依著聲音的誓言魔力放置,兩位武裝的守衛者在大門前的警告,系成於一首古老聖詠曲的節奏上!在這裡,觀賞、道德和劇情攜手並進,以在音樂中刻下結合的印章。……【En-twurf eines Vorwortes zur Partitur des“Doktor Faust”…,Op.cit.。】早在組曲時代的一頁草稿裡,就可看到以後之歌劇和《魔笛》之相似性: 相當導奏:殘忍的〈劃掉改以〉陰鬱的畫面,在開始時 三個謎 愛情與美麗 經過掙紮成為 歡喜與解答 此外:個性的 阿拉伯進行曲與舞蹈音樂 面具的喜劇性 主題“東方” ……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浦契尼的圖蘭朵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浦契尼的圖蘭朵
圖蘭朵,遠遠不止是一個中國公主招親的故事,在西方人眼中,它更多的,似乎是神秘幽遠的國度的謎一樣的文化展現。本書主要呈現這個童話故事如何成為一部跨越時空的音樂劇場藝術作品,讓美麗的童話和神秘的東方令人神往。
作者簡介:
羅基敏,德國海德堡大學音樂學博士,中國台灣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及音樂研究所副教授。
梅樂亙,瑞士伯恩大學音樂博士,柏林自由大學及“浦契尼研究中心”主持人,並曾作曲及導演歌劇。
章節試閱
浦契尼的《圖蘭朵》每一幕之架構均不同。第一幕之劇情僅自宣旨、故人異地重逢至異國王子報名猜謎為止,和其他的《圖蘭朵》歌劇相較,要簡單得多。然而浦契尼卻不以直線的方式鋪陳,而係以其相當擅長的多層次架構來寫作:以宣旨官宣布解謎不成的波斯 王子將被砍頭,群眾期待行刑、等圖蘭朵現身的群眾場景為背景,在這背景之前演出帖木兒和卡拉富父子異地重逢的劇情,並且輕描淡寫地交待帖木兒身旁侍女柳兒的愛屋及烏之忠心行為。重逢的喜悅亦未被多加著墨,緊接著就是行刑場景,圖蘭朵遠遠地現身,卡拉富愛上她,決定冒死解謎。就場景分配...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縮寫符號說明
劇情大意
浦契尼歌劇作品簡表
浦契尼與他的時代(代序)
第一章浦契尼之《圖蘭朵》與20世紀劇場美學
第二章由童話到歌劇:“圖蘭朵”與19世紀的《圖蘭朵》歌劇
一、“圖蘭朵”的誕生
二、由戲劇到歌劇――19世紀的《圖蘭朵》歌劇
第三章卜松尼的《圖蘭朵》:一部劇場童話
一、組曲―劇樂―歌劇:卜松尼的“圖蘭朵”緣
二、組曲與歌劇之音樂戲劇結構關係
三、卜松尼《圖蘭朵》之異國情調
四、《圖蘭朵》與《魔笛》:卜松尼的音樂劇場美學
第四章《圖蘭朵》:浦契尼的天鵝之歌
一、孕育至難產
二、音樂戲劇結構
三、兩幕與三幕的《...
劇情大意
浦契尼歌劇作品簡表
浦契尼與他的時代(代序)
第一章浦契尼之《圖蘭朵》與20世紀劇場美學
第二章由童話到歌劇:“圖蘭朵”與19世紀的《圖蘭朵》歌劇
一、“圖蘭朵”的誕生
二、由戲劇到歌劇――19世紀的《圖蘭朵》歌劇
第三章卜松尼的《圖蘭朵》:一部劇場童話
一、組曲―劇樂―歌劇:卜松尼的“圖蘭朵”緣
二、組曲與歌劇之音樂戲劇結構關係
三、卜松尼《圖蘭朵》之異國情調
四、《圖蘭朵》與《魔笛》:卜松尼的音樂劇場美學
第四章《圖蘭朵》:浦契尼的天鵝之歌
一、孕育至難產
二、音樂戲劇結構
三、兩幕與三幕的《...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