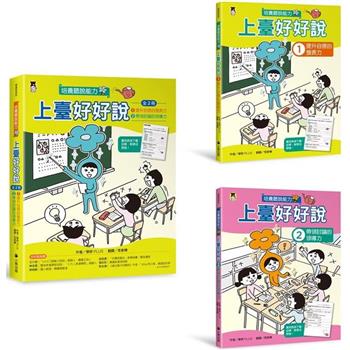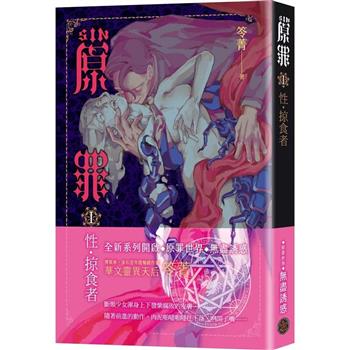修生學兄新著《元雜劇史》出版了。他囑我談點感受。我雖淺陋,但也略知著述的甘苦,知道這部著作的分量,本著向他學習的精神,便欣然從命了。 我和修生學兄相知多年了。記得在打倒“四人幫”以後,游國恩等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準備重新出版。當時,修生兄等一批參加該書修訂的年富力強的學者,集中在中山大學,和王季思老師一起研究修改方案。趁此機會,中山大學中文系師生邀請修生兄作了學術報告。那一天,教室裡座無虛席,氣氛熱烈。修生兄聲音洪亮,神態從容,條分縷析,新見迭出,使同學們大開眼界。我坐在後座,仔細聆聽,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記得聽課後,季思老師囑我認真向兄弟院校的同輩學者學習。我自知一向浮躁,更應多向嚴謹沉穩、功底扎實的修生兄求教。此後,我們又都擔任過中文系主任。常有機會在工作會議和學術會議上聚首,接觸愈多,愈感到修生兄為人處事的作風與其治學態度如出一轍。他的許多長處,正是我所不足。在切磋的過程中,我常受啟發。獲益良多。修生學兄新著《元雜劇史》出版了。他囑我談點感受。我雖淺陋,但也略知著述的甘苦,知道這部著作的分量,本著向他學習的精神,便欣然從命了。<br> 我和修生學兄相知多年了。記得在打倒“四人幫”以後,游國恩等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準備重新出版。當時,修生兄等一批參加該書修訂的年富力強的學者,集中在中山大學,和王季思老師一起研究修改方案。趁此機會,中山大學中文系師生邀請修生兄作了學術報告。那一天,教室裡座無虛席,氣氛熱烈。修生兄聲音洪亮,神態從容,條分縷析,新見迭出,使同學們大開眼界。我坐在後座,仔細聆聽,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記得聽課後,季思老師囑我認真向兄弟院校的同輩學者學習。我自知一向浮躁,更應多向嚴謹沉穩、功底扎實的修生兄求教。此後,我們又都擔任過中文系主任。常有機會在工作會議和學術會議上聚首,接觸愈多,愈感到修生兄為人處事的作風與其治學態度如出一轍。他的許多長處,正是我所不足。在切磋的過程中,我常受啟發。獲益良多。<br> 近幾年,修生兄致力於元代文學的研究。一方面,他對白朴等重要作家深入鑽研;一方面,作為《全元文》的主編,他對整個時代的文獻資料全面掌握。正因為有了長期的學術積累,所以,他對元代戲劇發展的種種判斷,就顯得準確,更有系統性,更有說服力。我曾讀到他在《文學遺產》發表的有關元劇分期的論文,深感他搜集的資料十分豐富,思考比以前更加周密。而當我知道他決定動筆編寫《元雜劇史》一書時,對他在學術上的“戰略部署”,似乎又有所領悟。他從點到面,博約結合,鍥而不捨,持之以恆,於是結出了碩果。當然,這一部署,也可以說是“有計劃,有步驟,有組織”的陽謀。然而,作為一個學者,如果沒有長遠的目光,只計較一時一事的得失,又怎能卓有所成,寫出扎實的論著?現在,《元雜劇史》的出版,標幟著修生兄的學術水準,又登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按照他的性格,我知道,他不會到此為止。《元雜劇史》的完成,將是他下一步成功的開端。<br> 近幾年,學術界對古代戲劇的研究,似乎處在“卡殼”的階段。有些論著,不能說寫得不深不細,但始終在幾十年耕築的框架上徘徊,學術水準沒有新的進展。究其原因,我想,很可能是由於研究者沒有擺脫過去蘇歐戲劇觀念的約束,依然以蘇歐的話劇理論,作為分析評價中國戲曲的依據。例如,在剖析戲曲作品時,往往只著意於捕捉戲劇矛盾,抓住人物性格的衝突,審視矛盾的契機。這樣做,自然是必要的,但卻不能解決中國戲曲評論的全部問題。因為我國的古代戲曲,既是“戲”,也是“曲”。所謂“曲”,實即詩。在劇作中,“曲”占著極其重要的位置。加上戲曲作家,往往就是詩人,當他們安排關目,表現人物的時候,不可能不受到詩歌創作特有的思維方式的影響。而詩歌創作,最重“意境”,注重作者的主觀情意與客觀景物相融合,從而誘導讀者產生聯想,參與創造,體驗形象之外的涵義。以我看,戲曲作家特別是雜劇劇作家,有不少人致力於意境的追求。<br> 這本書原是80年代在學校講選修課的講稿。<br> 這本書是為中文系學生編寫,自然偏重文學方面,但戲曲是一門綜合藝術,劇場及其他藝術因素也應給予一定注意。顯示全部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