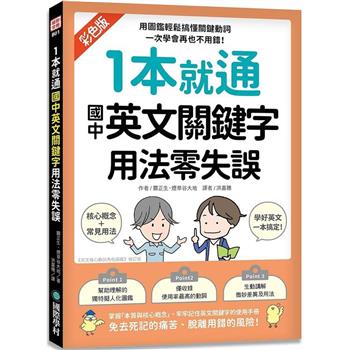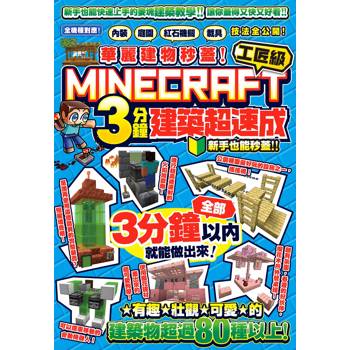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有名人物無名氏:阮義忠經典攝影集的圖書 |
 |
有名人物無名氏: 阮義忠經典攝影集 作者:阮義忠 出版社:攝影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1-05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192頁 / 29.5 x 29.5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422 |
攝影 |
$ 1422 |
攝影集 |
$ 1620 |
攝影作品集 |
$ 1620 |
藝術設計 |
$ 1674 |
中文書 |
$ 1674 |
攝影 |
$ 1710 |
各類攝影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有名人物無名氏:阮義忠經典攝影集
《有名人物無名氏》這本專輯的作品,橫跨了二十世紀70和80年代,那個充滿文藝復興氣息和理想色彩的時空。人物的涵蓋面雖然廣闊,但卻有一個明顯的向度:對生活本身的熱情,對個人工作的專注,對生命價值的追尋。美麗、單純而浪漫。這些人物,多半都有一個自覺的信念,也大都有著貫徹這一信念的行動力。那時候,金錢物質的壓力、血緣地緣的分歧,還不曾像今天這般焚燒我們的社會和人心,也沒有那麼多複雜的、現實的、功利的考量。這些人在各個不同的角落裡奮鬥、摸索,一點一滴地為台灣的願景打底,為人文的風貌用心用力的素描。回歸和認同,參與和服務,傳承和創造,共鳴著他們抑揚的音色。
--高信疆
作者簡介:
一九五○年出生於台灣宜蘭。早年曾任《幼獅文藝》編輯,退伍後任職《漢聲》雜誌英文版,開始攝影生涯。一九七五年轉任《家庭月刊》攝影,同時撰寫本土攝影報導文章。一九八一年,由攝影跨行到電視節目製作,以紀錄片《映象之旅》等廣為人知。一九八八年起任教於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長達二十五年。
三十多年來,阮義忠跋山涉水,深入鄉土民間,尋找動人細節,拍攝了大量以百姓日常生活為題材的珍貴照片,作品也成了台灣獨一無二的民間生活史冊。
著作豐富,出版《想見,看見,聽見:走出鏡頭之外》《想念亞美尼亞》《失落的優雅》《正方形的鄉愁》《北埔》《八尺門》《人與土地》《台北謠言》《四季》……等;論著《當代攝影大師》《當代攝影新銳》被視為海峽兩岸的攝影教育啟蒙書;創辦的《攝影家》雜誌(1992-2004)被譽為攝影史上最具人文精神的刊物之一。阮義忠攝影作品為海內外重要機構展出及收藏。多年來深刻且廣泛影響全球華人地區的攝影視野。
2016年成立阮義忠攝影人文獎
2017年回家鄉宜蘭設立阮義忠台灣故事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