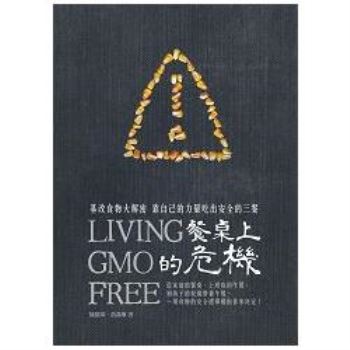隱沒於小說、詩篇閒暇情趣下的帝國主義
從十九世紀以迄二十世紀初,西方列強建立了從澳大利亞直抵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帝國,在此同時,西方文藝大師也創造了從《曼斯斐爾公園》以至《黑暗之心》和《阿伊達》等傑作。然而,大部分的文化批評家仍視其為兩個互相分離的現象。
薩依德繼《東方主義》之後所寫的這本里程碑式的鉅作,精心構築了西方帝國之野心與其文化之間戲劇性的關聯,兩者相互輝映、相互增強。他以十九、二十世紀的小說敘事為分析對象,從艾略特、康拉德開始,一一檢視了葉慈、阿契比、魯西迪等作家的作品,以顯示被支配的臣民如何產生屬於他們自己的反對與抗拒之充滿盎然生機的文化。同時,薩依德也論及音樂(如《阿伊達》)、藝術與美學表達(如現代主義)等其他領域。
薩依德的重點是要將「帝國主義」的威權及其餘緒加以鋪陳,顯出帝國主義作為普遍的文化領域,充斥著特殊的政治、意識型態、經濟、社會力道。因此,隱沒於浪漫小說、詩篇閒暇情趣之下奴役及殖民體制,也就在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及其歷史脈絡中重現其意涵。
如此寬廣的視域與令人驚異的博學,《文化與帝國主義》再度開啟了文學與時代生命的對話。
作者簡介: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
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文學與文化評論大師、後殖民思潮先驅、也是一位特立獨行的集大成人物。薩依德1935年出生於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1950年代赴美國,取得哈佛大學博士,1963年起任教哥倫比亞大學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所,這位知名的巴裔美籍學者,也公認為是巴勒斯坦獨立運動在西方最雄辯的代言人。2003年9月24日薩依德因白血病逝世。
薩依德著作等身,尤以「中東三部曲」:《東方主義》(Orientalism)、《巴勒斯坦問題》(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遮蔽的伊斯蘭》(Covering Islam)開啟「東方學論述」場域,影響了整個西方對東方研究的思考與研究的方向。薩依德尚著有《世界‧文本‧批評者》(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以及他的回憶錄《鄉關何處》(Out of Place)等書。其作品已被譯為二十四國語言,並在歐洲、亞洲、非洲、澳洲等地區出版。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薩依德持續其獨特與極為重要的批判作品。有時當文學批評逐漸變成一種奧祕的遊戲之際,薩依德強調它和今日世界整體所面臨的巨大問題息息相關,且以萬鈞之力討論探索誠實的知識份子所需要的態度上之根本轉變。
-法蘭克.凱默德(Frank Kermode)
媒體推薦:
真知灼見的……至始至終都是如此引人入勝……薩依德對個別小說的評價展現出淵博的學識和對文學真誠的熱情……。這部作品以緊湊逼人的寫作方式提出對此一領域的更迫切需要之綜合,其他批評家無人能及,薩依德使他自己卓然特出。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文化與帝國主義》具有其他文學批評著作中罕見的雄辯式與迫人之主題風格……他的學養具全球性的視野……挑戰並激發了我們對所有知性領域的新思維。他是一位具有深刻情感和倫理想像的人。
-卡蜜兒.帕格里奧(Camille Paglia), 《華盛頓郵報書香世界》(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文化與帝國主義》對其主題提供一個深刻、綜合、敏銳而詳細的說明。假如人們必須仰賴有關帝國文化的任何單本之材料書的話,當然就是這本百科全書式的研究作品,它極實際地觸及歐洲現代史的每件重大的帝國冒險行動,並且以史無前例的細膩性集中探討十九世紀法國和英國殖民系統的精心謀略,橫跨從小說、詩歌、歌劇至當代大眾媒體的文化生產之領域……一部巧思、大膽和迫切需要的作品。
-《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
名人推薦: 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薩依德持續其獨特與極為重要的批判作品。有時當文學批評逐漸變成一種奧祕的遊戲之際,薩依德強調它和今日世界整體所面臨的巨大問題息息相關,且以萬鈞之力討論探索誠實的知識份子所需要的態度上之根本轉變。
-法蘭克.凱默德(Frank Kermode)媒體推薦: 真知灼見的……至始至終都是如此引人入勝……薩依德對個別小說的評價展現出淵博的學識和對文學真誠的熱情……。這部作品以緊湊逼人的寫作方式提出對此一領域的更迫切需要之綜合,其他批評家無人能及,薩依德使他自己卓然特出。
-《紐約時...
目錄
英文版相關評論
<導讀> 對抗西方霸權 ◎廖炳惠
<譯序> 流亡、認同與永恆的他者 ◎蔡源林
導論
I重疊的領土、交織的歷史
1帝國、地理與文化
2過去的影像
3黑暗之心的兩種視線
4差異的經驗
5串聯帝國與世俗的詮釋
II凝聚的景象
1敘述和社會空間
2珍.奧斯汀與帝國
3帝國的文化嚴整性
4運作中的帝國:威爾第的《阿依達》
5帝國主義的享樂
6掌控下的土著
7卡繆和法國的帝國經驗
8對現代主義的一個註腳
III抵抗與反叛
1兩面性
2反抗文化主題
3葉慈和去殖民化
4心路歷程與反對勢力的出現
5勾結、獨立與解放
Ⅳ未來:源自宰制的自由
1美國勢力之上揚:公共領域之論戰
2挑戰正統與權威
3運動與移民
英文版相關評論
<導讀> 對抗西方霸權 ◎廖炳惠
<譯序> 流亡、認同與永恆的他者 ◎蔡源林
導論
I重疊的領土、交織的歷史
1帝國、地理與文化
2過去的影像
3黑暗之心的兩種視線
4差異的經驗
5串聯帝國與世俗的詮釋
II凝聚的景象
1敘述和社會空間
2珍.奧斯汀與帝國
3帝國的文化嚴整性
4運作中的帝國:威爾第的《阿依達》
5帝國主義的享樂
6掌控下的土著
7卡繆和法國的帝國經驗
8對現代主義的一個註腳
III抵抗與反叛
1兩面性
2反抗文化主題
3葉慈和去殖民化
4心路歷程與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