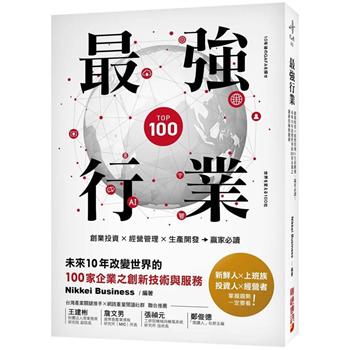【摘文1】Chapter1 住在栗樹巷的人
查爾斯先生的頭頂有晒傷的痕跡,這是我在他巡視玫瑰叢的時候發現的。他會仔細檢查每一朵玫瑰、搖晃一下比較大的花朵看看花瓣是否掉落,然後繼續慢慢前進。他頭上那一大塊光禿禿的地方現在變成了一塊發亮的粉紅色圓頂,周圍有蓬鬆的白髮圍繞。天氣這麼熱,他應該戴帽子的,但是我想當你很專心的時候,應該很難注意頭頂上的高溫。
不過我就注意到了。
從這個窗戶,我注意到很多事情。
我可不是在做壞事,我只是喜歡觀察鄰居來打發時間,我想鄰居應該不會介意。有時候,住在五號的傑克.畢夏會對我吆喝「怪咖」、「怪胎」或「肖仔」,他很久沒有叫我馬修了,不過在我心裡他就是個白癡,所以我不是很在意他說了什麼。
我家位在一條安靜的死巷裡,鎮上的人都很慶幸自己不是住在又大又臭的倫敦市區,可是每天早上他們卻拚了命的擠進去。
這條巷子裡有七間房子,其中有六間長得一樣,都有向外凸出的方形窗戶、內嵌玻璃的大門,以及白色的外牆,但是夾在三號跟五號中間的那棟房子卻長得很不一樣,它是用血紅色的磚塊砌成,座落在這些白色房子當中,看起來就像參加了一場沒人想要變裝的萬聖節派對。那間房子的黑色大門上方有兩扇三角形的窗戶,都被人從裡面用紙板遮了起來,不曉得是為了擋風還是要避免被人偷窺。
爸告訴我,二十年前建商在蓋我們的房子時,曾經想要拆掉那間牧師宅,但是它還是憑著自己百年的歷史想辦法存活了下來,就像一顆蛀壞的舊牙齒。牧師過世後,他的妻子老妮娜依然住在那裡,不過我很少看到她。她有一盞桌燈,就放在客廳的灰色窗簾後面,無論白天、晚上都亮著橘色的光。媽說她刻意保持低調,以免教堂的人在她丈夫死後請她搬走,畢竟這不是她的房子。她的門階上有三盆花,她固定在每天早上10:00出來澆花。
我是從家裡前側的空房間觀察老妮娜和其他鄰居的,我喜歡這個房間。檸檬黃的牆壁十分清爽乾淨,即使過了五年依然有剛粉刷過的感覺。爸媽都叫這間房間「辦公室」,因為這裡是放電腦的地方,但是事實上,它原本的功能是「育嬰房」。媽在角落的一堆盒子和購物袋上放了一串嬰兒吊飾,垂著六隻填充的條紋大象娃娃,那是有一次她逛街購物一整天之後帶回來裝上的,不過爸覺得那個東西不吉利。
「別迷信了,布萊恩,我們要確認東西是好的啊。」
當她轉動上面的小鑰匙,我們就會看著大象隨著〈一閃一閃亮晶晶〉這首歌轉圈圈。我會在音樂停止後高興得拍手,那時候的我只有七歲,就是個傻乎乎的年紀。媽說她會找時間拆開她買回來的那些東西,但是她根本沒有這麼做。那些東西完全沒有人動過,尿布、奶瓶、嬰兒監視器、消毒鍋、小背心,這些都是給我弟弟用的,如果我沒有……嗯,如果他還活著的話。
這個房間有個面向街道的窗戶,我會從那裡觀察鄰居的早晨活動:
上午9:30
查爾斯先生又把凋謝的玫瑰剪掉了。他用了一把新的紅柄剪刀,晒傷的頭頂看起來很痛。
查爾斯先生的年紀大約在六十五到九十五歲之間,因為他看起來好像不會變老。我想他應該是活到了一個他很喜歡的年紀,就決定停止老化。
上午9:36
戈登和潘妮.蘇利文從一號的房子走了出來。戈登上了車,潘妮則向對面的查爾斯先生揮揮手。
查爾斯先生也向潘妮揮手,並像牛仔那樣旋轉手上的剪刀,還對著空氣剪了三下,銀色的刀片在陽光底下閃閃發亮。這個動作把潘妮給逗笑了,她瞇起眼睛,用手遮住眼前的強光,但是臉卻沉了下來──她看到我了。查爾斯先生也順著她的視線,發現我正從窗戶看著他們。我馬上閃到一旁、躲開他們的視線,心臟猛烈的砰砰跳。聽見戈登把車倒出私人車道的聲音後,我才再度回到窗前。
上午9:42
潘妮和戈登出門,前往超市進行每週一次的採購。
上午9:44
梅樂蒂.柏德走出三號的大門,拖著家裡養的臘腸狗法蘭基。
今天是週末,代表輪到梅樂蒂去遛狗了。週間的遛狗工作都是由她媽媽克勞蒂亞負責,但是我不懂她們幹麼這麼麻煩,因為在我看來,法蘭基每一次都很不開心,一路上只想回家。梅樂蒂邊走邊拉扯黑色針織衫袖子上的毛線,每走三步就停下來等狗狗跟上。那件黑色針織衫就像長在她身上一樣,即使外面有三十度的高溫也依然穿著它。他們停在路燈下,法蘭基在那嗅了一會兒,然後挖挖土,接著就想跑回家。但是梅樂蒂繼續拉著牠往前走,他們的身影逐漸消失在那條通往牧師宅後方墓園的小巷裡。
上午9:50
七號的門打開了,是那對「新婚夫妻」。
詹金斯先生和他的太太漢娜住在我們隔壁,我們兩家之間並沒有相連。雖然他們已經結婚將近四年,這條巷子的居民還是稱他們為「新婚夫妻」。漢娜總是滿臉笑容,並不知道有人在偷看她。
「在這麼熱的天氣跑步不好吧,羅瑞。」她說,臉上依然帶著笑容。
詹金斯先生沒有理她,繼續舉著手側彎伸展。詹金斯先生是我們學校的體育老師,他覺得不運動的人根本沒有必要存在這個世界上。在他眼裡,我絕對是「小人物」的類型,我也盡量避免引起他的注意。
他身穿白色緊身衣和藍色短褲、手插著腰,在他家的走道上一步一步的深蹲。
「別去太久喔,」漢娜說,「我們還要決定要買哪種兒童安全座椅。」
詹金斯先生低聲回應。我低頭看向門前的台階,當我看到漢娜懷孕的大肚子時,緊張的瑟縮了起來。她把手放在肚子上,規律的輕拍著,然後轉身走進家門,我這才吐出剛剛憋住的氣。
詹金斯先生往商店街走去,並且跟查爾斯先生揮揮手,不過查爾斯先生正忙著弄花,所以沒有注意到他。查爾斯先生仔細查看每一朵玫瑰,它們隨風搖曳的樣子好像露天市集裡賣的棉花糖。如果有花朵沒有達到他的標準,就會被喀嚓剪去、丟進塑膠桶。整理完玫瑰叢之後,他就會帶著那桶玫瑰屍體走回去。
上午10:00
沒看到老妮娜出來澆花。
不過以這條巷子今天早上的熱鬧程度來看,她沒有出現也不奇怪。
五號的門打開了,有一個跟我年紀差不多的男孩出現。他走在他家的私人車道上,眼睛盯著一個方向──我的方向。這次我並沒有閃躲,而是穩穩的站在原地回瞪他。他走到我家前面,抬起頭並從喉嚨裡發出奇怪的聲音,然後往我家的走道吐了一大口痰。我暫時忽略噁心感,緩緩的對他拍了拍手。他看到我的手之後皺起眉頭,我趕快把手收回來,接著,他往我家牆上用力踢了一腳就轉身離開了。
上午10:03
傑克.畢夏出現了,還是一樣混蛋。
傑克離開之後就沒有什麼好看的了。詹金斯先生跑步回來,白色的T恤吸滿了汗;蘇利文夫婦從後車廂提了十一袋東西回來;梅樂蒂單手抱著法蘭基散步回來,那條狗看起來對這樣的結果感到非常滿意。
巷子又回歸平靜。
直到牧師宅的大門緩緩開啟。幹嘛
上午10:40
老妮娜站在台階上,一隻手拿著銀色的澆水壺,看起來十分緊張。
這位年邁的女士穿著黑色裙子、奶油色上衣,還有桃色針織衫,她讓水慢慢的流進花盆,數到五就換下一盆。澆花的同時,她的眼神在巷子裡來回游移。正當她要澆最後一盆花的時候,有一輛車轉進了這條巷子,於是她立刻放下澆水壺、溜回家裡並甩上沉重的大門。
那台緩緩移動的車就是爸說「貴得像一間房子」的那種,顯然不是這些鄰居的車。它乾淨得發亮,我可以在它經過的時候從黑色的車門看見我家房子的倒影。車子在十一號前面停了下來,我趕緊拿起筆記本,等待車門打開。
上午10:45
巷子裡有一台我從來沒有見過的超高檔黑色轎車,就停在隔壁!是查爾斯先生的訪客嗎?
這可有趣了。我對鄰居的作息可說是一清二楚,但是現在似乎有陌生人來到這條巷子作客。我想從車子裡的狀況獲得一些線索,但是車窗的顏色太深了,看不出所以然。車停好後,引擎又繼續靜靜的運轉了一陣子才熄火,接著,駕駛座的車門打開了。
有個女人走下車來並環顧了這條巷子一圈。她戴著一副超級大的墨鏡,遮住了大部分的臉龐。她撥了撥臉上的頭髮、甩上車門。這時候,查爾斯先生出現了,他快步走出車道,手在衣服前面抹了抹。
「親愛的!」他說,同時伸出了晒黑的手臂。
「哈囉,爸爸。」
她保留了一點兩個人之間的距離,讓查爾斯先生親吻臉頰,接著回去打開車子後座。一個大約六、七歲的小女孩從車上爬了下來,手裡抱著一個陶瓷娃娃。我貼近窗戶,但是只聽得見幾個字。
「妳一定是凱西!那這位是誰呢?她要留下來嗎?」
查爾斯先生伸手想要摸摸娃娃的頭髮,但是小女孩轉來轉去的所以沒有摸到。那個娃娃看起來就像從古董店買來的,不像一般的玩具。戴著大墨鏡的女人從後座抱出一位金髮男孩,把他放在人行道上,查爾斯先生向他伸出手。
「很高興見到你,泰迪,我是外公。」看著眼前布滿皺紋的手,小男孩用臉頰磨蹭著緊緊抱著的灰藍色毯子一角查爾斯先生的手尷尬的懸在空中,沒多久就放棄了,跑去幫忙拿女兒的行李。他們背對著我交談了一陣子,但是我聽不見內容。
那個女人把兩個黑色旅行箱放在柵門邊,摸著兩個孩子的臉龐跟他們說話,然後親吻他們。她捏了捏查爾斯先生的手臂後回到車上,引擎再度發出低沈的運轉聲。閃亮的黑色轎車緩緩駛離,三個人站著目送她,直到車子消失在視線之外。
「好了,我們進去吧。」
查爾斯先生揮舞著手臂示意要兩個孩子進屋子裡,接著就像趕綿羊一樣把他們趕進屋子、臉上露出了誇張的笑容。小男孩在走道旁的一朵玫瑰前停了下來,繼續用臉頰摩蹭著毯子。
「啊啊啊,不可以摸!」外公說著並再度揮手要他們進屋去。
一分鐘後,查爾斯先生又走了出來,把兩個旅行箱拉在身後。他往上瞥了我一眼,我立刻閃開,但是也注意到他臉上的笑容已經消失殆盡。
【摘文2】Chapter2 床底下的祕密盒
我的床底下有個祕密盒。
我會想要這樣形容它:
那是我在院子裡挖到的一個神祕老木箱,我偷偷摸摸的把它帶上樓、放在床底下,用垂下的床單遮住,讓它靜靜的待在那裡、守護裡面的寶物。只要我認為你值得信任,你就可以跪在我旁邊看著我打開它。這時候可能會有乾掉的泥塊從鬆動的蓋子掉到地毯上,但是我可以暫時不去在意,因為箱子裡的寶物會讓你看得瞠目結舌。
真希望這是我的祕密盒,可惜它不是。
事實上,我的盒子裡裝的是醫療用品。它是由白色和灰色的硬紙板做成的,外型和大小就像一個小鞋盒,上面有個橢圓形的洞。盒子側面印著製造商的名稱,靠近底部的角落有黑色的粗體字寫著:「數量:100」。
但是裡面大概只剩下三十個。
我說「大概」,其實是很肯定的意思,裡面就只剩下三十個。
媽知道我的祕密盒,但是爸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一定會生氣,他不見得會對我生氣,但是會氣媽「鼓勵我」用這種東西。
「這樣不行,席拉。妳為什麼要給他那種東西?這樣只會讓他愈來愈糟。」
這就是爸會有的反應。
他不了解,如果我在某些時刻沒有這種東西,人生對我來說真的太難了。
我跟床底下的祕密盒就住在栗樹巷九號,這是一間非常普通的半獨立式房屋,有三間臥室、一間浴室、一個餐廚空間,還有一個方形的後花園(但是幾乎都是雜草),那裡有儲藏室和玻璃屋。玻璃屋裡原本有一張柳編沙發和同款的扶手椅,但是最近換成了一張新的撞球桌。幾個星期以前,我從房間看著送貨員努力把撞球桌擠進大門,從那天開始,爸每天都會問我要不要跟他較量一下。
但我一點也不想。
如果玻璃屋屋頂的遮光簾沒有拉上,從我房間的窗戶往下看,就可以看到爸獨自一人在打撞球。爸昨天就抓到我在看他,雖然我馬上躲到窗簾後面,但是不到五十秒,我的房門就砰砰作響。
「兒子,怎麼不下來呢?陪你爸玩一場吧!」
「改天吧,謝了!」
然後他就離開了。我知道他的目的,但老實說,撞球?這個點子是從哪裡來的?我已經決定,絕對、絕對不會再踏進那間玻璃屋一步。我們的貓奈吉不知道在那冰冷的白色磁磚上吐出了多少鳥和老鼠內臟,你能想像有多少東西會在那裡爬來爬去嗎?夏天的熱氣還會讓病菌在整個玻璃屋裡到處翻滾。而且彷彿是為了徹底擊潰我想跟爸一起玩的任何小小衝動,撞球桌已經成為奈吉最喜歡的午睡地點。牠每天都在那塊綠色的布面上伸展著,似乎要把自己獻給撞球桌上的眾神。唯一能把那張桌子弄乾淨的方法就是噴滿消毒水,但是我可沒有笨到真的這麼做,因為那張桌子花了爸不少錢。
這間房子最棒的地方就是我的房間,這裡很安全、沒有病菌。出了我的房間到處都是危險,大家都不了解,有灰塵就代表有細菌,有細菌就會生病,生病了就會死掉。仔細想想,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我不容許有任何一點差錯,而在我的房間,我就能掌控一切。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緊盯房子裡的一切。
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房間裡,這代表我對這個環境瞭若指掌,舉例來說:
‧床頭櫃前側右腳鬆動了,還有一點傾斜。
‧窗台底部的油漆剝落了,經常打掃肯定會更嚴重。
‧當你從某個角度看床鋪上方的某一處,那裡的壁紙看起來就像一隻獅子。
不是「森林之王」那種兇猛的獅子,而是看起來有點好笑、沒有牙齒的獅子。牠的鬃毛凌亂、鼻子又長又扁、眼皮也垂垂的。我想,如果你身上壓著一張十年的舊壁紙和無數的乳膠塗層,大概也會變成這個樣子。有時候我會跟那隻獅子說話,雖然我知道大家對「跟東西說話」這種行為有點意見,但是我很確定在教科書上看過一段話,說我有這樣的行為是「完全正常」的:
「到了第十天左右,足不出戶的人難免會覺得無聊,因此開始跟身邊的東西說話。這是正常的現象,不需要過度擔心。」
我的情況則是第八天。那天我又待在家裡不想去上學,而且下午的時候心情很糟,我覺得壁紙獅在房間角落盯著我,我馬上就知道是牠,然後就時不時的注意了牠一陣子,並且克制自己想要跟牠說話的衝動。最後,我終於到達臨界點、再也忍不住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在想:『噢,可憐的馬修,整天關在家裡,太悲慘了吧?他為什麼不去學校呢?為什麼不到外頭去做些有意義的事呢?』我告訴你,這是不可能的!你就別白費力氣擔心我了!」
說完這些話,我其實覺得平靜多了,有一種好像吵贏牠的感覺。現在牠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我偶爾會說話的對象,就像媽會跟貓講話那樣。這並不奇怪,如果牠會回應我那才奇怪,但是這從來沒有發生過。
當然,沒有人知道我會跟牠說話,這是我的另一個小祕密。其實,怕髒的事情也是個祕密,直到最近才被發現,我的朋友湯姆就是第一個注意到的人。我在上自然課的時候去了廁所,當我回到座位,他用拳頭撐著頭、盯著我看。
「小馬,你怎麼了?」
我看著他。
「什麼意思?」
湯姆靠過來說悄悄話。
「廁所啊,你每堂課都會去,下課也去,你沒事吧?」
我去洗手,那就是我一直跑去廁所的原因。我總是覺得不夠乾淨,所以得一直洗手,想要把病菌洗掉。我開口想要告訴他,但卻不知道該怎麼說,只好聳聳肩繼續做我的事。我差不多就是在那之後沒去上學的。
既然不用去學校,我的狀況也比較好了,還可以愛怎麼打掃就怎麼打掃。浴室是最讓我困擾的地方,因為我每次進去都覺得那裡細菌叢生。幾個星期前我崩潰了一次,那時候媽正在上班,等我心情平復的時候已經傍晚了,媽已經回到家了。她站在門邊,不可置信的張大嘴巴,看著我用沾滿漂白水的脫脂棉球擦拭水龍頭內側。
「馬修,你到底在做什麼?」
她看了看四周白得發亮的磁磚,如果你看見她誇張的表情,大概會以為我在到處亂畫。
「這不對勁……別再弄了,夠了。」
她往前跨了一步,我馬上退開靠在水槽邊緣。
「馬修,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你怎麼了?你的手一塌糊塗……」
她把手伸向我,但我搖搖頭。
「妳不要動,媽,別再靠過來了。」
「我只是想看看你的手,小馬。你的皮膚看起來在流汁……」
我把兩隻手夾在腋下。
「是不是灼傷了,馬修?你的手是不是灼傷了?你不能把漂白水直接倒在皮膚上啊,親愛的。」
「我沒事,不要管我。」
我快速從她旁邊走過、回到房間,並且用腳把房門關上。我躺在床上,剛剛把手夾在腋下的時候我感到一陣又一陣的抽痛。媽站在房門外,她知道這時候最好不要進來。
「親愛的,我能幫上什麼忙嗎?拜託你告訴我好嗎,馬修?我跟你爸沒辦法繼續這樣,今天學校又打來了,我沒辦法一直跟他們說……說你生病了。」
她發出微微的哽咽聲,聽起來就像突然忘了呼吸。我閉上眼睛,對她大喊。
「手套。」
一陣沈默。
「你說什麼?」
「乳膠手套,拋棄式的那種。我需要的就是這個,好嗎?現在可以讓我一個人靜一靜嗎?拜託!」
「好吧,我……我來想辦法。」
事情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床底下的祕密盒。它不是什麼覆滿灰塵又裝著寶藏的舊木箱,而是一盒一百隻拋棄式乳膠手套,現在只剩下十五雙了。我跟媽達成祕密協議:我不再用漂白水消毒皮膚,而她會提供我手套。
我們覺得沒必要告訴爸,他不會理解的。
|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金魚男孩【榮獲英國童書聯盟獎,卡內基兒童文學大獎、水石書店童書獎入圍】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3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金魚男孩【榮獲英國童書聯盟獎,卡內基兒童文學大獎、水石書店童書獎入圍】
一位患有強迫症的男孩、一名失蹤的小寶寶、一個深藏心中的祕密……
暢銷英、法、美、韓、義、西等全球12國
榮獲英國童書聯盟獎
卡內基兒童文學大獎、水石書店童書獎入圍作品
關於失落、勇氣與面對的療癒故事
▌囊括、入圍多項童書大獎
英國童書聯盟(The Federation of Children’s Book Group)童書獎
豪恩斯洛學校圖書館(Hounslow SLS)少年圖書獎
博爾頓兒童圖書獎(Bolton Children’s Fiction Award)
南華克圖書獎(Southwark Book Award)
英國水石書店(Waterstones)當月選書
韓國幸福晨間閱讀(행복한 아침독서)選書
卡內基兒童文學大獎(Carnegie Medal)入圍
英國水石書店(Waterstones)童書獎入圍
布蘭福博斯獎(The Branford Boase Award)入圍
英國讀寫學會(UKLA)圖書獎入圍
好閱讀(Goodreads)最佳少年與兒童圖書入圍
100雙手套、55封郵件、34篇日記、7個家庭、1名失蹤的孩童,
以及生活在玻璃窗內的「金魚男孩」……
12歲的小男孩馬修患有嚴重強迫症。
他不願意走出大門(太多細菌了!)
不准爸爸媽媽碰到他(太髒了!)
也不允許任何人踏進他的房間(他絕對受不了!)
但是,沒有人了解馬修為什麼要不斷的洗手、戴上手套隔絕外界,甚至無法去上學,他就像一隻魚缸裡的金魚,每天待在房間裡、看著窗外的世界、無聊的觀察鄰居的生活瑣事,並且記錄在筆記本中。
直到有一天,鄰居家中1歲多的小寶寶離奇失蹤了,馬修成為最後一位見到小寶寶的人,他的筆記則成了破案的關鍵。為了找回小寶寶,馬修決定親自調查這場謎團,但是問題是,為了破案,馬修必須鼓起勇氣走出戶外、接觸外面的世界,還要面對多年前弟弟死亡而深深影響馬修的那個祕密……
「不要等待暴風雨過去,你得自己走出去,然後在雨中起舞。」
卡內基兒童文學大獎入圍作家麗莎.湯普森以細膩、幽默的筆調,帶領我們跟著馬修一起在逆境中成長茁壯、在孤獨時尋找友誼、在無助時尋覓希望,讓我們在故事中看見:成長,就是在大雨中起舞。
【本書特色】
1. 給孩子的「療癒」之書。
人生不一定每件事都盡如人意,《金魚男孩》的故事帶給孩子的不只是探案的精彩刺激,還有深深的療癒與勇氣,讓孩子知道面臨困境時可以更敞開心胸的尋找協助。若我們無法避免暴風雨,或許可以學著在與中跳舞、學會與困境相處。
2. 給父母的「理解」之書。
當家中面臨失落時,孩子也會用自己的方式來面對、保護我們。《金魚男孩》的故事能讓家長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孩子的問題行為,或許當我們更理解孩子的內心,原以為的「難搞」、「不乖」,「難以理解」的表現,其實是他們正面臨焦慮與憂慮的反應。
3. 給大眾的「同理」之書。
孩子表面的行為問題可能有更深的背後含意,《金魚男孩》讓大眾可以更同理特殊孩子的狀況,有時候「問題兒童」的背後,其實帶著深深的哀傷與憂愁。
◎國際媒體感動推薦◎
「受強迫症與弟弟死亡的罪惡感所苦的馬修,真實得令人心碎,然而,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這本小說從沒讓我們放棄一絲希望。」──柯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
「這則溫馨的故事能帶給強迫症患者極大的安慰,也能幫助其他人了解他們。」──衛報(The Guardian)
「這本小說成功編織了小男孩馬修面對強迫症的兩個故事──他內心的掙扎以及尋找失蹤孩童的過程,從而創造一部充滿神祕冒險色彩又溫馨動人的小說。」──學校圖書館學報(School Library Journal)
「這不只是一部懸疑小說,也是一部探討恐懼與孤獨的作品。故事精彩,人物刻劃也溫暖又深刻。」──每日郵報(Daily Mail)
「感人且幽默的故事,伴隨著關於家庭價值、友誼、面對恐懼的深刻訊息,是一部傑出的處女作。」──觀察家報(The Observer)
「一本層次豐富的推理小說,既懸疑又溫馨。」──書目雜誌(Booklist)
「麗莎‧湯普森是最有創造力的兒童作家之一。」──泰晤士報(The Times)
◎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好評◎
「我好愛這本書以及催人淚下的結局。如果你喜歡《奇蹟男孩》,那你一定會喜歡這本書!」──黛比 D. ★★★★★
「閱讀《金魚男孩》就像老朋友給了你一個溫暖的擁抱,結局讓我感動落淚了!」──丹尼爾 H. ★★★★★
「這本書幽默又感人,還涵蓋了許多重要的議題:友情、霸凌、強迫症……我小時候怎麼沒有這種書呢?」──K. 愛德華★★★★★
「令人喜愛的角色加上懸疑的案件,我無法停止閱讀這本書!」──丹尼★★★★★
推薦人
「這個故事令人感動,與引發諸多省思,『我們應該如何讓一般孩子接納特殊孩子呢?』確實值得我們再三思索。」──邱慕泥(戀風草青少年書房店長)
「在玻璃缸裡的金魚,到底是置身事外或是旁觀者清?罹患強迫症而足不出戶的主角,因為脆弱而更能注意他人的變化,自己成為怪咖才能理解他人的獨特;《金魚男孩》讓我們與主角一同掙扎,從旁觀者到走出家門親身參與,需要克服的不只是表面上的問題行為,還有一層層自我逃避的關卡,跳出魚缸真的會窒息?或是發現自己可以不是金魚呢?」──羅怡君(親職溝通作家與講師)
【兒童文學界、教育界 落淚推薦】
王淑芬|兒童文學作家
吳在媖|兒童文學作家
李貞慧|繪本暨青少年文學閱讀推廣人
林世仁|知名兒童文學作家
林怡辰|彰化原斗國小教師
邱慕泥|戀風草青少年書房店長
胡展誥|心理諮商師、作家
徐永康|台灣兒童閱讀學會常務理事
許建崑|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
陳安儀|親職教育部落客
游珮芸|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理事長
湯華盛|精神科醫師
番紅花|親職作家
黃筱茵|兒童文學工作者
羅怡君│親職溝通作家與講師
作者簡介:
麗莎.湯普森 Lisa Thompson──著
★卡內基文學獎、水石書店童書獎、布蘭福博斯獎提名作家
曾任職於英國BBC電台及CPL製片公司,從小最大的願望就是成為作家。首部作品《金魚男孩》熱銷英、美、法、西、義、韓等12國,更入選「英國水石書店當月選書」。
麥克.羅利Mike Lowery──繪
美國作家和插畫家,作品類型廣泛,包含卡片、童書及畫廊作品。現與妻子及女兒住在亞特蘭大。
譯者簡介:
陳柔含
大學及研究所皆畢業於臺大生化科技學系,喜歡透過翻譯與研究探索世事,並將收穫傳遞給更多的人。譯有《專注力:吸引力法則的成功關鍵》(好人)、《人體的運作美學》(小樹文化)。
聯絡信箱:jouhanchen@gmail.com
章節試閱
【摘文1】Chapter1 住在栗樹巷的人
查爾斯先生的頭頂有晒傷的痕跡,這是我在他巡視玫瑰叢的時候發現的。他會仔細檢查每一朵玫瑰、搖晃一下比較大的花朵看看花瓣是否掉落,然後繼續慢慢前進。他頭上那一大塊光禿禿的地方現在變成了一塊發亮的粉紅色圓頂,周圍有蓬鬆的白髮圍繞。天氣這麼熱,他應該戴帽子的,但是我想當你很專心的時候,應該很難注意頭頂上的高溫。
不過我就注意到了。
從這個窗戶,我注意到很多事情。
我可不是在做壞事,我只是喜歡觀察鄰居來打發時間,我想鄰居應該不會介意。有時候,住在五號的傑克.畢夏會對我吆...
查爾斯先生的頭頂有晒傷的痕跡,這是我在他巡視玫瑰叢的時候發現的。他會仔細檢查每一朵玫瑰、搖晃一下比較大的花朵看看花瓣是否掉落,然後繼續慢慢前進。他頭上那一大塊光禿禿的地方現在變成了一塊發亮的粉紅色圓頂,周圍有蓬鬆的白髮圍繞。天氣這麼熱,他應該戴帽子的,但是我想當你很專心的時候,應該很難注意頭頂上的高溫。
不過我就注意到了。
從這個窗戶,我注意到很多事情。
我可不是在做壞事,我只是喜歡觀察鄰居來打發時間,我想鄰居應該不會介意。有時候,住在五號的傑克.畢夏會對我吆...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1. 住在栗樹巷的人
2. 床底下的祕密盒
3. 查爾斯先生家的池塘
4. 該拿馬修怎麼辦?
5. 柯爾醫生
6. 金魚男孩
7. 梅樂蒂與傑克
8. 玩花瓣的泰迪
9. 泰迪失蹤了
10. 傑克的故事
11. 搜救小組
12. 第一次上電視
13. 借宿一晚
14. 羅德醫生
15. 梅樂蒂的祕密
16. 墓園裡的美人魚
17. 神祕的牧師宅
18. 血痕
19. 潘妮‧蘇利文
20. 出現目擊者
21. 老妮娜的燈
22. 拜訪十一號鄰居
23. 跟蹤老妮娜
24. 哈靈頓居家妙方
25. 詹金斯先生的奇怪舉動
26. 惡魔的貓
27. 壁紙獅的危機
28. 警察拜訪老妮娜
29. 仿聲鳥胸前的顏...
2. 床底下的祕密盒
3. 查爾斯先生家的池塘
4. 該拿馬修怎麼辦?
5. 柯爾醫生
6. 金魚男孩
7. 梅樂蒂與傑克
8. 玩花瓣的泰迪
9. 泰迪失蹤了
10. 傑克的故事
11. 搜救小組
12. 第一次上電視
13. 借宿一晚
14. 羅德醫生
15. 梅樂蒂的祕密
16. 墓園裡的美人魚
17. 神祕的牧師宅
18. 血痕
19. 潘妮‧蘇利文
20. 出現目擊者
21. 老妮娜的燈
22. 拜訪十一號鄰居
23. 跟蹤老妮娜
24. 哈靈頓居家妙方
25. 詹金斯先生的奇怪舉動
26. 惡魔的貓
27. 壁紙獅的危機
28. 警察拜訪老妮娜
29. 仿聲鳥胸前的顏...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2021/04/21
2021/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