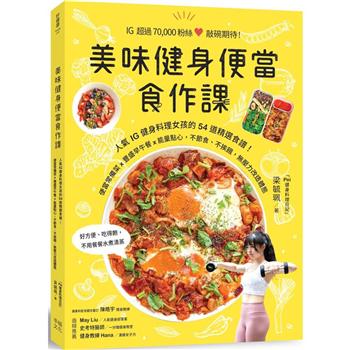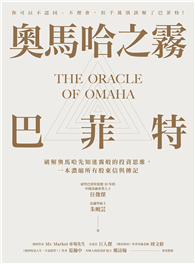推薦序1
也是一段人鹿戀?
巴代
我從來沒有隨意翻閱一份書稿,在幾頁之內便產生強烈的同感與一口氣讀完的念想,並產生出想為它寫點文字的感動。《鹿人。手札》便是這樣一本書。那樣的同感與共鳴來自於我族口傳故事中,關於人與鹿之間流傳百千年的情韻流動,也來自於我個人參與部落大獵祭最初的森林經驗。這樣的情韻與經驗,我不曾在台灣關於自然書寫出版品中閱讀與經歷過,而遠在法國的森林,在喬佛.德洛姆的筆下,居然鮮活的呈演在行文中。在猶豫該不該摘錄原文作為吸引讀者往下翻閱時的現在,請容我先說說關於卑南族的〈人鹿戀〉傳說與個人森林經驗作為呼應。
在卑南族kasavakan(台東建和部落),流傳著一個關於人鹿戀的故事:
位於半山腰的部落附近,一對夫婦生養著一個美麗的女孩,夫妻甚為疼愛這女孩,但日常農忙無暇多照顧,也就任女孩隨意活動。還好部落附近沒什麼危險的地形與動物,女孩總在父母下田工作時在附近四處冶遊,偶而追逐蝴蝶時出現在父母的小米田,又一閃而逝。一天,那母親看見女孩手上拿著一條琉璃珠串,女孩說那是一位朋友送給她的禮物,牠是一隻高大雄壯的鹿,那母親並不以為意,只當女孩頑皮,胡亂編織故事。
一日吃晚餐時間,那父親憂愁的說,小米田出現了不少蹄印,像是有動物出沒,他想去獵殺那頭動物。小女孩一聽,急忙說她有一位雄鹿朋友偶爾會出現在小米田附近,但已經約定好了不會進入小米田,如果父親看見牠,千萬別獵殺牠。那父親知道那頭鹿是女兒的玩伴,便答應了。第二天一大早,那父親帶著弓到小米田準備埋伏,卻見到一隻有著三叉角的雄鹿在小米田旁遊走嚼草,他不加思索的立刻搭箭拉弓,連射了兩箭命中鹿的要害。那雄鹿驚詫的抬頭看著那父親,頸部噴濺的血液,讓牠蹣跚移動幾步便倒了下來,那父親見狀興奮的跑回部落喳呼,讓人一起幫忙抬到家裡。
女孩早預感到一股不祥,早早醒來等在院子裡,看見那頭鹿,她霎時昏了過去。醒來時,她啜泣責備父親沒有遵守約定。女孩絕望的說,既然都殺了雄鹿,她也不好再怪罪父親,她請求父親答應一件事,將雄鹿擺在屋簷前,把鹿頭擺正、叉角朝上,她想從屋子上方好好看牠一眼。說完,便趁眾人調整鹿的姿態時從屋後爬上了屋頂,她傷心欲絕的看著那頭仍然睜著眼的雄鹿,忽然一躍而下讓鹿角穿胸而死。她的父母傷心極了,復又看到女兒房間裡到處掛著的琉璃珠串,才知道女兒與雄鹿交往已久且用情至深。
〈人鹿戀〉的故事淒美,人鹿之間的溝通,族人深信那是可以進行的,只是如何進行?但是多年來,我未能從部落長老口中得到答案。本書作者喬佛.德洛姆以他在森林七年的生活體驗,先後與雄鹿達達、小威接觸、交往、溝通、成為朋友與鹿群家人的經驗,給了我一個具象與細緻的答案。他以生動、平實又謙遜與飽滿情感的文字,敘述著鹿的氣味與行誼,解析著鹿群語言結構的特質,描繪著鹿群迷人又難以理解的生活習性與藥理知識。這使得我個人經驗中,森林擁擠的喬木與灌木叢交疊的影像,在鹿群的活動下忽然變得開闊與透視似的,在人眼與鹿眼交相的視野下,一切顯得舒緩與可預測。彷彿我也聽懂了鹿的言語,牠們指責我童年時期某日,不帶同情的,只顧著好奇張目瞪著大鍋裡,一個有著三叉角的台灣水鹿頭顱,正隨著水溫逐漸增高而沿著鍋邊流動。當然,喬佛的鹿並沒有真正的指責我,但喬佛的森林描述,卻把我帶進部落大獵祭時期的森林經驗,那種夜裡瀕臨失溫,又不得不提高警覺防著野生動物夜裡覓食、移動時可能帶來危險的記憶,隨便一隻飛鼠滑翔而過搧起的風,也教人感到悚然。
最後,我決定不摘錄原文來誘惑讀者,因為本書多數的頁面中,隨處可見醒目又讓人忍不住筆記的段落,我相信讀者隨意翻閱,便會墜入其中。我得說,這是一本優秀的自然書寫作品,既真實、細緻又警醒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甚至人與人之間所應該存有的信任、尊重與善意。
推薦序2
奔向森林,找回對自由的渴望
林雋
接受社會、融入社會,成為社會的一員,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勢必會流失部分的「自己」。換句話說,社會化是被包裝為成長的妥協,捨棄自己成全他人,有時只是希望自己不被當成異類,時常被說以自我為中心的我,何嘗不是如此。在成長的過程中,喬佛完全保留了真實的自己。
《鹿人。手扎》除了是作者友情的告白,也是森林的陳情書,在喬佛筆下的麆鹿,比人類更近似人類,並不是人類無情,而是動物更有情。
喬佛的書寫是溫柔的,但他的下筆卻極為深刻,對於森林生態細膩的勾勒如鹿穿越森林,節奏輕巧如梟振翅,但那些蹄痕卻無法掩飾,那是他寫作的勁道,他隱居在森林中,卻在文字與影像之中展露著強烈的存在感。萬物皆擁有著同等地位,即使是最不起眼的小蟲子也散發著耀眼的光芒,若他是導演,任何風吹草動在他的文筆轉化之下,皆能成為一齣視聽享受的電影。
喬佛的攝影是柔中帶剛的,書中留下的攝影作品雖量少卻質精,在他的觀景窗中,鹿不再躲藏,任何一個野生動物攝影師都知道,要以中長焦鏡頭拍下動物的肖像,即使是現代相機狙擊槍一般精準的對焦能力,也十分困難。而令這些照片難能可貴之處,是鹿在喬佛面前能夠自由自在的生活。我相信喬佛的鹿友們是真的對他卸下防備。
喬佛也稱他在森林的生活有如冒險一般,不僅享受著生的樂趣,也必須時刻和死亡拔河,雖然家人無法接受,但他熱愛這樣的人生,甚至可以為了和鹿共同生活,並且完全成為鹿的同類,他漸漸不再回家補給物資,只為了不讓身體沾染人類的氣息。
用七年的歲月細心聆聽,在我看來,喬佛的純潔引領他走向自然,在森林中他找到可以相濡以沫的同伴,他看到了一群具有靈性的物種。動物不需要言語便可以展露有情的一面,而人類卻自以為是的認為能透過科學去計算森林可以容納的物種數量,卻不知道森林本就有一套調節機制,使得動植物間達到相互依賴的平衡。
同樣是喜愛戶外的人,我很能理解喬佛所寫的「我的內心深處有追求自由的本能,讓我一有機會就想逃離」,熱愛自由,只要感受到束縛,便會極力反抗。我有同感也有同情,正是因為生活在一個備受壓迫的環境,才能寫出自由的可貴,正因為無法壓抑心中的渴望,才義無反顧奔向森林。他用行動告訴人們,即使不當物質的奴隸,也可以自在活著。
喬佛用「被馴服」來比喻他和鹿之間的關係,文中的強調再三,不免讓我思考,原來我們人類不自覺的會認為自己的智慧駕馭在萬物之上。像我們常會說「我的狗」、「我的貓」,如果語言反應思想,那麼其他的動物對人類而言是否只是附庸的角色?而這樣的高傲彷彿根深柢固在人性之中,喬佛談人類對待自然的方式,一切其來有自。
喬佛長時間待在森林也使他看待事物的視野比凡人更為寬廣,他寫森林的溫柔,也寫森林的殘酷,大自然的演化遵守著汰弱留強的鐵律,對動物、植物或是人都一樣,如果不謹慎應對,用輕浮的態度進入森林之中,很快就會被森林反噬。從喬佛的故事裡,我知道他可以為了這唯一的目標全心全意付出。他專注、有決心,且不怕艱難,進入森林前,他花費時間學會辨識植物,學習在森林的生活方式。如果有人可以寫出一本關於鹿的森林史,也唯有喬佛能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