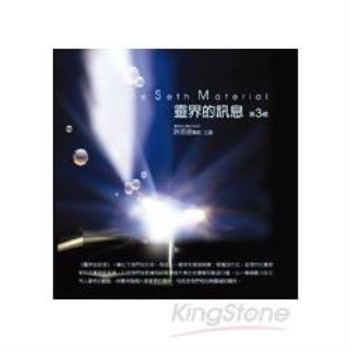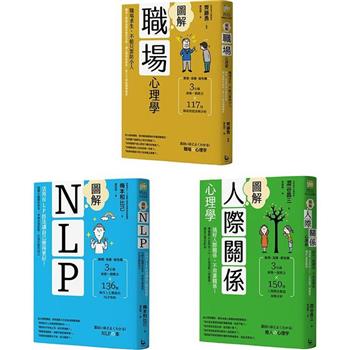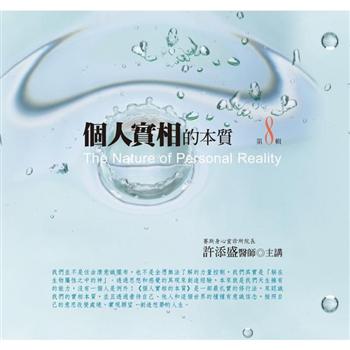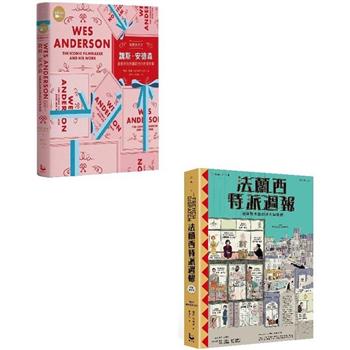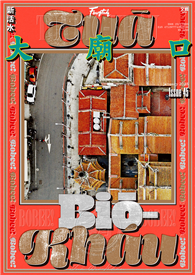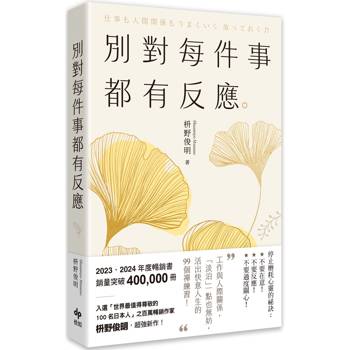【書摘試閱】
劍橋所見‧所思
記不得是二十幾年前在那裏讀了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和「康橋再會罷」,但我知道我對劍(康)橋的嚮慕是這位詩人的彩筆麗藻所挑起的。徐志摩是熱情如火的詩人,他依戀過無數山川故城,但他只對劍橋說:「汝永為我精神依戀之鄉。」稍為熟悉志摩的詩文的人,都不能不承認他的洞察力與自悟力的深透靈空,但他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慾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的意識是康橋給我脫胎的。」劍橋有如許的魔力,怎叫人不想一探她的幽秘?
八月一日早晨,在溫暖的陽光下,我與妻,帶了四個孩子,踏入了這個陌生而又似曾相識的大學城。
「歡迎你們來劍橋!」劍大的人類學者華德英女士(Barbara E.Ward)和她的夫婿倫敦經濟學院的摩里斯教授(Stephen Morris)好意地在車站接迎。
「劍大在那裏?」我問駕著車的摩里斯教授,我急著想會見這個久已嚮慕的學府。
「劍大在那裏?很難說,劍大與劍城是分不開的。」是的,我後來才清楚,最合理的說,劍大不是一個地方,雖然他也有本身的教務大廈、圖書館等,還包括一 學人的組合:大學校長、學院院長以及學者,還包括一年級以上的學生。真正的劍大分散在劍城各個具體的學院裏,學院有自己性格的建築,有自己驕人的傳統,但的的確確,學院又是大學的有機的一部份。所有的課程都是大學主持的,學位的考試與授予也是大學的事。學院只是宿舍,是吃飯、睡覺、談天、討論的地方。有社交的成份,也有知識的成份。這是一個與中國、美國,乃至歐陸大學都不同的制度,它是很獨特的英國歷史的產物。誰設計的?沒有人,劍大是慢慢成長起來的,不是一下子創造出來的。
「金先生,你看左邊,那是Peterhouse,他是劍大最古老的學院,成立於一二八四年」。剎那間,我被那古銅色的、蒼老的建築吸引住了,陳舊,是的,七百年了,但我只感到他的古雅。其實,當踏入劍橋時,一股濃厚的古典氣息就撲面而來。劍橋的建築很少有鮮明的顏色的,雖然滿眼是紅磚的房屋,但那種紅是深沉的,帶點褐色的,是那種經過幾世紀的風雨洗禮的紅,已經不紅了,這種不紅的紅更好、更好味道,至少在我的眼裏。「那街頭遠處的尖塔樓閣,看見嗎?那最高的是王家學院的禮拜堂,是十五世紀亨利六世建造的,它對面的是Great St, Mary Church,是大學的教堂,是十三世紀初葉蓋的。」王家學院的禮拜堂(King's Chaple)有一種王者氣象,有點旁若無人的睥睨感。在遼闊的劍橋的平原上,在多半是二層高的建築的屈冰頓(Trampington)街道上,那尖塔就好像插入雲霄的石筍。突然,我意會到浮凸在天空中的都是尖塔樓閣。
「摩里斯教授,到處似乎都是教堂、禮拜堂,所有的高建築都是!」
「是的,劍橋有許多教堂、禮拜堂,究竟有多少,我也不清楚。」中古,我憶起歷史書中所述的中古的寺院世界。不錯,這就是劍橋之所以為一中古的大學城吧!在過去一個月中,我與妻參觀了好些教堂與學院的禮拜堂,我漸漸知道教會在劍橋的歷史所扮演的角色。劍橋如果沒有劍大只不過是一個風景秀麗的小城,劍大如果沒有教堂、禮拜堂也必然會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風姿。不!我根本懷疑會否有這個世界著名的大學。是無數的尖塔樓閣把時間凍結在這個小城裏,賦予了他歷史的悠久感與莊嚴的面貌。中古的森冷窒息的空氣已被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的浪潮沖洗一空,但寺院畢竟給予了劍橋學術的根苗。劍大許多學院是國王、王后、貴族夫人哺育長大的,如王家學院、三一學院、克萊亞學院、皇后學院、潘普羅克學院,但許多學院則不是由寺院培養成長便是與教會有關的,如Peterhouse, Michaelhouse, Trinity hall, Jesues, Selwyn。劍橋的學術生命是與寺院、教堂長期結合的;在劍大誕生之前,最早的傳道、授業之處即是白納德教堂,在一七三○年大學的教務大廈未建立前,所有的學位考試與畢業禮就是今日的瑪利亞教堂舉行的。大學不只本身有教堂,劍大的所有學院也都有自己的禮拜堂。一個學院如果沒有一個禮拜堂就會覺得缺少什麼似的,早期的學院建設如果沒有教堂,就像畫龍不點睛了。不論教堂是否是人天相接的階梯,但沒有了教堂,在劍橋會變成一個無聲音的古城(真的,劍橋的靜是出奇的!),至少就聽不到向晚的鐘聲了。鐘聲激發了劍橋的詩情,也是鐘聲把中古帶來了二十世紀。在劍橋,上帝未死,祂與科學都被鐘聲羽化成詩了。轉過了劍橋中心,更靜了,車外,多的是參天的古樹,多的是一塊塊綠得想在上面滾一滾的草地,街道上最少的就是人,所看到的是二位騎在自行車上的一老一小,是祖母與她的孫女兒吧!?那小女孩的笑聲像銀鈴似的散落在滿地的綠裏。其實,將就點,不需要到劍城郊外的格蘭賽斯德草原去踏青,綠就舖在每個人家的門口。噢!原來是這份綠使我感到那麼心曠神怡。來劍橋後,每個黃昏,我們都捨不得讓它輕輕溜走,或者,騎車向炊 處飄去,沒有目的,沒有牽罣,像少年時在去碧潭的路上任「鐵馬」 躍。忘了時間,忘了「規矩」,跟孩子一起在格蘭賽斯德草原上翻滾,滾得滿身是點點金光,一直到素月冉冉上升,送別夕陽在遼闊的地平線上。我們是回到自然,回到大地的懷抱中來了!香港五年摩天高樓上的生活使我漸漸忘了自然的樂趣,在劍橋的尋覓中,尋覓到了自然,也尋覓到了自己。更多的夏晚,我們會披一件薄毛衣,隨著清脆的鐘聲向劍河慢慢地踱去。去探望劍河是不可太匆忙的,在匆忙中你不會捕捉到她那份文靜,那份女性的柔情。去看劍河,除了夕陽鐘聲裏,最好是晨星的冷霧中。在清晨你可以瞥見她睡夢中醒來的嬌態,若有若無的少女的神秘笑靨;到黃昏時分她又是婀娜端莊的貴婦了!最醉人的是在微風中她伴著垂柳婆娑起舞的美姿,永遠是那樣的徐緩,那樣的有韻律,那樣的親切的招呼!劍河輕盈地穿過皇后學院、嘉薩琳學院、王家學院、克萊亞學院、三一學院、聖約翰學院、麥德蘭學院,她穿過世界上這些最古老學院的后園,為這些男性化的建築帶來了妖嬈與明媚。劍河兩岸的學院的草地像一塊塊藍玉,像一幅幅錦繡,也像一片片浮雲,而跨過劍河的則是一座座如雨後的彩虹的橋了。志摩說:「康橋的靈性全在一條河上,康河,我敢說是全世界最秀麗的一條水。」我想我們的詩人沒有誇張,不過,我畢竟要想,假如沒有這些古典的學院,沒有那些幾個世紀以來從學院的拱門中走出來的大學者、大科學家、大詩人,劍河會不會那樣秀麗?會不會那樣有靈性?會不會那樣秀名遠播,引人慕艾?是人使水秀靈呢?抑或是水使人秀靈呢?我不知道。但劍橋真是出過不少靈秀的人物,真正靈秀的人物。不去算那一長列叱吒風雲的政治家了,也不去算我們孤陋不知的學者了,只消舉幾個我們熟悉的學術史上的名字好了,牛頓、達爾文、哈維、馬爾薩斯、凱因斯、培根、羅素,這些名字在物理學,生物學、醫學、人口學、經濟學、哲學上,不是巨手開鑿新紀元,便是在知識的旅途中豎起了里程碑,至於史賓塞、拜侖、米爾頓、伍爾華茨、丁尼生,則都是詩國的桂冠和驕子。這些人在劍橋留下了足印,留下了音貌,留下了謎樣的故事。劍橋是靜寂的,靜寂得幾乎有些寒意,但她永不會叫人無聊。靜寂使人孤獨,但孤獨正可以使人與劍橋歷史中的巨靈對話。劍橋最高的精神活動是在那些孤獨的歷史的對話中進行。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劍橋語絲的圖書 |
 |
劍橋語絲 作者:金耀基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77-07-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83 |
中文書 |
$ 84 |
世界國別史 |
$ 90 |
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劍橋語絲
★本書作者深度探訪劍橋大學,帶領讀者體驗劍橋歷史與文化的厚度。
劍橋什麼事都講傳統,但劍橋的傳統永遠容忍,甚至鼓勵新的嘗試。
英國劍橋大學是十三世紀以來,最能保有古典神貌與傳統的大學,在其巍巍建築、無數尖塔的樓閣裡,蘊藏著歷史與文化的厚度。
牛頓、達爾文、培根、凱因斯、懷海德、羅素、維根斯坦、拜侖、史賓塞、米爾頓這些名字在物理學、生物學、醫學、經濟學、哲學上,不是巨手開鑿新紀元,便是在知識中豎起了里程碑,甚至是詩國的桂冠和驕子。他們都出自劍橋,在這裡流下了音貌,留下了謎樣的故事與傳奇。在劍橋大學將近一年的訪問學人,作者由劍河兩岸的中古學院談起,為劍橋大學裡學院的傳奇故事、學術制度及其迷人的幽祕清靈之景作一番巡禮,為劍橋大學烙下了深刻亙常的人文印記。
作者簡介:
金耀基
1935年生,浙江天台人。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碩士,美國匹茲堡大學哲學博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社會學系講授教授。著有《大學之理念》、《從傳統到現在》、《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民本思想》、《中國的現代轉向》及散文集《海德堡語絲》。另有多篇論文在國際學術專刊及中英文專書中發表。
章節試閱
【書摘試閱】
劍橋所見‧所思
記不得是二十幾年前在那裏讀了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和「康橋再會罷」,但我知道我對劍(康)橋的嚮慕是這位詩人的彩筆麗藻所挑起的。徐志摩是熱情如火的詩人,他依戀過無數山川故城,但他只對劍橋說:「汝永為我精神依戀之鄉。」稍為熟悉志摩的詩文的人,都不能不承認他的洞察力與自悟力的深透靈空,但他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慾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的意識是康橋給我脫胎的。」劍橋有如許的魔力,怎叫人不想一探她的幽秘?
八月一日早晨,在溫暖的陽光下,我與妻,帶了四個孩...
劍橋所見‧所思
記不得是二十幾年前在那裏讀了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和「康橋再會罷」,但我知道我對劍(康)橋的嚮慕是這位詩人的彩筆麗藻所挑起的。徐志摩是熱情如火的詩人,他依戀過無數山川故城,但他只對劍橋說:「汝永為我精神依戀之鄉。」稍為熟悉志摩的詩文的人,都不能不承認他的洞察力與自悟力的深透靈空,但他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慾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的意識是康橋給我脫胎的。」劍橋有如許的魔力,怎叫人不想一探她的幽秘?
八月一日早晨,在溫暖的陽光下,我與妻,帶了四個孩...
»看全部
目錄
目 次
劍橋語絲再版序
自序
劍橋所見‧所思
霧裡的劍橋
劍橋之為劍橋
漫談劍橋大學的學院制
是中古的呢?還是現代的?
談劍橋的學院之性格
從劍橋到牛津
DON:在歷史中漫步的人
劍橋一書賈
書城飄香
遠懷雲五師
是那片古趣的聯想
劍橋的三一
記一間偉大的學院
一間中古大學的成長
談劍橋的「變」與「守」
劍橋‧海德堡
從劍橋到劍橋
漫談哈佛與M.I.T.
牛津劍橋的競戲
附錄
人間壯遊
追念王雲五先生
劍橋語絲再版序
自序
劍橋所見‧所思
霧裡的劍橋
劍橋之為劍橋
漫談劍橋大學的學院制
是中古的呢?還是現代的?
談劍橋的學院之性格
從劍橋到牛津
DON:在歷史中漫步的人
劍橋一書賈
書城飄香
遠懷雲五師
是那片古趣的聯想
劍橋的三一
記一間偉大的學院
一間中古大學的成長
談劍橋的「變」與「守」
劍橋‧海德堡
從劍橋到劍橋
漫談哈佛與M.I.T.
牛津劍橋的競戲
附錄
人間壯遊
追念王雲五先生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金耀基
- 出版社: 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77-07-01 ISBN/ISSN:957050082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90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西方國別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