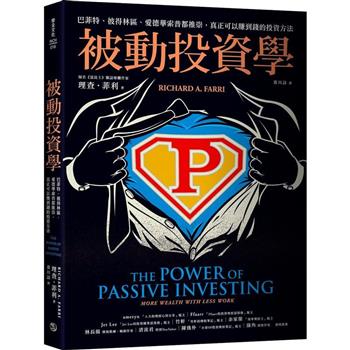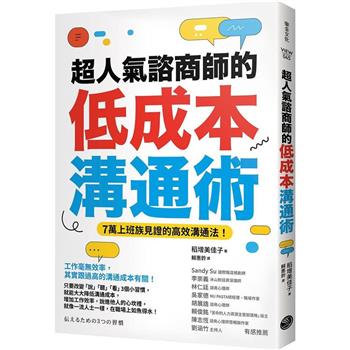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小獵犬號環球航行記的圖書 |
 |
小獵犬號環球航行記 作者:達爾文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8-08-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35 |
二手中文書 |
$ 379 |
科學家傳記 |
$ 379 |
科學家傳記 |
$ 408 |
社會人文 |
$ 432 |
自然科學 |
$ 446 |
中文書 |
$ 446 |
自然科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1831年底,達爾文隨英國皇家軍艦小獵犬號出發,展開為時五年的科學考察之旅。他並不知道,日後他影響深遠的學說將奠基於此。
五年間,他四度橫渡大西洋,走遍南美大陸及其周邊,深入南太平洋,遠赴印度洋。在廣範圍的經緯度的移動中,他親歷了豐富多變的自然與人文狀態:火山、地震、熱帶雨林、化石、海嘯,陌生的民族,迥異的制度;此外,船上的生活,在考察據點的採集與狩獵,他那近乎哲學的生物學思考,物種發生與遞變的軌跡,都一一筆錄在日記之中,大量的文字資料和精緻的繪圖,既是知識的,又是文學的,精確而敏感,不斷逗引我們參與一次虛擬的旅程。
由於達爾文所開啟的視野,讓人與神的界限再度泯滅,他和小獵犬號帶領我們前往的,是新世界同時也是舊世界─人類的失樂園。我們像亞當、夏娃一樣,眼前的每一個景象,都是那樣新奇;每一樣事物都等待命名……
作者簡介:
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
英國博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人。他從小即熱衷於蒐集植物、昆蟲標本,19歲按照父親意願進了劍橋大學,準備當一位牧師,在學中他與一干科學家密切交往。畢業後參加英國海軍艦艇小獵犬號的環球航行(1831-1836),這決定了他一生的事業。回國後他將一路上的觀察結果繼續進行深入思考,並於1838年創立了「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的理論。
42年他將理論整理籌35頁的摘要,44年擴充為230頁,其學說大體完成,但並沒有立即發表,希望繼續蒐集材料驗證理論。58年他第一次向學術界發表他的學說,而為世人熟知且影響深遠的《物種起源》一書在次年出版,並引起熱烈爭議。完整的書名是《依據自然選擇或在生存競爭中適者存活的物種起源》。
他的主要著作還有《小獵犬號環球航行記》、《達爾文自傳與書信集》、《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人類和動物的感情表達》、《蘭科植物的傳粉》、《攀緣植物的運動與習性》、《食蟲植物》、《植物界異花傳粉與自花傳粉的效果》、《腐殖土與蚯蚓》等。
譯者簡介:
葉篤莊
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實科畢業。曾任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編譯委員會主任,《農業科學通訊》等雜紙主編,現任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副會長兼科技翻譯委員會主任。著有《華北農作物栽培制度》、《華北棉花及其增產問題》等,譯有《達爾文進化論全集》13卷、《米丘林全集》4卷及及《赫胥黎自傳》等。
原中文譯者前言iii
達爾文與《小獵犬號環球航行記》v
原序xi
著者附言xii
第一章 佛德角群島的主島聖地亞哥001
第二章 里約熱內盧027
第三章 馬爾多納多055
第四章 從內格羅河到布蘭卡港085
第五章 布蘭卡港107
第六章 從布蘭卡港到布宜諾斯艾利斯141
第七章 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到聖菲163
第八章 東方班達和巴塔哥尼亞189
第九章 聖克魯斯河、巴塔哥尼亞和福克蘭群島231
第十章 火地島263
第十一章 麥哲倫海峽;南部海峽的氣候297
第十二章 中智利325
第十三章 奇洛埃島和喬諾斯群島349
第十四章 奇洛埃島和康塞普西翁...
- 作者: 達爾文
- 出版社: 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8-08-01 ISBN/ISSN:957051483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648頁
- 類別: 中文書> 科學> 自然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