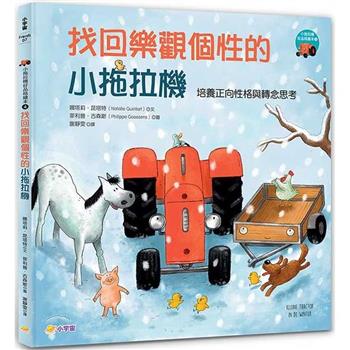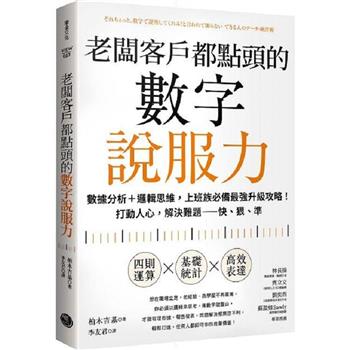名人推薦:
芙蘭西絲‧梅耶思因為旅行,幸福感存在
文/謝勳(講義雜誌「國家地理新鮮聞」專欄主編)
十一年前女詩人及作家芙蘭西絲‧梅耶思(Frances Mayes),開啟了讀者心中歸屬義大利的感性和詩意,隨著她幾度神遊托斯卡尼地區的山光嵐影和那裡人生活的愜意。現在,她再度以特有的溫馨而富饒詩意的文筆,喚醒讀者的觸角去感受世界其他角落多姿多采的文化。
當她在托斯卡尼買下一間古老房子後,開始寫些關於房子的事,出版了那經典之作《托斯卡尼豔陽下》(台灣商務)。那本書連續有兩年半出現在紐約時報暢銷書名單上,而且改編成一部電影。她說過,她的幸福生活觀體現在置身於義大利鄉間以及當地人的熱情之中。之後梅耶思又寫了三本關於托斯卡尼的書:《美麗托斯卡尼》《把托斯卡尼帶回家》(均為台灣商務)和《在托斯卡尼》。近十年來吸引了數不盡的遊客來此地度假。難怪有人稱她為托斯卡尼的代言人。
她捨棄趕景點式的觀光,而從餐桌上、市場裡和居民談話間欣賞當地的文化。到了一個地方,她喜歡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跟當地人接觸,還有和他們坐下來吃一頓道地的家常便飯,並且好好地談天。她融合了個人的感覺與淵博的見識,涵蓋各地藝術、文化、歷史、景觀和餚饌,啟發讀者的知識、思考和想像。
這位曾在舊金山州立大學主持文學創作的教學的作家,也是位詩人,她認為,從詩裡學到語言的節奏,句法的心理,用字的精確,還有更重要的:如何創造讀者立刻可以感受的意象。梅耶思善於用準確的意象表達對一個地方的感覺,傳達那些超越明顯和尋常的感受,讓讀者有臨場感。她曾擔任2002年美國最佳旅遊作品集的編輯,也出版了六本詩集、教科書《詩的發現》和一本小說,並且在有名的雜誌上發表了很多的詩作及自傳性隨筆。她的著作已經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的譯本。
梅耶思認為,最好的旅遊作品意味著一種追求,一種經歷的改變或某方面成長的願望,或者仔細又用心的觀察。她對於不同的文化一向很感興趣。她的新書《地球玩一年:歌頌旅行的魅力與樂趣》(台灣商務)是她一向感興趣的主題的延伸;那主題便是:在某個地方生活是怎麼個樣子。她到處旅行,去了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希臘、摩洛哥、土耳其,還有英倫三島與法國。為的是探討那主題,並親身體驗了美麗的景物和當地人的熱情所帶來的幸福感。她在市井小民間賃屋而居,在鄰近的市場購物,在偏僻的街巷漫遊。
在那些繞著地球的旅程中,梅耶思對「家」的觀念感到興趣:如何在這個都市或那個村莊感覺自在,像在家裡一樣?誰能隨處感覺自在,為什麼?我在那裡能定下心來住嗎?她喜歡到觀光客去的景點,但到了每個地方她更喜歡過當地人的生活。
她曾說過,寫這本新書寫得很歡喜。因為有機會到一些絕佳的地方,更徹底地品味到這世界的形形色色,還有每個地方本身就具有的氣勢。她認為,這世界可不小呢,不是一個「地球村」。即使像法國這樣一個她已經熟悉的國家,仍然保有只有法國才有的特色,她希望這種地方性的特色會繼續存在。
她說,旅行使人更有智慧,因為當旅行時你必須拋棄成見。每個人都會有一些成見,可是當睜開眼觀察所到之處時,必然看到該地的現實,常和你從遠處帶來的想像大有出入。我們都需要覺察到文化間的差別,並讚美那些差別。
*文中芙蘭西絲‧梅耶思的照片,由台灣商務提供。
摘自金石堂出版情報2007/11/19人物特寫單元
媒體推薦:
「凡是想探索自己還有哪些面向是以往所不知道的人,會去冒險犯難、歷險探奇……順帶也發掘別的文化裡不同的節奏、滋味、氣味和生而為人的方式──這樣的讀者可以在梅耶思的文字裡找到一種親和、熱切與堅忍不拔的指引。」
──《休士頓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
「梅耶思擅長透過豐富詩意的敘述,捕捉濃醇厚實的地域感。」
──《奧蘭多前哨報》(Orlando Sentinel)
「不難理解何以梅耶思成為追求美好生活的代表人物,她不僅鼓舞我們把握當下、啜飲美酒、聞嗅玫瑰的芳香,她還讓我們覺得改變生活是極有可能的,正如她就辦到了那樣。」
──《萊辛頓領導前鋒報》(Lexington Herald-Leader)
「梅耶思所展現的天賦是透過書寫表現日常生活……同時呈現一種比較單純而不紛亂的生活方式。」
──《今日美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