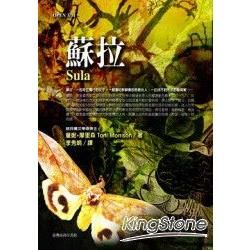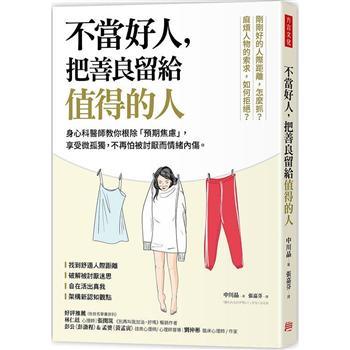譯者序
在虛構的記憶中寫歷史:《蘇拉》的時間與空間結構 李秀娟
一
童妮.摩里森的第二本小說《蘇拉》(Sula)在一九七三年出版,當年四十二歲的摩里森,還沒有登上人生的峰頂。在《蘇拉》面世三年以前,摩里森剛以《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 1970)在文壇上嶄露頭角。《蘇拉》雖然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的提名,四年之後摩里森會以《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 1977)贏得全國書評家協會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八年之後,隨著《黑寶貝》(Tar Baby; 1981)的出版,她會登上《新聞周刊》(Newsweek)封面;十五年之後,在一九八八年,《寵兒》(Beloved; 1987)會先為她贏得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的肯定;而在《蘇拉》出版之後整整二十年,摩里森更將以《寵兒》榮膺一九九三年諾貝爾桂冠,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非裔女性作家。在《寵兒》締造的創作高峰之後,摩里森仍然筆力不輟,先在一九九二年揉和文學創作與爵士樂結構,撰寫文字風格一新的《爵士樂》(Jazz),一九九七年再推出人物、結構、敘述聲音多元複雜的史詩式巨作《樂園》(Paradise),完成了《寵兒》、《爵士樂》、《樂園》三部曲。接著,在二○○三年,也是《蘇拉》出版之後三十年,摩里森推出《LOVE》(Love),再以聳動的情節與糾結的人物關係,詮釋多年來她一直關注的主題──「愛」,將愛與恨、愛與權力、愛與暴力的關係處裡得淋漓盡致。
綜觀摩里森綿延已近四十年的創作生涯,每一部作品幾乎都可以被視為里程碑。而隨著一部又一部擲地有聲的作品面世,讀者也一次又一次獲得在不同時間點上重新審視摩里森每一部作品的機會。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幫摩里森製作年表,依時間先後順序勾勒出她如何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單親母親,躍身成為世界文壇舉足輕重的人物,摸索她從處女作初試啼聲到榮膺文學桂冠的垂直生命軌跡,摩里森的作品似乎更可以被放入一個透過不同時間點的連繫而穿越時間縱軸的網絡中,彼此連結、互為對話。首先,談摩里森創作宇宙中的時間連結,不能忽視在她的作品中,真實歷史背景所構築的時間網絡。摩里森鍾情虛構,卻不忘透過想像進行獨樹一格的歷史考掘;她的作品多植基於非裔子民自十七世紀以來由非洲大陸離散、遭奴役、消音、與掙扎再起的歷史某一段落。《最藍的眼睛》是八部小說創作中自傳色彩最濃厚的。小說以摩里森在俄亥俄州的家鄉樂仁鎮(Lorain)為背景,寫的是摩里森自己成長的年代,即二十世紀中期美國中西部小鎮黑人家庭的故事。《蘇拉》將《最藍的眼睛》的歷史時間向前、後延展,從第一次世界戰後寫到一九六○年代黑人民權運動方興未艾之際,其中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與黑人社群的變遷。《寵兒》則將摩里森關懷的歷史時間往前推到十九世紀中期,重啟美國蓄奴制度之下非裔子民的創傷記憶。《爵士樂》再度將歷史時間向後延伸,這次是以二十世紀初非裔子民由美國南方大舉北遷(the Great Migration)至北方大城市與哈林文藝復興(the Harlem Renaissance)的歷史為背景,寫一則黑人在紐約,融合音樂的愛情故事。《樂園》中的虛構敘事不斷指涉非裔美國真實的歷史事件,作為故事背景的歷史時間由一八七○年代延伸至一九七六年。 《LOVE》故事發生的時間則由一九二九年綿延到一九九○年代。可以見得,摩里森不斷透過小說創作,在不同的時間點拾起歷史片段,讓歷史時間在不同的故事之間互有交疊、互為補足,開展成為前後左右串接,過去、現在、與未來聲息互通的非裔族群歷史網絡。
而除了個別小說中歷史時間所構築的網絡,摩里森的作品彼此不斷進行互文對話,還因為摩里森經常在不同作品中,用不同手法與人物角度探索類似的主題,其中最明顯的包括歷史創傷、種族身分、愛與慾望、性別權力、自我實現與社群建構等等。摩里森曾經在訪談中表示,自己所有的故事均取材於「陳腔濫調」(clich??),並補充說明某些「陳腔濫調」尚未被棄如敝屣的事實,正印證了其存在的普世價值:「好的陳腔濫調是寫不盡的;永遠神秘。就像美和醜的概念對我而言永保神秘。」摩里森對許多主題的探索總是書有未盡,這讓她必需一次又一次回到相同的主題再作發揮。於是,摩里森的每一部作品總是言而未盡、意溢言外,或是指向未來另一種可能的詮釋,或是指涉過去未完待續的創作思維,讓讀者在她不同作品的主題和概念連結之外,還可以找到某種超出直線時間、超出出版先後順序、在多元的時間向度上環環相扣的可能。
當然,完整地分析摩里森到目前為止八部小說互相投射、互為記憶的時間結構,不是這篇譯序的篇幅所能允許的。以下我僅想試著以《蘇拉》為例,看摩里森如何早在一九七三年,就已經嘗試透過《蘇拉》搬演多元的時間向度,在虛構的記憶中寫歷史,讓小說敘述所建造的文字空間載入時間、介入歷史,揉合過去、記憶現在、與投射未來。藉由分析《蘇拉》的記憶與時間結構,我們可以看見記憶作為一種敘述策略和思考方式,試著推敲出一種特殊的「摩里森式」看歷史與寫歷史的方式,並進而思索《蘇拉》滋生的記憶在摩里森的創作宇宙中具有的意義。
二
《蘇拉》毫無疑問是一部攸關記憶的小說。當然,記憶在摩里森的小說敘述中可以說無所不在。《寵兒》中廣為流傳的名句,「那不是一則可以流傳的故事」("It is not a story to pass on"),鮮明地訴說了回憶的困難和痛苦。然而,《寵兒》全書寫的正是一則揮之不去的歷史記憶,寵兒的現身,具形化了非裔子民所遭受的種族創傷,讓歷史變得有血有肉,也讓記憶的過程變成一種即使不願意,終究還是不得不承受的痛。《蘇拉》當然也帶入了真實歷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戰場中「飽受摧殘與永久驚嚇」的薛德瑞(Shadrack),還有從戰場歸來之後即鎮日吸毒、夢想鑽回母親子宮的梅果(Plum),說明了戰爭為個人、家庭、與社群帶來的傷害。另外,整部小說在首章之後由「一九一九年」開始,到最後一章「一九六五年」,每一章均以一個特定的年份為標題,給了整部小說一個看似明確的歷史框架。和《寵兒》不同的是,《寵兒》的寫作源起於一則報導,記憶一名黑人母親寧願弒子也不希望其淪為奴隸的真實歷史事件,《蘇拉》則虛構了俄亥俄州的城鎮梅德里安(Medallion),以座落於這座城鎮山坡上的黑人社區(neighborhood)「麓谷」(the Bottom)為回憶對象。另外,《寵兒》再現的是一段不堪回首的黑人遭奴役歷史,《蘇拉》透過虛構搬演的則不只是黑人歷史的創傷片段,還包括在時光流逝中對「麓谷」深深的懷念。或許,兩本小說在處理記憶議題上最大的不同是,《寵兒》寫被壓抑歷史的復返(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history),寫復返的歷史幽魂為現時生活帶來的波動,逼得原本希冀自我封閉的現時生活不得不重新面對歷史過去,《蘇拉》則藉由創造虛構的記憶對象刻意搬演記憶的氛圍,形塑一種記憶的姿態,重點不盡在於重啟真實的歷史過去,也不在於是否有時間縱軸上確切的歷史指涉點,而在於記憶的形式本身能成就些什麼。
我在這裡想指出的是,《蘇拉》試著讓記憶變成一種敘述策略,一種認識自我與參與歷史有效的思考與再現方式。記憶一般總存在、衍生於現在與過去兩個時間點的往返辯証。當然,記憶的努力暗示著對直線式歷史發展的一種逆反(retrospection),讓現在不再只是過去歷史發展必然的(因此也是被動的)結果,而可以主動地開展歷史,或至少可以掌握歷史詮釋的主導權。不管引爆回憶的是過往歷史本身或存在現時的不滿與創傷感,回憶所帶出的時間結構總是迴旋式(cyclic)的,體現於過往與現在不斷地相遇、衝撞、協商。有趣的是,《蘇拉》書中的時間結構和一般回憶的時間結構不完全相同,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即是「麓谷」的虛構性。摩里森曾經在訪談中說明她創造梅德里安的緣起:
……〔和《最藍的眼睛》裡的黑人社區比起來,〕梅德里安比較難寫,因為它整個是虛構的;雖然是我母親從前告訴我的一些事,讓我想寫這樣的一個城鎮。母親剛結婚時,和父親一起搬到匹茲堡。我記得她說過那時黑人住在匹茲堡的山區,而現在他們住在煙塵瀰漫的市中心。山區的日子清朗多了,我就用了這樣的概念,但將故事移到俄亥俄州一座河畔小城。俄亥俄州緊傍肯達基州,因此大致也可以算作「南方」了。對黑人而言,那卻是很有趣的一州,它南邊依傍著俄亥俄河,北端卻又接上加拿大。許多廢奴論者住那兒,但是三K黨也住那兒。此外,那兒只有一個真正的大都市,和成千上百的小城鎮,而大多數黑人都住在小城鎮。……很多書總是寫黑人住在紐約或是一些具異國風情的地方,但我們生命中大部分的時間其實都花在小城鎮,那些散佈全國的小城鎮。那兒是……我們真正生活的地方。生活的精髓來自那兒,我們也在那兒有所成就,我說的成就不是成功,而是成就我們如今的樣貌。我想要寫那個,因為那樣的題材非常寬廣。
在這一段談話當中,摩里森首先指出梅德里安最初的創造靈感雖然來自於她母親的觀察,《蘇拉》關於這個城鎮的刻畫實則純屬虛構。其次,為了增添這座想像城鎮的象徵層次,摩里森安排讓其座落於俄亥俄州,這個在她眼中兼具美國南方風貌與北方特色的一州,既吸引了倡導黑人民權的廢奴論者,也是傳統種族主義者的駐紮地。再者,摩里森之所以想創造像梅德里安這樣的小城鎮,是因為那是大多數黑人真正生活的地方。有趣的是,當摩里森提到「我們生命中大部分的時間其實都花在小城鎮」,以及小城鎮是「我們真正生活的地方」,她用的是現在式動詞。小城鎮對美國非裔子民的意義,即使到了摩里森接受訪問,作出以上談話的一九七六年都還是現在式,《蘇拉》書中所「追憶」的黑人生活,其實不盡然已經成為過去。
這樣的分析,當然不是要指控《蘇拉》假借記憶過去之名,再現的其實是摩里森所理解、觀察到的黑人現時∕現實生活點滴,也不是要主張真實歷史年代在《蘇拉》這部小說裡就只是個框架,只是視作品需要而加入,就像俄亥俄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族裔人口而被挪用來為小說的敘述增添層次。藉此,我想要思考的其實是文學創作中使用記憶不同的方式與意義:文學透過記憶斡旋歷史,採用的方法是不是可以不僅僅是回到過去某一個明確的歷史時間,用現在的觀點去與那一段歷史協商?正因為事物通常要成為記憶才會有力量,就是要已經失落的才會產生魂牽夢繫的魔力,文學創作是否得以──甚至應該──自創記憶、虛構回憶,進而借用記憶帶來的力量更有效地介入歷史現時∕現實的書寫?
在同一個訪談裡,摩里森表示自己在撰寫《蘇拉》時很感興趣的是去創造一個地方,「一個像人物一樣令人印象深刻的城鎮、社群、社區」,而又不至於讓這個地方定於一,失去駁雜與多樣性,淪為大寫的「城鎮、他們」。地方的書寫與空間的塑造或許才是《蘇拉》的重心。然而,從小說的第一頁起,摩里森念茲在茲要創造的黑人社區「麓谷」就已經被放入記憶的框架,曾經存在,如今卻已化為過往煙塵。弔詭的是,「麓谷」的美好和價值似乎也正體現於它在小說中是多麼令人難以忘懷。正因為被擺入了時間的過去,「麓谷」的一切無不沾染一層懷舊情緒,進而帶來想像空間與情緒感染力:連繫「麓谷」與梅德里安山谷的道路上,滿樹梨花原本無甚特別,但是當有人發現梨樹已經成為「過往陳跡」,曾經「隔著滿樹花海向路過的行人鬼吼大叫」的小孩聲音,於是幻化為時光流逝中再也揮之不去的鬼魅聲響。兩個黑人小女孩手牽著手到一家叫「快樂屋」的冰淇淋店看似稀鬆平常,但是當這個動作被放入一九二二年那個「吃冰淇淋還太冷」的春天裡,成為記憶的一部分,這個動作就變成了意義深長的歷史里程碑。同樣的道理說明了妮兒(Nel)的臥房為何在沾染了朱德(Jude)與蘇拉(Sula)偷情的記憶之後就變得「搖搖晃晃」,小得似乎不再容得下她;而蘇拉在埃傑克斯(Ajax)離開之後,同樣也發現自己的屋子裡,「門邊的鏡子現在不是門邊的鏡子了」,埃傑克斯常坐的廚房紅色搖椅現在也不只是張搖椅了。一旦蒙上記憶,所有的家俱都變得突兀搶眼。諸如此類的例子,說明了地方總是在記憶之中找到無窮盡的存活、延展空間。就是要透過記憶向四面八方、過去未來綿亙延伸的時間網絡,地方的聲音、氣味、溫度、觸感、氛圍才能無所不在,四處滲透。
三
或者我們可以試著主張,《蘇拉》刻意將地方書寫擺入記憶,讓地方在時間的多元向度中變得活靈活現。摩里森是在時間軸度上找空間,搬演時間成為開展小說敘述空間的一種方法。而循著這樣的論點,摩里森作品中經常被討論的「再記憶」(rememory),似乎應該可以被理解為不只是「再一次」回到歷史某一刻去記憶過去;「再記憶」可以是一種「重新拼湊部分」(re-member)的努力:透過虛構文字拼湊多層次的時、空,好虛擬出一方地理空間,一段歷史縱深,讓回憶過去的姿態為介入現實,甚至想像未來鋪路。事實上,摩里森在《蘇拉》首頁的獻辭裡就已經透露了將現在放入記憶框架的意義:
思念一個還會在身邊停駐很久的人,
是莫大的福分。
謹以此書獻給福德和史萊德,
他們還在我身邊,
我對他們的思念卻已然開始。
在這一段獻辭裡,摩里森不只將《蘇拉》獻給了自己的兩個兒子福德(Harold Ford Morrison; 1961- )與史萊德(Slade Kevin Morrison; 1964- ),更為《蘇拉》這部小說的記憶敘述策略下了一個有趣的註腳:「思念現在」不只表達了對現時人事物的珍惜,更是用歷史光環為之加冕,將其鑲框留駐在文字編寫的歷史中,成為時光流逝中值得追憶的對象。
瞭解了記憶的魔力,我們就不難了解摩里森為何要在《蘇拉》的敘述中安排層層疊疊的記憶。不只在小說的一開始要由匿名的敘述者追憶早已「蕩然無存」的「麓谷」種種,小說的最後一章還要透過妮兒懷念一九二○年代「麓谷」那些迷人的男孩。而在小說敘事推進的過程中,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六五年看似直線發展的敘述時間之下,埋藏的依然是一圈一圈迴旋的記憶:一九二三年伊娃(Eva)追憶著梅果,思緒徘徊在一八九五年嬰兒梅果便秘,那一個椎心刺骨的寒冷冬夜,還有一九二一年燒死梅果的明亮火焰之間;一九四○年蘇拉在病榻上回憶著一九二二年夏天,十二歲的她和妮兒兩個人沿著河岸奔跑,風如何吹著她們的洋裝緊貼兩腿之間;一九四一年薛德瑞依然念念不忘一九二二年那個曾經來拜訪過他的小女孩蘇拉,以及他對她「永遠」的承諾。而當「麓谷」居民在一九四一年站在新河路的隧道工程之前,他們又如何能忘記從一九二七年開始,白人給的那一個一直沒能實現,像「枯葉般死亡」的工作承諾。當然,到了一九六五年,妮兒還必須去推敲一九二二年小雞崽(Chicken Little)摔入河中那一個事件對她和蘇拉的意義,還得重新去思索一九三七年當朱德離開,而自己也與蘇拉決裂時,她悲傷的源頭究竟何在。摩里森不斷在敘述過程中創造新的記憶。《蘇拉》每個章節均呈現死亡,或者是具象徵性的社區、自我、友誼之死,或者是小說人物生命的殞落,未嘗不是為了要讓懷念與哀悼無所不在。摩里森坦白指出,她讓蘇拉在一九四○年那一章就死去,為的就是要她被懷念,成為小說所搬演之記憶的一部分。
而除了利用小說人物彼此之間不斷纏繞累積的記憶來打破章與章的直線連結,摩里森還不時讓全知的匿名敘述聲音進入敘述,帶領讀者跳離特定事件發生的時空,超越稍縱即逝的現時剎那,給與個別事件在宏觀歷史中的視角。比方說,在描述了一九二○年妮兒的紐奧良(New Orleans)之旅,點明了妮兒如何在旅行之後發現自我,全知的敘述聲音立刻跳出事件當下時空的限制,指出這場旅行其實是妮兒生命中絕無僅有的一次旅行。在開始寫「麓谷」居民在最後一個「全國自殺日」跟隨著薛德瑞,宛如「花衣魔笛手所帶領的一列隊伍」,走向新河路的隧道口之前,敘述聲音也是先跳到事件發生之後多年:「多年以後,大夥兒會爭論究竟是誰先發難的。」又,在寫到妮兒與朱德的婚禮,妮兒望著蘇拉離開「麓谷」的背影,敘述聲音又再一次轉向已知的未來:「她們要十年之後才會再見面了,而且見面時天空會滿佈飛鳥。」《蘇拉》在文字空間中構築了一個過去、現在、未來互通的神話時間結構,將時間空間化。於是,不只是過去以記憶的形式可以如影隨形,未來順著時間軸線的伸展也可能歷歷如繪。最明顯的例子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陸戰場歸來,飽受心靈創傷的薛德瑞躺在醫院病床上,渴望藉由記憶安撫自我的恐懼與不確定感,於是他「放任思緒溜進任何記憶洞口」。而他看見的竟然是自己生命未來的一個片段,他即將在「麓谷」定居之後的生命片段:「他看見面向河流的一扇窗口,曉得河中有許多魚。有人正在門外柔聲細語……」。薛德瑞在追憶一個還沒有到來的世界∕視界。在這裡,《蘇拉》搬演的記憶已經不僅僅攸關過去時光的回返,或是對現存的人事物進行歷史加持,而是在投射未來──一個或者可以幫助我們將過去與現在放進歷史框架、看得更清楚的未來。
摩里森擅寫記憶,執著於回憶的重要性,但是回憶的思緒在她的作品中不只可以進入過去,還可以摸索開啟未來的時間窗口。摩里森不只一次表示,創作的目的是為了要「想見想不到的」("think the unthinkable")。寫作應該指向未來,意在想像的開展。在《蘇拉》所鋪陳的時間網絡中,我們的確可以看見追悼過去的策略和投射未來的努力如何密不可分。《蘇拉》表面上記述一個黑人社區的崩潰、女性情誼的失敗。這一個「麓谷」淪為過往煙塵的記憶,似乎悲觀地陳述非裔子民在美國主體凋零與社群離散的宿命。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麓谷」只是在虛構的情節敘述中被說成是消失了。《蘇拉》一邊搬演「麓谷」辛酸的歷史,一邊其實對這個黑人社區的愛恨點滴投以最深情的一瞥,既看它如何走向傾圮,也看它曾經如何能包容、滋養各色各樣的非裔子民。更明確地說,透過記憶,《蘇拉》寫的不只是已經消失的虛構黑人社區「麓谷」,而是在投射一個(過去或未來、或一直)可能存在的黑人生活方式。是《蘇拉》構築的時間讓「麓谷」永遠存在,成為令人永難忘懷,得以介入現在與未來非裔美國族群想像的一塊地方。
簡單地說,虛構過去成了改變未來的一種策略。過去的不可能可以為未來的可能鋪路。在《蘇拉》的最後一章,妮兒來到「櫸木果墓園」悼念死去已有二十五年的蘇拉。蘇拉和母親哈娜(Hannah),還有梅果、珍珠(Pearl)四個琵思(Peace)家族的成員埋在一起──「四塊石碑上的字,連起來念像首頌歌:琵思一八九五~一九二一,琵思一八九○~一九二三,琵思一九一○~一九四○,琵思一八九二~一九五九。」摩里森在這裡不只玩弄「Peace」既是姓氏,也意味「和平、平靜」的一字雙關,更饒富意義地翻轉歷史過去的失落為對未來的憧憬。妮兒這樣解讀這一排像頌歌般的墓誌:「它們代表的不是死去的人。它們是一排字。也不只是字。它們是祝願,是渴望。」由哀悼逝去的琵思家族與∕或失落的和平∕平靜,妮兒的記憶被轉化為對未來的祈願與祝禱。透過《蘇拉》在文字裡對殞落的琵思∕和平∕平靜的思念(to miss the missing Peace/peace),琵思∕和平∕平靜或許會獲得更多在未來現實中實現的可能。
四
《蘇拉》撰寫記憶,透過文學虛構為非裔子民創造值得追憶的歷史,作為一部小說創作,它當然也成為摩里森創作史中難以被忘懷的記憶。也許,有人會認為《蘇拉》屬於摩里森早期的創作,在形式和內容上都還充滿試探性,在非洲歷史與神話運用的完整性上可能不及《所羅門之歌》與《黑寶貝》,在刻畫歷史創傷與回返記憶的感情強度上不及《寵兒》,在歷史格局與敘述的複雜度上則比不上《爵士樂》、《樂園》、以及《LOVE》。摩里森自己也曾經表示,她是在完成了《所羅門之歌》之後,才確認了自己的作家身分。《最藍的眼睛》和《蘇拉》因此可以說是摩里森在確定自己成為作家之前,摸索自我生命可能的實驗創作。但也許正因為《蘇拉》是試探之作,摩里森將它寫成了篇幅精短、探索的主題卻多元得幾近千頭萬緒的一部作品。摩里森表示當她開始著手創作《蘇拉》時,只曉得自己要寫一部「有關善惡與友誼」的小說。在評論者眼中,《蘇拉》卻形貌萬千,容許各家觀點殊異的詮釋:《蘇拉》可以是一則寓言、一部女同性戀小說、一部黑人女性成長小說、一部英雄追尋小說、一部歷史小說、一部戰爭(或反戰)小說、一個典型的後現代文本、一部女性心理探索小說、一部諷刺二元思維的文學作品等等。摩里森將女主角蘇拉寫成一位將生命當成實驗,找不到藝術形式的危險藝術家;她自己在寫作《蘇拉》的過程中,未嘗不也在實驗種種題材與敘述形式。用摩里森自己的話來說,《蘇拉》發展到最後其實像一面「碎裂的鏡子」──蔓生的時間、枝節、畫面等著一次又一次被重新拼湊,重建因果。
在二○○七年的現在重新展讀摩里森一九七三年的舊作,面對《蘇拉》所銘記的片段、記憶的層疊、與意義的糾結,一方面我們可以說,隨著摩里森一本又一本新的作品面世,當初她創作《蘇拉》時某些未盡發揮的思考點已逐漸被延展、擴大,是後起的創作不斷充實了《蘇拉》書寫與敘述的密度。另一方面,《蘇拉》雖然被創作在先,卻可以被閱讀在後。迴旋的時間結構給了我們在閱讀摩里森作品時理當要能夠前後左右逢源的啟示:《蘇拉》創造的記憶因此也可以不斷介入、充實讀者對後起作品的理解。比方說,讀到《樂園》裡的黑人社群(community)「路比」(Ruby),其堅實的父系威權、封閉的排外政策與集體暴力,令人不得不想起「麓谷」作為一個女人當家、疆界不明、包容異己的社區(neighborhood),所提供的另一種黑人生存策略與族裔倫理。而當留心(Heed)和柯莉絲汀(Christine)在《LOVE》的末章終於跳出多年以來對父權∕錢的執迷不悟,重拾兩人年少時期的同性情誼時,摩里森似乎又回到《蘇拉》裡對女性情誼的探索:蘇拉和妮兒的情誼成為留心和柯莉絲汀關係的最佳註腳。當然,當我們閱讀摩里森在《蘇拉》之後的創作,面對敘事結構與人物關係愈見複雜斷裂的一部又一部小說,逐漸習於在閱讀摩里森的過程中努力地在腦海裡為小說中的故事繪製年表,一次又一次找出、修正各個事件發生的時間先後順序,《蘇拉》看似平鋪直敘,披著直線時間表面,暗底裡其實事件糾結、情感層疊的書寫方式,或許別具一種敘述的張力與情緒感染力。
我個人閱讀《蘇拉》的歷史也包含了一連串迴旋的「再記憶」。一九九二年第一次接觸到的摩里森作品就是《蘇拉》。那時在著名的族裔文學學者李有成教授的帶領之下,初探非裔身分政治與文學,對摩里森筆下複雜的人物與文字之美有了朦朧領會。一九九六年在美國密西根大學「酷兒理論」的課堂上,我有了第二度接觸《蘇拉》的機會。再一次細讀《蘇拉》,我思考摩里森如何在一部充斥傳統異性戀關係的作品中,探索同性愛戀的可能與意義,同時驚豔於她書寫情愛與慾望的文字功力。不再是研究生之後,我在二○○○年將《蘇拉》帶進自己的課堂;看著學生從各種觀點嘗試去理解這部作品,建立和這部作品的連繫,我再一次看見《蘇拉》在精薄外表之下的豐富內蘊。其實,每一次和《蘇拉》再相遇,情緒上都像極了小說末了的妮兒在一九六五年重新回顧一九二○年代的「麓谷」還有她和蘇拉的關係。這樣的回顧不是為了想要返回歷史過去,也不光為了滿足一種懷舊的慾望,而是想透過生命中不同時間點的連結,建構新的時間網絡,好讓記憶釋放開來,在時光流逝之中找到重思過去、認識自我的空間。
我要感謝資深摩里森研究學者何文敬教授的推薦,以及台灣商務印書館的支持,讓我有機會翻譯《蘇拉》。何教授細心閱讀了譯文與譯序,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更慷慨傳承了翻譯摩里森作品的經驗,讓筆者受益良多。我還要感謝我的學生,也是極具潛力的新生代摩里森研究學者楊志偉在整個翻譯過程中的協助。他細心地校訂翻譯初稿、找尋資料、撰寫部分譯註、並就翻譯文字的使用提出許多精彩的建議,讓譯文增色不少。我還要特別感謝台師大英語系高瑪麗教授(Professor Mary Goodwin)。她不厭其煩地回答我對《蘇拉》文字上的許多疑問,讓譯文得以更精確地掌握摩里森的文字奧微。另外,在翻譯的過程中,筆者再次拜讀了何文敬教授《寵兒》與馮品佳教授《LOVE》的中譯本,深受兩位學者流暢的譯筆與學術用心所啟發。最後,我要感謝商務編輯團隊在編務上的專業協助,讓譯文得以最完整的面貌呈現在中文讀者面前。摩里森在文學創作中搬演記憶,而筆者謹希望能藉此序文,記憶為《蘇拉》中文譯作付出努力的朋友們,還有二○○七年從盛夏到深秋,這一段翻譯《蘇拉》的難忘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