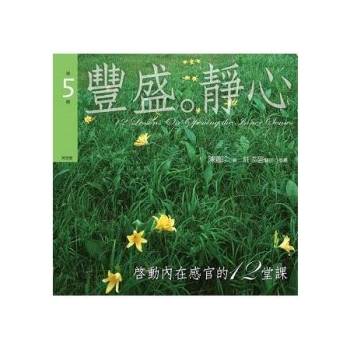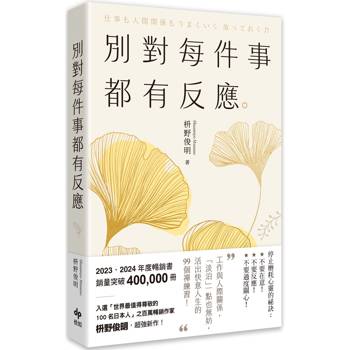隱居在麻豆的作家
人生稱圓滿,快意駕輕舟。
迎面徐風吹,從此不回頭。
春天乍到,麻豆鎮公所便在大街小巷廣插旗幟,迎風招展。上面有幾個大字;「柚花飄香,單車愜意行!」
連續好幾年了,熱熱鬧鬧的元宵節好像才過去不久,鎮公所便透過這些旗幟提醒我們;文旦柚開花了,大家要準備好。三月初旬某一天,大家在鎮公所選定的地點集合,坐在文旦樹下喝咖啡,享受柚花香味。或是一人騎一部單車,夫妻同行、朋友結伴,親子同樂都好。郊遊途中,觀賞雪白柚花的美麗倩影,快快樂樂的玩一天。
在台灣,好像不管在哪個地方,我只要提到自己的家鄉,台南縣麻豆鎮,大家都會很快地接下來說:「喔,那個出產麻豆文旦柚的地方……。」
麻豆文旦柚,父老相傳,清朝末年在麻豆種植成功。日據時期,尪祖府附近「買郎宅」的文旦柚被呈獻給日本天皇品嚐,博得好評。從此麻豆文旦柚享有盛名,每年初春,雪白柚花開遍樹梢,形象高潔,香味清牙,真是麻豆人的驕傲與喜悅。
只不過,鎮公所舉辦柚花觀賞大會那天,我坐在文旦樹下喝著可口的咖啡,心裡卻有一種遺憾。在潔白高雅的柚花當中,我依稀看到一個逐漸遠去的身影。他是隱居麻豆多年、人品高潔的作家,也是詩人。畫家的粟耘,在三月四日凌晨悄悄地去世了。說悄悄地去世,是因為很少麻豆人知道有他這一號人物,在這個政客滿嘴謊言,人心混亂迷惑的時代,謙卑自牧,喜歡過簡單、自在隱居生活的粟耘,雖然使我敬重有加,可是,恐怕連住在他隔壁的鄰居也不知道他的真正身分吧!
十多年前,任職文建會的丘秀芷有一天突然打電話到麻豆來,問我有沒有辦法聯絡到粟耘,想邀他參加一次作家的旅行活動。
我心中一震,才知道粟耘果然隱居到我們麻豆鎮來了。可是我為難地表示,粟耘是厭惡都市生活,厭惡社交活動才選擇隱居在鄉下的。我貿然去找他,有可能他根本沒讀過我的作品,不知道有我這個同道,場面一定很尷尬。更何況,我一向不善於交朋友,根本不知道他隱居在麻豆的哪一個角落,所以沒辦法聯絡到他。
之前,我在報章雜誌上看到粟耘的作品,一定會仔細拜讀。他人品高潔,如同古代的陶淵明;他的小詩和構圖精簡的水墨畫,最讓我欣賞。現在,知道他就隱居在我們小鎮,心裡真是高興。麻豆,以前寫成麻荳,在台灣原住民西拉雅的母語當中,是「眼睛」的意思。粟耘可說是我們麻豆人的靈魂之眼。他以超凡自在的眼光,穿透虛偽、混亂的紅塵世界,把他體會到的庶民的平實、善良、謙卑一一呈現在詩文中、圖畫中,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以後再看到他的作品,我常常莞爾一笑,心領神會地點點頭。我知道他詩文中寫的大概是哪一個場景,哪一個人物。然後,我也知道他隱居在麻豆郊外「總榮里」的偏僻地方。雖然十多年來,我們曾經在相同的報紙上發表文章,也在兩、三家相同的出版社出版作品,但是我從來不曾去拜訪他。我尊重他是不喜歡被打擾的人,所以偶而路上看到他和太太各騎一單車出來逛逛,我也只是默默地站在一旁,不曾想過上前攀談。
粟耘隱居的「總榮里」往北約兩、三百公尺,叫「水堀頭」,俗名「龍喉」,這是我們麻豆大名鼎鼎的地方。明朝末年、清朝初年,該地是相當熱鬧的碼頭,福建漳州、皇州的漢人大量移居到此,利用小船可航至台南安平港和嘉義布袋港,其繁華熱鬧可想而知。移民從大陸供奉「李池吳朱范」五府千歲在此建廟,他們是愛民有加的唐朝名將,因此香火鼎盛,遠近馳名。只可惜,清朝時有地理師傳言,水堀頭上空瑞雲光彩,麻豆地區可能出生大人物,於是皇帝派人前來水堀頭破壞風水,斬斷龍脈,大量埋入榨蔗糖的石車、大木以及污穢的狗血,終於使水堀頭水路逐漸淤塞,市景凋零,成為人煙稀少的荒涼地區。
五王廟中的「李池吳朱范」五府千歲也被迫遷徙,流落至現今北門鄉的南鯤鯓,幾乎與麻豆人失去了聯繫。四十幾年前,有農夫在水堀頭附近碰上「李池吳朱范」五府千歲化身的老人,告訴他麻豆地理即將復興,請集合眾人之力,在埋入石車、大木、污穢狗血之處開挖,擇地建廟,必有利於地方發展。這個消息一傳十、十傳百,慢慢地形成地方上的一件大事。所以,我唸國小的時候,也跟著地方父老參加挖掘工作,現場撫觸泥土的奇形怪狀石車、大木,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的美妙經驗。不久,麻豆代天府五王廟又蓋起來了,地方父老相信,麻豆以後一定會文風鼎盛,人才輩出。
在這種氛圍中,高潔自矜的粟耘偕同太太隱居於此,也是冥冥中註定的吧!粟耘本名粟照雄,太太名鄭顗,他們在三十六歲那年不再求職謀生,開始在樸素鄉下讀書、寫作、畫圖,閒暇則養雞種菜,怡然自得。我比粟耘小兩歲,跟他一樣沒有手機,不會使用電腦,不會開車。大概因為這樣的緣故,我看粟耘的一切都很順眼。
幾年前,有一個下午,我拿稿件到郵局去寄,正好粟耘站在我前面,我看他一身寬鬆衣服,滿頭白髮,猜想他要寄的是飄逸如陶淵明的詩吧!結果他反覆摸摸口袋,窘迫地向櫃台小姐說:「抱歉,一個十元硬幣大概掉了,沒辦法寄掛號,我等一下再來。」
「沒關係,沒關係。」櫃台小姐說,「大家都是熟人,我先幫您墊,下一次您再還我就好。」
粟耘搖搖頭,堅持回家拿錢。
「我也是要投稿的,讓我幫您付這十元吧!」我衝動地想要這樣說。可是,想到粟耘都不肯接受熟識的櫃台小姐的幫忙,怎麼肯接受我這個陌生人的協助。因此,我終究沒有開口,只能默默地看著清瘦的粟耘騎上車,緩緩地離去。
人生稱圓滿,快意駕輕舟。
迎面徐風吹,從此不回頭。
發現肝癌惡化後,粟耘在台南市成功大學附屬醫院裡寫下這一首詩,真是瀟灑飄逸,了無牽掛。他從二十多本著作中,挑選最滿意的部分,出版「沙子自己知道」一書。沙子謙卑自在,在浩浩蕩蕩的海水中飄流滾動,無可無不可,何曾眷戀什麼?可是它知道生命的尊嚴、靈魂的高潔。粟耘就是這樣一粒沙子,知足常樂,不留戀不喧嘩。
今天出門,又難大街小巷中看見迎風招展的大旗,上面寫著「麻豆代天府丙戌年五朝王醮祭典」。原來,三年一科的五府千歲出巡大祭典又將開始了。連續三天旗幟飛揚,萬頭攢動,鑼鼓喧天的熱鬧,會把麻豆鎮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縷空氣都驚動喚醒,這樣的騷動,不知能不能把粟耘敏銳的靈魂召喚回來。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快意輕舟─丘榮襄的趣味人生的圖書 |
 |
快意輕舟: 丘榮襄的趣味人生 作者:丘榮襄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7-01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74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187 |
社會人文 |
$ 198 |
傳記 |
$ 205 |
中文書 |
$ 205 |
歷史人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快意輕舟─丘榮襄的趣味人生
「當你歡樂的時候,抬頭看看雲吧,雲彩變幻莫測,告訴你「人生短暫,歡樂要把握。」當你愁苦的時候,抬頭看看雲吧,雲彩千變萬化,告訴你「再大的苦惱與悲愁,也會消逝得無影無蹤。」
有一位作家──丘榮襄老師,他是退休的老師,是台南麻豆人。麻豆大大小小的作家也不少,但,這位特別不同。他經常關懷憂鬱症和監獄裡的受刑人,他寫了很多勵志的書籍……
他曾是「放牛班」的老師,這一個難得的經驗,讓他後來成為一位心理諮商教師。
他要敷平所有的、來得及與還未發生的,不平與傷害。
從初中榜示的喜悅,在台南一中、中興大學,完成了他的學業。退伍後,他成為一位國文教師,開始為年少時的夢想著色。循著求學、教學與生活的片段,漸漸的,從文字裡發現:其實,從年少至今,他所關懷的,正是在社會上、生活裡,一些永遠處於弱勢的人群。他們的身影,出現在他的小說裡、電影中,無一不牽動著他每一處神經。
在這些回憶的文字中,人生可圈可點,正如,麻豆鎮上的柚子清香,也隨之撲鼻而來。
作者簡介:
丘榮襄
台南縣麻豆鎮人,中興大學法律系畢業,彰化師大心理輔導研究所結業。曾任教於國中、高中及高職、擔任過心理輔導老師。在嘉義監獄、台南市憂鬱症關懷協會擔任心理輔導志工,現任台南市憂鬱症關懷協會理事。
熱愛寫作,已出版小說與散文有《叛逆的青春》、《愛要及時》、《在逆境中找到生命的出口》等四十餘本,長篇小說《可憐花》曾改拍成電影。短篇小說由「中華民國筆會」譯成英文,介紹到歐美、日本。
章節試閱
隱居在麻豆的作家
人生稱圓滿,快意駕輕舟。
迎面徐風吹,從此不回頭。
春天乍到,麻豆鎮公所便在大街小巷廣插旗幟,迎風招展。上面有幾個大字;「柚花飄香,單車愜意行!」
連續好幾年了,熱熱鬧鬧的元宵節好像才過去不久,鎮公所便透過這些旗幟提醒我們;文旦柚開花了,大家要準備好。三月初旬某一天,大家在鎮公所選定的地點集合,坐在文旦樹下喝咖啡,享受柚花香味。或是一人騎一部單車,夫妻同行、朋友結伴,親子同樂都好。郊遊途中,觀賞雪白柚花的美麗倩影,快快樂樂的玩一天。
在台灣,好像不管在哪個地方,我只要提到自己的家...
人生稱圓滿,快意駕輕舟。
迎面徐風吹,從此不回頭。
春天乍到,麻豆鎮公所便在大街小巷廣插旗幟,迎風招展。上面有幾個大字;「柚花飄香,單車愜意行!」
連續好幾年了,熱熱鬧鬧的元宵節好像才過去不久,鎮公所便透過這些旗幟提醒我們;文旦柚開花了,大家要準備好。三月初旬某一天,大家在鎮公所選定的地點集合,坐在文旦樹下喝咖啡,享受柚花香味。或是一人騎一部單車,夫妻同行、朋友結伴,親子同樂都好。郊遊途中,觀賞雪白柚花的美麗倩影,快快樂樂的玩一天。
在台灣,好像不管在哪個地方,我只要提到自己的家...
»看全部
目錄
序:書香情緣
緣起:生日是回憶的好日子
隱居在麻豆的作家
鹽分地帶文藝營
長篇小說改拍成電影
名作家余阿勳老師
意外驚喜
當了小老師
快樂時光
從曾文初中到南一中
台南一中的文科學生
「呆園」季刊
難忘的教官
遇騙記
音樂老師給我62分
中興大學法律系
法庭上
圖書館與彈子房
兩位室友
幼獅通訊社的記者
世間奇男子
正青文藝社社長
再會吧!貧血的太陽
空軍少尉
老士官,小瘦子
我成了國中國文老師我的學生
創辦特刊
結婚
考績乙等
「新學風」的誕生
「放牛班的春天」
師鐸獎
網球與我
高雄師範大學
彰化師範大...
緣起:生日是回憶的好日子
隱居在麻豆的作家
鹽分地帶文藝營
長篇小說改拍成電影
名作家余阿勳老師
意外驚喜
當了小老師
快樂時光
從曾文初中到南一中
台南一中的文科學生
「呆園」季刊
難忘的教官
遇騙記
音樂老師給我62分
中興大學法律系
法庭上
圖書館與彈子房
兩位室友
幼獅通訊社的記者
世間奇男子
正青文藝社社長
再會吧!貧血的太陽
空軍少尉
老士官,小瘦子
我成了國中國文老師我的學生
創辦特刊
結婚
考績乙等
「新學風」的誕生
「放牛班的春天」
師鐸獎
網球與我
高雄師範大學
彰化師範大...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丘榮襄
- 出版社: 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7-01 ISBN/ISSN:978957052384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6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歷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