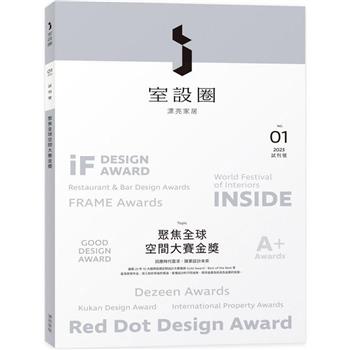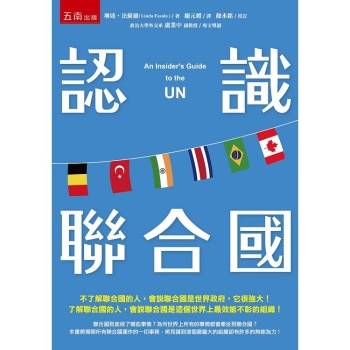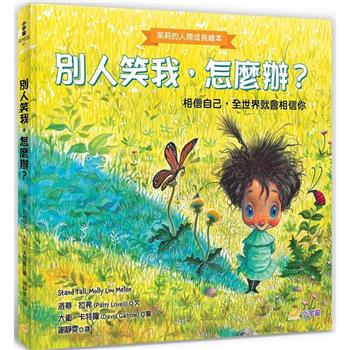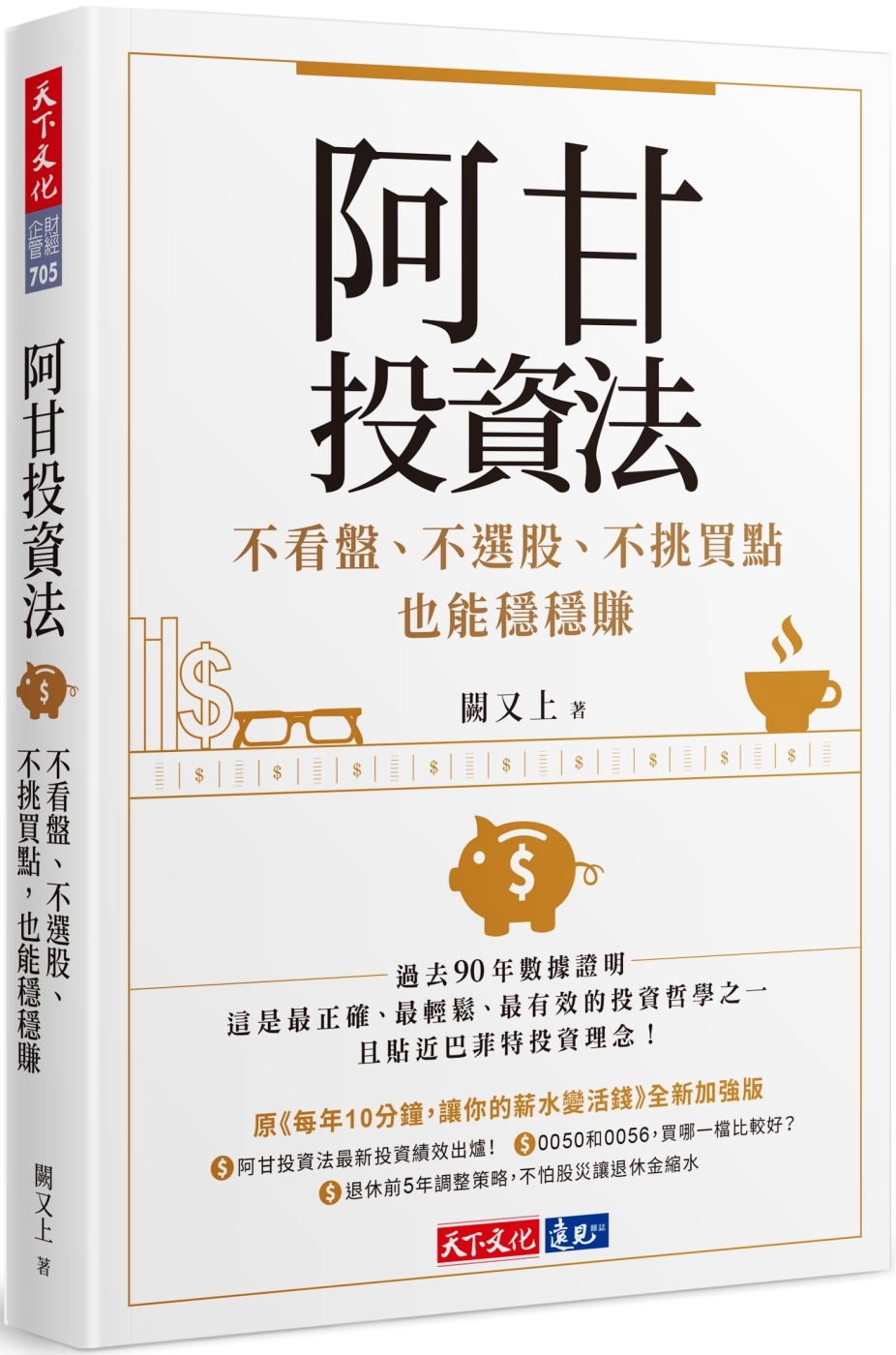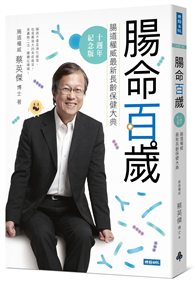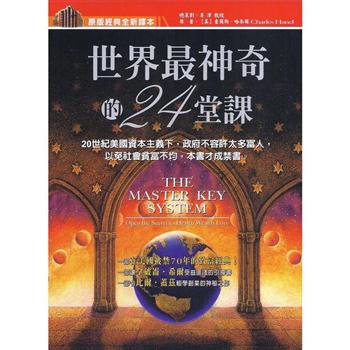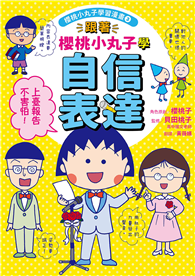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新人生觀(修訂本)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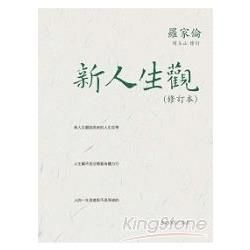 |
新人生觀(修訂本) 作者:羅家倫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06-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54 |
個人成長 |
電子書 |
$ 154 |
生活哲學 |
$ 173 |
社會人文 |
$ 174 |
近代文學 |
$ 187 |
近代文學 |
$ 187 |
社會人文 |
$ 204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本書特色】
羅家倫在抗戰期間,在中大校園連續發表了十六次演講,大氣磅礡,後來集結成為《新人生觀》,激勵了無數青年奮發圖強,公認為是抗戰中最有影響力的不朽勵志作品!
【內容簡介】
在這個舊道德標準已經動搖的時代,建立新人生觀,更有重要的意義和使命。我們要趕著每一個變動,增加自己的生存力量。新的人生哲學不是專講「應該」,而是要講「不行」;不專恃權威或傳統,乃要以理智來審查現實的要求和生存的條件;不專講良心良知,而講整個人生及其性格風的養成,並從經歷和習慣中樹立其理想的生活。所以新的人生觀是動的人生觀,是創造的人生觀,也是大我的人生觀。
作者簡介:
羅家倫
1897年生。少承庭訓,習讀文史,後曾就讀於南昌英文夜校、上海復旦公學。
1917年以作文滿分考入國立北京大學文科,期間曾主編《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運動中,撰寫《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為學生領袖之一。
1920年赴美留學,先後於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深造,接著遊歷歐洲倫敦大學、柏林大學、 巴黎大學。
1926年回國,任教於國立東南大學歷史系及附中。稍後以一介書生投筆從戎參加北伐軍,任北伐軍總司令 部參議、編輯委員會委員長、戰地政務委員兼教務處長,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教務主任、代教育長。
1928年8月,清華學校更名國立清華大學,出任首任校長。
1932年8月,出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1941年調離中大,曾出任滇黔黨政考察團團長、西北建設考察團團長、監察院首任新疆省監察使。
1945年抗戰勝利後,先後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籌備會議代表、首任駐印度大使兼世界各國駐印使節團團長。
1949年到臺,先後出任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中國筆會會長、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等職。
1969年12月25日在臺北逝世。
【修訂者簡介】
周玉山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專任副教授。學歷:文化大學中山研究所博士。研究專長:中國新聞思想史/副刊與文藝/中國大陸新聞傳播。
建立新人生觀,就是建立新的人生哲學。它是對於人生意義的觀察,生命價值的探討,要深入的透視人生的內涵,遙遠的籠罩人生的全景。我們生命的意義是什麼?生在世上有什麼價值?我們如何能得到富有意義和價值的生命?我們的前途又是怎樣?這些不斷的和類似的問題,我們今天不想到,明天不定會想到;一個月不想到一次,一年不定會想到一次;在紅塵滾滾,頭昏腦漲的時候縱然不想到,但正值曉風殘月,清明在躬的時候,不定也會想到。想到而不能作合理的解答,便是面臨人生極大的危機。若果有永遠不想到的人,那真不愧為醉生夢死...
- 作者: 羅家倫
- 出版社: 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06-01 ISBN/ISSN:978957052488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4頁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