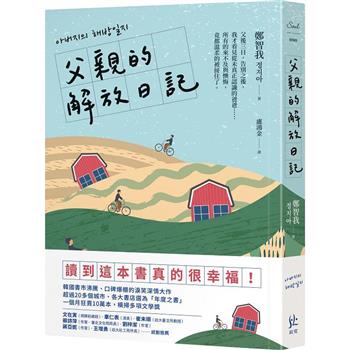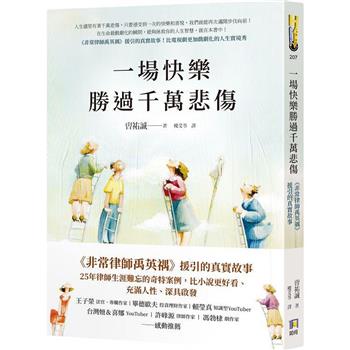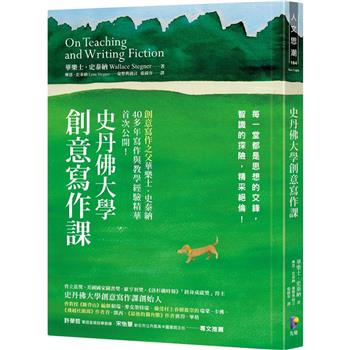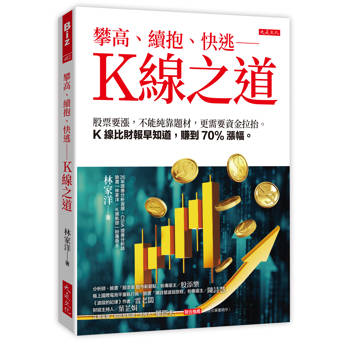序
《詞選》的工作起於三年之前,中間時有間斷,然此書費去的時間卻已不少。我本想還擱一兩年,等我的見解更老到一點,方才出版。但今年匆匆出國,歸國之期遙遙不可預定,有些未了之事總想作一結束,使我在外國心裡舒服一點。所以我決計把這部書先行付印。有些地方,本想改動;但行期太匆忙,我竟無法細細修改,只好留待將來再版時候了。
我本想作一篇長序,但去年寫了近兩萬字,一時不能完工,只好把其中的一部分—「詩的起源」—抽出作一個附錄,其餘的部分也須待將來補作了。
今天從英國博物院裡回來,接著王雲五先生的信,知道此書已付印,我想趁此機會寫一篇短序,略略指出我選詞的意思。有許多見解,已散見於詞人的小傳之中了;我在此地要補說的,只是我這部書裡選擇去取的大旨。
我深信,凡是文學的選本都應該表現選家個人的見解。近年朱彊□先生選了一部《宋詞三百首》,那就代表朱先生個人的見解;我這三百首的五代宋詞,就代表我個人的見解。我是一個有歷史癖的人,所以我的《詞選》就代表我對於詞的歷史的見解。
我以為詞的歷史有三個大時期︰
第一時期︰自晚唐到元初(856-1250),為詞的自然演變時期。
第二時期︰自元到明清之際(1250-1650),為曲子時期。
第三時期︰自清初到今日(1620-1900),為模倣填詞的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詞的「本身」的歷史。第二個時期是詞的「替身」的歷史,也可以說是他「投胎再世」的歷史,第三時期是詞的「鬼」的歷史。
詞起於民間,流傳於娼女歌伶之口,後來才漸漸被文人學士採用,體裁漸漸加多,內容漸漸變豐富。但這樣一來,詞的文學就漸漸和平民離遠了。到了宋末的詞連文人都看不懂了,詞的生氣全沒有了。詞到了宋末,早已死了。但民間的娼女歌伶仍舊繼續變化他們的歌曲,他們新翻的花樣就是「曲子」。他們先有「小令」,次有「雙調」,次有「套數」。套數一變就成了「雜劇」;「雜劇」又變為明代的戲曲。這時候,文人學士又來了;他們也做了「曲子」,也做劇本;體裁又變複雜了,內容又變豐富了。然而他們帶來的古典,搬來的書袋,傳染來的酸腐氣味又使這一類新文學漸漸和平民離遠,漸漸失去生氣,漸漸死下去了。
清朝的學者讀書最博,離開平民也最遠。清朝的文學,除了小說之外,都是朝著「復古」的方面走的。他們一面做駢文,一面做「詞的中興」的運動。陳其年、朱彝尊以後,二百多年之中很出了不少的詞人。
他們有學《花間》的,有學北宋的,有學南宋的;有學蘇辛的,有學白石、玉田的,有學清真的,有學夢窗的。他們很有用全力做詞的人,他們也有許多很好的詞,這是不可完全抹殺的。然而詞的時代早過去,過去了四百年了。天才與學力終歸不能挽回過去的潮流。三百年的清詞,終逃不出模倣宋詞的境地。所以這個時代可說是詞的鬼影的時代;潮流已去,不可復返,這不過是一點點迴波,一點點浪花飛沫而已。
我的本意想選三部長短句的選本:第一部是《詞選》,表現詞的演變;第二部是《曲選》,表現第二時期的曲子;第三部是《清詞選》,代表清朝一代才人借詞體表現的作品。
這部《詞選》專表現第一個大時期。這個時期,也可分作三個階段。
1 歌者的詞,
2 詩人的詞,
3 詞匠的詞。
蘇東坡以前,是教坊樂工與娼家妓女歌唱的詞;東坡到稼軒後村,是詩人的詞;白石以後,直到宋末元初,是詞匠的詞。
《花間集》五百首,全是為娼家歌者作的。這是無可疑的。不但花間集序明明如此說;即看其中許多科舉的鄙詞,如喜遷鶯,鶴沖天之類,便可明白。此風直到北宋盛時,還不曾衰歇。柳耆卿是長住在娼家,專替妓女樂工作詞的。晏小山的詞集自序也明明說他的詞是作了就交與幾個歌妓去唱的。這是詞史的第一段落。這個時代的詞有一個特徵︰就是這二百年的詞都是無題的︰內容都很簡單,不是相思,便是離別,不是綺語,便是醉歌,所以用不著標題;題底也許別有寄託,但題面仍不出男女的艷歌,所以也不用特別標出題目。南唐李後主與馮延巳出來之後,悲哀的境遇與深刻的感情自然抬高了詞的意境,加濃了詞的內容;但他們的詞仍是要給歌者去唱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始終不曾脫離平民文學的形式。北宋的詞人繼續這個風氣,所以晏氏父子與歐陽永叔的詞都還是無題的。他們在別種文藝作品上,儘管極力復古,但是他們做詞時,總不能不採用樂工娼女的語言聲口。
這時代的詞還有一個特徵︰就是大家都接近平民的文學,都採用樂工娼女的聲口,所以作者的個性都不充分表現,所以彼此的作品容易混亂。馮延巳的詞往往混作歐陽修的詞;歐陽修的詞也往往混作晏氏父子的詞。(周濟選詞,強作聰明,說馮延巳小人,決不能作某首某首蝶戀花!這是主觀的見解;其實「幾日行雲何處去」一類的詞可作忠君解也,也可作患得患失解。)
到了十一世紀的晚年,蘇東坡一班人以絕頂天才,採用這新起的詞體,來作他們的「新詩」。從此以後,詞便大變了。東坡作詞,並不希望拿給十五六歲的女郎在紅氍毹上裊裊婷婷地去歌唱。他只是用一種新的詩體來作他的「新體詩」,詞體到了他手裡,可以詠古,可以悼亡,可以談禪,可以說理,可以發議論。同時的王荊公也這樣做;蘇門的詞人黃山谷、秦少游、晁補之,也都這樣做,山谷、少游都還常常給妓人作小詞;不失第一時代的風格。稍後起的大詞人周美成也能作絕好的小詞。但風氣已開了,再關不住了;詞的用處推廣了,詞的內容變複雜了,詞人的個性也更顯出了。到了朱希真與辛稼軒,詞的應用的範圍,越推越廣大;詞人的個性的風格越發表現出來。無論什麼題目,無論何種內容,都可以入詞。悲壯、蒼涼、哀豔、閑逸、放浪、頹廢、譏彈、忠愛、遊戲、詼諧…這種種風格都呈現在各人的詞裡。
這一段落的詞是「詩人的詞」。這些作者都是有天才的詩人;他們不管能歌不能歌,也不管協律不協律;他們只是用詞體作新詩。這種「詩人的詞」,起於荊公、東坡,至稼軒而大成。
這個時代的詞也有他的特徵。第一,詞的題目不能少了,因為內容太複雜了。第二,詞人的個性出來了;東坡自是東坡,稼軒自是稼軒,希真自是希真,不能隨便混亂了。
但文學史上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文學的新方式都是出於民間的。久而久之,文人學士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採用這種新體裁來做他們的文藝作品。文人的參加自有他的好處;淺薄的內容變豐富了,幼稚的技術變高明了,平凡的意境變高超了。但文人把這種新體裁學到手之後,劣等的文人便來模倣;模倣的結果,往往學得了形式上的技術,而丟掉了創作的精神。天才墮落而為匠手,創作墮落而為機械。生氣剝喪完了,只剩下一點小技巧,一堆爛書袋,一套爛調子!於是這種文學方式的命運便完結了,文學的生命又須另向民間去尋新方向發展了。
四言詩如此,楚辭如此,樂府如此。詞的歷史也是如此。詞到了稼軒,可算是到了極盛的時期。姜白石是個音樂家,他要向音律上去做工夫。從此以後,詞便轉到音律的專門技術上。史梅溪、吳夢窗、張叔夏都是精於音律的人;他們都走到這條路上去。他們不惜犧牲詞的內容來遷就音律上的和諧。例如張叔夏《詞源》裡說他的父親作了一句「鎖窗深」,覺得不協律,遂改為「鎖窗幽」,還覺得不協律,後來改為「鎖窗明」,才協律了。「深」改為「幽」還不差多少;「幽」改為「明」,便是恰相反的意義了。究竟那窗子是「幽暗」呢,還是「明敞」呢?這上面,他們全不計較!他們只求音律上的諧婉,不管內容的矛盾!這種人不是詞人,不是詩人,只可叫做「詞匠」。
這個時代的詞叫做「詞匠」的詞!這個時代的詞也有幾種特徵。第一是重音律而不重內容。詞起於歌,而詞不必可歌,正如詩起於樂府而詩不必都是樂府,又正如戲劇起於歌舞而戲劇不必都是歌舞。這種單有音律而沒有意境與情感的詞,全沒有文學上的價值。第二,這時代的詞側重「詠物」,又多用古典。他們沒有情感,沒有意境,卻要作詞,所以只好作「詠物」的詞。這種詞等於文中的八股,詩中的試帖;這是一般詞匠的笨把戲,算不得文學。在這個時代。張叔夏以南宋功臣之後,身遭亡國之痛,還偶然有一兩首沉痛的詞(如高陽臺)。但「詞匠」的風氣已成,音律與古典壓死了天才與情感,詞的末運已不可挽救了。
這是我對於詞的歷史的見解,也就是我選詞的標準。我的去取也許有不能盡滿人意之處,也許有不能盡滿我自己意思之處。但我自信我對於詞的四百年歷史的見地是根本不錯的。
這部《詞選》裡的詞,大都是不用注解的。我加的注解大都是關於方言或文法的。關於分行及標點,我要負完全責任。《詞律》等書,我常用作參考,但我往往不依他們的句讀。有許多人的詞,例如東坡,是不能依《詞律》去點讀的。
顧頡剛先生為我校讀一遍,並替我加上一些注,我很感謝他的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