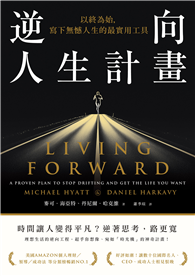法是什麼?為求正確理解法的本質,而不至錯誤,對於法的概念,不是應該下個定義嗎?
這個問題,是貫通法律學全部的根本的中心問題,可說是法律學的樞軸或根柢。何則?因為在所有學問上,如果它的研究對象,先弄不明白,那麼這學問的性質,乃至其研究方法,均不得而定了。
不幸得很,關於這最重要的基本問題,學說紛紛,迄無定論!自然法學、歷史法學、宗教法學、分析法學、實證法學、利益法學等諸學派,對於法的本質,各有其特別的見解,一直至於現代,所謂新康德派、新黑格爾派、社會法學派、純粹法學派、新自然法學派等,猶是種種意見對立,不知所止。即如法的本質,是“存在”(sein)抑是“當為”(sollen)的根本問題,還是在意見不一致的狀態之中。曾經屢屢被人引用的康德──“法律學者,現在?是在摸索法的概念底定義之中”的嘲笑,即在今日仍能適用。
因為這個原故,法律學者中,很有想將“法的概念”棄置不論者,據Bergbohm所述J.oudot和Lsid Muller兩人,都以劃定“法的概念”,徒生混雜,寧是以除去為妙,即在最近Fritz Sander還有:“法律學,老是對於法的概念,作無用摸索的事實,不可不趕速拋棄”之說哩!
但是,假使承認法律學是以法為研究對象的學問,那麼,拋棄“法的概念”,即不外否認法律學的存立,何則?研究對象如果弄不明白,任何學問,將都沒有成立的餘地。
這樣看來,明瞭法的本質,對於法的概念,提出的確的定義,在研究法律學者,實極必要。
二、問題的意義
要論研究法的本質,不能不先瞭解問題的意義。
這並不是說,研究特定時代特定社會的“法”的具體內容。法的具體內容,依時代而變遷;又因社會而不一其致,或時代以信仰異教為違法,懸為厲禁,或時代且把承認信教自由,定於法律,某社會的法律,承認一夫多妻制度,而別的社會的法律,一夫一妻之外,概不承認者,又復有之,“所謂法有如何具體內容”云云,僅是就某特定時代、某特定社會而言,就此而為研究,即是實證的法律學的任務所在。在這種意義下的法律學,唯限於某特定時代,或某特定社會,得以成立,超越時代和社會的法律學,是不能存在的。日本的憲法學和英吉利、美利堅的憲法學不同,又現代日本的憲法學,和德川時代、鎌倉時代的日本憲法學也不能不大異其趣。此外民法與刑法學也是相同的情形,自不待說。而所以紛紛如是者,要不外因為它係以法的具體內容,為研究對象的緣故。
至於論研究法的本質,那就和前面的不同,並非論究法的具體內容,和這個?沒有關係,亦不專注於某特定時代,或某特定社會——不問時之古今,洋之東西,亦不問文化程度之高低;貫串所有的時代,所有的社會,所有的文化,以明瞭法的性質,蒙昧野蠻底原始人的生活,和已達高度文化的現代人底生活,比較起來,法的內容,殆有不能相較底程度的差異。固是不難想像;但是不管這個,只要人類實行某種集團底生活,即社會生活,縱然是野蠻的原始人,也不能不和文明人一樣,應有某種形態的“法”。以故,法是貫串所有的社會生活,而為其存立底不可缺的要件。法的具體內容,固依時代或社會而不同,但法的性質,則不問怎樣的社會和時代,皆無二致。法的本質如何的問題,即是在求瞭解各種社會生活所共同的法的本質為何。
三、法的二種要素
要瞭解法的本質,得先將它的二種要素,區別明白。
其第一要素,係關於法的內容底要素,法的具體內容固是千差萬別,不一其揆,但是?然都具有法的性質,其內容上,也必不能不有某種共通的要素。它的共通要素是什麼?具備如何內容,纔獲有法的性質?它和道德風俗的區別,在什麼地方?這是為瞭解法的本質,第一要研究的問題。
其第二要素,係關於法的基礎的要素,即法何以得成為“法”?“法”所以成為法的根據何在的問題。
這和法的內容有別,法的內容係揭櫫法是怎麼定的?而法的基礎,則係進而究討其所包含的意義,和成立的淵源。關於法的本質,所以意見紛紛,主在於對於這個問題見解的不同,或謂法是主權者的命令,或謂法是一般意思的表現,或謂法是神所賦與的準則,或謂法是民族的“法的確信”,又有謂法是實力,法是正義等等,?說紛紛,要均是企圖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在這些學說中,那一個是正當的呢?抑或其中都沒有中鵠之論,應該別求根據呢?這是為瞭解法的本質,第二應研究的問題。
關於法的本質,這兩種要素,有分別討論的必要。如果這兩方面不明瞭,那法的本質,也就難得瞭解了。例如,法常被稱為人的行為規範,這種說法,縱是得當,亦不過說明法的內容而已,法的基礎,即法所以成為法的根據,毫無說明。而且人的行為規範,紛繁多端,有能成為法的規範者,亦有不能成為法的規範者。將近考試時間的學生,自己規定日課,實際上又能克意實行,這自然是行為的規範,但不得謂有法的性質。因為行為規範,而能具有法的性質者,更不能不備有得以成為法的根據,以故,這種說法,對於法的本質,仍未明瞭。法又屢屢被稱為主權者的命令,這種說法的當否,後再論及。但縱假定其為適當,亦不過說明法的成立根據而已,法的內容,曾無所示。縱令是主權者的命令,亦唯有具備某種內容,始能為法律,沒有不問內容,任何命令,都成為法,其內容?不限定,自不能說是已把握到法的本質。
這兩個要素,也不可混同,討論法的本質的人,常有說法是“當為”(sollen)者,那就是為了不認識兩者的區別,而生的錯誤。所謂法是“當為”之說,縱使假定其為正當,那也不過說法的內容是規定人類所當為(應做的事和不應做的事)的範圍之內為正當。即僅就法的內容而為說明而已,並非說法的本質,即是“當為”,為法律學研究對象的“法”,指某時代某社會現在所實行的“法”而言,而所謂現在所實行的法云云,即其法現實地存在之意,就是說,法的本體是社會的實在,法律學和立法政策學不同,不以應該作怎樣的“法”(de lege ferenda)作研究對象,其研究對象,寧是在“現在存在的法,是怎樣的法呢?”(de lege lata)之點,就E.Ehrlich的話說來,即以探求活著的“法”(das lebendige recht)為任務,而所謂活著的法,即不外其現實的存在的表明。法的基礎的問題,即不外於求瞭解,這作為“社會的實在”的“法”,基於什麼根據呢?又在怎樣形態之下而存在著?
以故,本書分為二章,第一章論法的內容,第二章論法的存立基礎。
第一章 法的內容
法,就其內容說來,可下以“在社會生活上,人類的意思及利益之強要的規律”的定義。
這更可分作四種的要素,而為觀察,即(1)法是社會生活的規律。(2)法是人類意思的規律。(3)法是人類利益的規律。(4)法是強要的規律。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法之本質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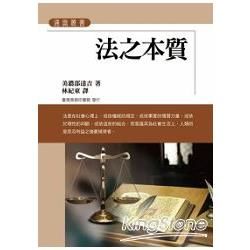 |
法之本質 作者:美濃部達吉 / 譯者:林紀東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1-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0 |
二手中文書 |
$ 158 |
法學理論/經典著作 |
$ 158 |
法學總論 |
$ 158 |
社會人文 |
$ 158 |
法律 |
$ 170 |
社會人文 |
$ 186 |
中文書 |
$ 186 |
法律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法之本質
★ 日本憲法學的奠基人之一、「日本憲法學的泰斗」、「學界第一人」──美濃部達吉重要著作!
法是在社會心理上,或依權威的規定,或依事實的慣習力量,或依於理性的判斷,或依這些的結合,而意識其為社會生活上,人類的意思及利益之強要規律者。
美濃部學說──
■ 「法的本質」是法律學的樞軸或根柢。
■ 法的兩種要素──法的內容的要素、法的基礎的要素。
■ 法是社會生活、人類意思、人類利益、強要性的規律。
■ 從實力說、主權說、歷史學派、承認說、自然法說等學說明瞭法的存立根據,並且就其全體而加以考察。
■ 法是一種「力」,係存在於社會心理之上的事實為前提。
■ 法是依著「法的權威」而定立的──國的立法行為與國法、行政及司法行為、自治立法及法律行為、自律的法與他律的法。
■ 法之歷史基礎及正義基礎。
作者簡介:
美濃部達吉(1873~1948)
日本憲法學的奠基人之一。其憲法學研究歷經明治、大正和昭和三個時期,被譽為「日本憲法學的泰斗」、「學界第一人」。
東京帝國大學畢業,1899年至歐洲留學,1902年回國後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
美濃部學說又稱「天皇機關說」,以德國法學家耶利內克(Georg Jellinek)的「國家法人說」為依據,主張天皇的權力應有所限制。
主要著作有:《憲法撮要》(1923)、《行政法撮要》(1924)、《逐條憲法精義》(1927)、《日本國憲法原論》(1946)等。
譯者簡介:
林紀東(1915~1990)
福建省福州市人。北平朝陽大學法學士,日本明治大學研究院研究。
歷任暨南大學、政治大學、臺灣大學、東吳大學等校教授;高等考試及特種考試典試委員、大法官等職。
章節試閱
法是什麼?為求正確理解法的本質,而不至錯誤,對於法的概念,不是應該下個定義嗎?
這個問題,是貫通法律學全部的根本的中心問題,可說是法律學的樞軸或根柢。何則?因為在所有學問上,如果它的研究對象,先弄不明白,那麼這學問的性質,乃至其研究方法,均不得而定了。
不幸得很,關於這最重要的基本問題,學說紛紛,迄無定論!自然法學、歷史法學、宗教法學、分析法學、實證法學、利益法學等諸學派,對於法的本質,各有其特別的見解,一直至於現代,所謂新康德派、新黑格爾派、社會法學派、純粹法學派、新自然法學派等,猶是種種意見...
這個問題,是貫通法律學全部的根本的中心問題,可說是法律學的樞軸或根柢。何則?因為在所有學問上,如果它的研究對象,先弄不明白,那麼這學問的性質,乃至其研究方法,均不得而定了。
不幸得很,關於這最重要的基本問題,學說紛紛,迄無定論!自然法學、歷史法學、宗教法學、分析法學、實證法學、利益法學等諸學派,對於法的本質,各有其特別的見解,一直至於現代,所謂新康德派、新黑格爾派、社會法學派、純粹法學派、新自然法學派等,猶是種種意見...
»看全部
目錄
譯者序
譯者例言
著者序
緒論
一、 問題之重要性
二、 問題的意義
三、 法的二種要素
第一章 法的內容
第一節 法是社會的規律 七
一、社會生活之二元的基礎 八
二、社會的單位 一一
三、團體法與社會法 一五
四、法與國家的關係 一七
第二節 法是人類意思 規律 二○
一、意思的規律的意義及其兩種態樣 二一
二、一般性是否?法的要素 二七
三、作?法的規律對象的意思 三一
第三節 法是人類利益的規律 三七
一、作?法的本質要素的利益 三八
二、法律上的利益?念利益和正...
譯者例言
著者序
緒論
一、 問題之重要性
二、 問題的意義
三、 法的二種要素
第一章 法的內容
第一節 法是社會的規律 七
一、社會生活之二元的基礎 八
二、社會的單位 一一
三、團體法與社會法 一五
四、法與國家的關係 一七
第二節 法是人類意思 規律 二○
一、意思的規律的意義及其兩種態樣 二一
二、一般性是否?法的要素 二七
三、作?法的規律對象的意思 三一
第三節 法是人類利益的規律 三七
一、作?法的本質要素的利益 三八
二、法律上的利益?念利益和正...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美濃部達吉 譯者: 林紀東
- 出版社: 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1-01 ISBN/ISSN:978957052671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92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