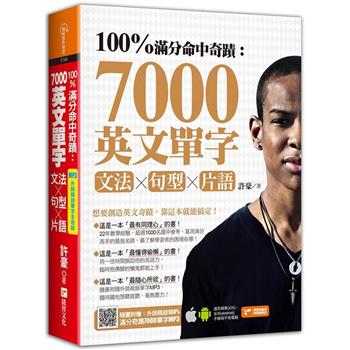「靜倚晴窗笑此生」一語,出自南宋禪僧淮海元肇的〈春日書懷〉一詩,其下句為「出遊歸隱兩無成」。元肇之詩以此二句為首,表達他在寺院歸隱與朝市優遊兩者間意欲兼顧而難作抉擇的無奈;倚窗之笑,是自嘲兩者兼顧而致兩事之皆無所成。儘管如此,這位以「肇淮海」之號知名於南宋叢林的文學僧之生涯,富有「出遊」與「歸隱」之情趣,蘊含出世與入世意識之激盪與整合,也塑造了「山林」與「朝市」相呼應而不相對立的詩禪世界。這個詩禪世界,展現於其詩集《淮海拏音》及其文集《淮海外集》中。本書作者檢視詩集中之三百五十餘首詩,及文集裡一百五十餘篇文,闡述元肇所扮演文學僧之角色,及他對南宋文學禪之成立所發生的作用。說明肇淮海之文學禪,上繼曇橘洲與簡敬叟,下開珍藏叟、觀物初與璨無文,不容佛教史家所輕忽。
本書是筆者研究南宋禪文化的成果之一,書中對南宋文學僧淮海元肇(或稱原肇)的詩文作了一番詳細的析論,說明元肇的詩文有助於南宋禪文化之走向文學禪。與筆者近著《無文印的迷思與解讀》及《文學僧藏叟善珍與南宋末世的禪文化》兩書一樣,本書也是為探討南宋個別禪僧詩文集而作,此類個別詩文集之存在,足以體現文學禪之形成與發展。合觀三書,可以對南宋若干禪僧「文字不離禪」之共識獲得更具體之印象。也可以對他們「隱心不隱跡」、「朝市亦山林」的認知有更深的理解。
作者簡介
黃啟江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歷史博士。曾任美國麻州Mt. Holyoke學院亞洲研究系助理教授、兼麻州Amherst 學院亞洲系客座助理教授,美國紐約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學院助理教授、副教授。現任紐約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學院亞洲語言文化系教授。曾獲蔣經國基金會北美教授研究獎(2004)、北美學者獎(2010),亞洲學會東北亞研究獎(2009)等等。
中文著作有《北宋佛教史論稿》、《一味禪與江湖詩─南宋文學僧與禪文化的蛻變》、《無文印的迷思與解讀─南宋僧無文道璨的文學禪》、《因果、淨土與往生─透視中國佛教史上的幾個面相》、《泗州大聖與松雪道人-宋元社會菁英的佛教信仰與佛教文化》等書。其他中英文論文多篇散見於國內外各大學術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