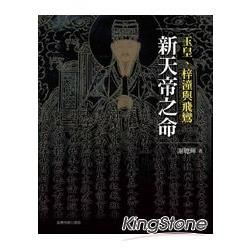導 論
一、研究義界與主題思想
《周易‧繫辭上》言:「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這是儒家經典在論述中國文化發展時,所特別強調的「通」與「變」的實踐功能;而「通」與「變」的意義內涵,在同篇〈繫辭上〉則以「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與「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來加以深入的闡述。以筆者的解讀,「通」的內涵是繼承傳統,即從優美沃壤的文明與先聖先賢的智慧中,找到可作為原理原則依循的活水泉源,使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成為新變的基礎與能量;「變」的內涵則是與時俱進,發展創新,在「使民不倦」、「使民宜之」等溥利厚生的宗旨下,使之神而化之,通久無窮。這既傳承又創新的通變思想,猶如「一陰一陽之謂道」,兩者兼容並蓄、缺一不可,循環變化而互為體用。而在文化發展新變的契機上,〈繫辭上〉直接點出是「窮」:此「窮」不僅可指各種文明形式與內容的窮限,更可包含個人與集體生命處在非常時空環境的窮困,甚至時代末嗣、天地崩壞的窮厄狀況認知,以及表現出陷入無法突破困境的憂慮,亦即生存窮迫與失去秩序的重要問題,因而能產生非變不可的強烈動力。
本書主標題「新天帝之命」,包含「新變」、「新天帝」與「新天命」三個核心觀念,即闡述《周易‧繫辭上》這種通變思想的文化結構,以及其傳承與創新的內涵。副標題「玉皇、梓潼與飛鸞」,則指陳其研究範圍涵蓋以下內容層次:一是「玉皇」作為神明信仰的意涵、流變、崇拜與祭祀活動;二是「梓潼」神格職能的衍變,以及作為新天帝之命落實於經典出世的關係意義;三是「飛鸞」的意涵與道教的轉化運用,以及主要飛鸞經典《玉皇本行集經》重要版本的研究。這三者中的玉皇作為新天帝、新天命的建構成立,可視之為「道」;而作為玉皇之道信仰落實於新出的經典功德,自是為「經」;另奉玉帝敕授,以如意飛鸞墨跡于天地之間,降筆出世經文以救末劫的梓潼帝君,也實質擔任了下教之「師」的天職。因此本書「道、經、師」三寶的新思想內涵,正具顯了道教在不同時代、信仰背景與文化潮流下,既吸收又轉化、既繼承又新變的活潑動力,以實踐其開劫度人的宗教性格。
(一)窮則變:新天帝之命的動力來源
《左傳‧成公十三年》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自古王者建國君民的政治神話敘述,皆以繼承「天命」來強調其政權、神權的正當合法性與神聖正統性。以商湯鼎革為例,其「新」意義即為革舊更新,重承天意與天命,重新命名新朝代,以建立新的存在秩序;完全符合儒家道德正義的新天命轉移與改朝換代的權力更替,所以古經典讚為奉天承運、應天順人的正當行動。而北宋是結束五代十國亂世的新朝代,開國之初內憂外患形勢猶未穩定,自認應運天命者多有所見,迫使趙宋皇朝必須採取措施以突破此「窮困」的情況,證明自己奉天承運「天命」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權威性。因此結合運用了五代末逐漸興起的「玉皇」作為「天帝」的思想,在帝王與道教的推波助瀾之下,逐漸取代「舊」的昊天而成為「新」的「玉皇大帝」與「昊天玉皇上帝」。此新的「神道設教」的建構與祭祀,期望產生如《周易‧觀卦‧彖辭》所說:「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敎而天下服矣」的政治效應與功能,「玉皇」信仰遂表現具有「新天帝」、「新天命」的神格。
從道教的發展史來看,南宋金元時期是繼踵魏晉南北朝的第二次「宗教大革命」時代。 各種新興的道派因應世變窮厄情境而創立,除繼承「開劫度人」的大傳統,一再強調為救劫而設外,在經典出世的模式與思想方面,也新創一種「飛鸞開化」的新類型;而且這種新創類型就集中在南宋初、中期,合乎「世變與文變」的內在互動邏輯。 且此一「飛鸞開化」道經出世類型所表現的特質,不具道派性質的侍鸞者佔絕大多數,這代表一種轉變,也代表一種新的趨勢。其不言其與道教史相關教派淵源關係,降鸞的主神不再是其他傳統方式所見的道派祖師,而代之以北宋新興而起且不斷接受朝封與道封的帝君級大神,如梓潼帝君即是代表性的神祇。
在此一窮厄世變如時代末的困境中,飛鸞出世的經典如《玉皇本行集經》,據筆者考證即在南宋寧宗嘉定十年(1217)與十一年(1218)之間,內先有天災地變的地震水旱災難,外有金兵侵略的「蜀罹敵難」危急窮迫情狀出世。依其相關經典的敘述邏輯,這就是負有「救末劫」使命的七曲梓潼帝君受命要託鸞降筆行世的時機;而其飛鸞大書的《玉皇本行集經》正具有救劫與安鎮的經德力量,以及勸誘世人積德行善以持經課誦感應的善書功能。然而為什麼會選擇七曲梓潼帝君作為飛鸞之主神?主要應與其地域性信仰逐漸擴充,以及其神格職能由戰亂時「禦患救災」,而後隨著道封、朝封列入祀典不斷增加與上昇有關;並至少在北宋末,梓潼帝君已兼有文昌神司祿桂籍、主管人間科第的職司,到了南宋以後則完全與文昌神結合為一,成為特別受到知識份子奉祀的全國知名神祇。
(二)通則久:新天帝之命的建構影響
宋朝玉皇崇拜與祭祀,乃透過各種方式來掌握對新天命的解釋權與祭祀權,以建構成為新的國家神話與道教宗教傳統;並對於當時與之後的朝廷禮制、祀典祭儀、道教壇場之制與神譜之位產生了重大的變化與影響。其至少具體表現於下列幾個方面:
(1)新的國家神話:新的道教玉皇神授天命神話,連接直通到宋朝的開國太祖與太宗,都是奉新的玉皇天命總治下方,以期強化儒家正統之外的新朝代新天命的更加神聖性。真宗朝更以「神道設教」的政治運作,利用「玉皇」與「天書」作為此一國家神話的核心,配合玉皇令聖祖授真宗天書以衹受天命與之後的「導迎奠安」,以及「東封西祀」、營建宮闕以宣傳天命之正統與建立禮制秩序,都是落實「新天命」思想的具體運作與唯一解釋權。而以「教主道君皇帝」自稱的宋徽宗,崇道奉道的各種作為將道教的地位推昇到歷史上最高,當然亦是此一天命思想的極致發揮。
(2)新的朝廷禮制:為了崇拜祭祀玉皇,必須營建相當規模的宮觀作為玉皇本宮,始能安奉玉皇與相關神祇,並舉行隆重的祭典禮儀。真宗、徽宗新建的玉清昭應宮與玉清和陽宮都屬於國家宗廟層級,相應的祭祀規模也為之新創調整,對宋代國家祀典產生重大影響。如恭謝禮、上玉皇聖號、寶冊與衮服的新創禮制,具體呈現與原先昊天上帝崇奉一樣的規模等級;而在圖畫聖像的繪造、公文書的用詞與祭典儀式的位序,也表現了禮容禮器下所蘊含的神譜階位秩序;另在聖像的鑄造、迎送、蒞京、法服裝飾與安奉過程中所表現出禮制威儀,也處處具顯玉皇作為新天命至尊神的崇敬措施。
(3)新的聖號徽稱:北宋真宗於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一日,親詣玉清昭應宮,率天下臣庶奉表奏告,恭上玉皇大帝聖號為:「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尊」;以及宋徽宗進一步於政和六年(1116)九月一日御製冊文,躬上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此後,「玉皇大帝」、「玉皇上帝」與「昊天玉皇上帝」等北宋新創詞彙,遂成為官方與道教、民俗各階層,正式、特定與穩定的且專指「萬神之神」的玉皇上帝尊稱徽號,並深刻影響至今。
(4)新的神譜位序:北宋朝廷以新出玉皇建構作為至尊神後,就必須面臨道教內部神譜原先三清尊神與玉皇階位的排列衝突與調整。其中隨著徽宗玉清和陽宮的建築完成,道教的三清四御神譜位序也逐漸完成定制,並在象徵皇權落實的國家最高禮制中,道教尊神的位階也超越了儒家傳統昊天的地位。而經過此官方與道教龍象建議協調後的階級位序,所建構而成的新國家神話與道教宗教傳統,也對道教神譜三清四御的建立與民間信仰產生了遵循依據。
(5)新的經典詮釋:因受「世變與文變」而新出的經典,如《玉皇本行集經》即落實了新思潮的詮釋:即有意改變《五老赤書真文經》的經文,卷中新增玉皇將神咒真誥祕篆授予元始五老,而成為此一靈寶首經傳經者的重要角色,以提昇玉皇的神格;更進一步利用宋徽宗已結合「昊天玉皇大帝」的神格,卷下敘述昊天上帝聽聞經法後,長跪帝前,請玉帝為持經人解說經法功德,以明昊天上帝之位階又出於玉帝之下的臣屬關係。而且自南宋中晚期開始後,由於《玉皇本行集經》不斷地鋟梓刻版與流傳,經中所記玉皇的本行故事與生日,已廣泛地流行於民間,「正月初九日」遂定型為官民特別重視與神聖的祭祀日子。
二、前人相關研究析論
(一)玉皇與梓潼信仰研究
目前學者對玉皇的神格、位階意涵與相關崇拜祭祀實踐上,曾有部分的討論。 但在不同經系經典,以及不同時代的文獻記載中,其相同或相關名稱所代表的實質內涵認知關係,則仍有許多未釐清與值得深入考證之處;也缺少較全面性的從「禮制」、「祭祀」、「神譜」與「經典」的角度,深入析論其背後重要的原因與動力。而在梓潼文昌帝君信仰與相關經典的研究上,則較受到關注而多元豐富,其與本題相關者:如森田憲司討論了文昌帝君從地方神到全國科舉神的歷程; 祁泰履(Terry F.Kleeman)探究了其從地方雷神發展到全國文昌信仰的演變脈絡與相關信仰儀式,以及《文昌化書》七十三化的形成和後世的文昌帝君信仰; 王興平考察了劉安勝道壇與相關文昌經典的出世關係; 胡其德則以「擴散與重組」的理論,分析文昌信仰研究的新觀點,並重新檢討文昌帝君信仰的流變。 以上諸論都在不同層面作出了貢獻,但對南宋時期作為飛鸞開化大神的梓潼帝君職能,和《玉皇本行集經》出世的關係,以及《文昌化書》七十三化以後每化出世的時間、地點與內容的深入考證,則仍甚少研究涉及。
(二)經典出世方式研究
在道教經典的本質研究上:指出其出自天界神聖又神秘的傳授與翻譯, 和末世劫難的出世因緣, 乃表現天地崩壞、宇宙末劫的「世變」集體憂慮,與對神聖權威建立與解釋的認知下, 具顯其所擁有不可思議的「開劫度人」經德功能 的相關研究上成績斐然;但對於傳統各道派道經出世的類型與特質,仍須有較完整的梳理,以比較舊的傳統與新的創化二者間的差異。至於目前所見扶箕與飛鸞的專門研究: 如許地山探究扶箕的起源與文化,森由利亞證實了清時蔣予蒲等現任菁英官員在呂祖信仰中所擔任的重要角色,以及全真道傳戒與呂祖扶乩的關係,焦大衛 (David K. Jordan)與歐大年 (Daniel L. Overmyer)關心元代以後民間教派扶鸞活動。其他明清以後區域性的重要研究:如王見川、志賀市子、范純武、康豹(Paul R. Katz)與游子安等等,也都有傑出的成果提出。但以上相關論文較少從道教的角度切入,深入論述「飛鸞開化」的意涵與轉化,也未分析比較扶箕與飛鸞的不同差異;而且對於作為飛鸞重要源頭的南宋時期新道經「飛鸞開化」出世類型與特質,也缺乏深入的論述。
(三)《玉皇本行集經》研究
在《玉皇本行集經》的研究上,目前學界除藉此討論玉皇神格的發展外,有多篇論文也論及此一經典成書時間的推測。歸納所見其成書時間推定,大分為四種:一是隋末唐初:此以丁培仁為代表,他援引了《全唐文》卷一六二唐貞觀時人陳宗裕所作的〈敕建烏石觀碑記〉,引證初唐道士張開先曾「唪誦皇經」,所以斷定其成書於貞觀三年(629)以前。 二是唐代:李養正在〈《玉皇經》與《心印妙經》〉一文中,指出張良本是現今最早的版本,並以經中宣稱「帝即道身也」,與未見宋代為玉皇所上的尊號,而仍只稱「道君」、「天尊」,斷定《玉皇經》可能出之於唐代玄宗時期。 三是北宋:《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第九卷〈皇天上帝部‧彙考一〉於「天禧元年上玉皇大帝寶冊袞服」條目下, 編集者特別加了按語:「按祀典之稱玉皇始此,而本末未詳。今錄近世所奉《玉皇本行集經》於後,恐是經或始於此時也。」說明此經可能出於北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左右。朱越利則以為此經有元、明之注本,而且玉皇大帝於宋代升為主神,所以本經當出於宋代。 四是北宋後:任繼愈認為宋徽宗封玉皇爲昊天上帝,經文始稱昊天上帝,故校正本當作於北宋後。 以上諸說因未能廣泛蒐集其他版本,提出令人折服的確實的證據,所以大多流於臆測;而且對《玉皇本行集經》如何出世?出世的背景為何?相關重要版本探討,以及與梓潼帝君的關係等等重要問題,也皆未能深入研究。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新天帝之命:玉皇、梓潼與飛鸞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77 |
宗教類 |
$ 277 |
神佛 |
$ 298 |
社會人文 |
$ 326 |
中文書 |
$ 326 |
道教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新天帝之命:玉皇、梓潼與飛鸞
本書主標題「新天帝之命」,包含「新變」、「新天帝」與「新天命」三個核心觀念,即闡述《周易‧繫辭上》通變思想的文化結構,以及其傳承與創新的實質內涵。副標題「玉皇、梓潼與飛鸞」,則指陳論文內容涵蓋三個層次:一是「玉皇」作為神明信仰的意涵、流變、崇拜與祭祀活動;二是「梓潼」神格職能的衍變,以及作為新天帝之命落實於經典出世的關係意義;三是「飛鸞」的意涵與道教的轉化運用,以及主要飛鸞經典《玉皇本行集經》重要版本的研究。這三者中的玉皇作為新天帝、新天命的建構成立,可視之為「道」;而作為玉皇之道信仰落實於新出的經典功德,自是為「經」;另奉玉帝敕授,以如意飛鸞墨跡于天地之間,降筆出世經文以救末劫的梓潼帝君,也實質擔任了下教之「師」的天職。
【本書特色】
本書「道、經、師」三寶的新思想內涵,正具顯了道教在不同時代、信仰背景與文化潮流下,既吸收又轉化、既繼承又新變的活潑動力,以實踐其開劫度人的宗教性格。
作者簡介:
謝聰輝
1963年出生於臺灣臺南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任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專任教授。研究專長為道教經典、道壇道法、道教文學與臺灣文化信仰,曾獲得2010與2011學年度「國科會特殊優秀人才獎助」肯定,持續開設「道教文化專題研究」與「神仙傳記專題研究」課程。已出版主要著作:《臺灣齋醮》(與李豐楙教授合著,國立傳統藝術籌備處,2001,初版)、《臺灣民間信仰儀式》(與吳永猛教授合著,國立空中大學,2011,再版),及相關論文數十篇。
章節試閱
導 論
一、研究義界與主題思想
《周易‧繫辭上》言:「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這是儒家經典在論述中國文化發展時,所特別強調的「通」與「變」的實踐功能;而「通」與「變」的意義內涵,在同篇〈繫辭上〉則以「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與「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來加以深入的闡述。以筆者的解讀,「通」的內涵是繼承傳統,即從優美沃壤的文明與先聖先賢的智慧中,找到可作為原理原則依循的活水泉源,使之...
一、研究義界與主題思想
《周易‧繫辭上》言:「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這是儒家經典在論述中國文化發展時,所特別強調的「通」與「變」的實踐功能;而「通」與「變」的意義內涵,在同篇〈繫辭上〉則以「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與「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來加以深入的闡述。以筆者的解讀,「通」的內涵是繼承傳統,即從優美沃壤的文明與先聖先賢的智慧中,找到可作為原理原則依循的活水泉源,使之...
»看全部
目錄
序一
序二
導論
第一章 北宋前「玉皇」概念之相關構詞意涵
一、 前言
二、 玉皇可指三清尊神
三、 高上玉皇相關神格意涵
四、 玉皇作為其他仙界高真或唐皇帝代稱
五、 結語
第二章 北宋玉皇崇拜與祭祀析論
一、 前言
二、 玉皇之命:新出天命的繼承與宣傳
三、 玉皇之祀:宮觀聖像的建鑄與迎奉
四、 玉皇之位:禮制神譜的建構與定序
五、 結語
第三章 南宋中期以前傳統道經出世的類型與特質
一、 前言
二、 接遇降傳類型
三、 石室示現類型
四、 真手傳譯類型
五、 其他類型
六、 結語
第四章 南宋道經...
序二
導論
第一章 北宋前「玉皇」概念之相關構詞意涵
一、 前言
二、 玉皇可指三清尊神
三、 高上玉皇相關神格意涵
四、 玉皇作為其他仙界高真或唐皇帝代稱
五、 結語
第二章 北宋玉皇崇拜與祭祀析論
一、 前言
二、 玉皇之命:新出天命的繼承與宣傳
三、 玉皇之祀:宮觀聖像的建鑄與迎奉
四、 玉皇之位:禮制神譜的建構與定序
五、 結語
第三章 南宋中期以前傳統道經出世的類型與特質
一、 前言
二、 接遇降傳類型
三、 石室示現類型
四、 真手傳譯類型
五、 其他類型
六、 結語
第四章 南宋道經...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謝聰輝
- 出版社: 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9-01 ISBN/ISSN:978957052859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道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