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從不真正睡覺,因為每兩小時她就得餵兒子吃奶。
她一分鐘也不敢離開他,所以兩天才洗一次澡。
她的頭髮像一團亂草垂在腦後,眼睛滿布陰霾。
她想,或許她只是需要一點獨處的時間。或許她只是需要走開而已。
等她準備好要當兒子的母親時,她就會回來。
裴琪五歲時,母親就離家失去音訊,但她對於母親的記憶以及思念卻從未減少,也希冀總有一天母親會回家,訴說不得不狠心拋下他們父女的原因。擁有繪畫天分的她夢想進入設計學院就讀,但因為一段羞為人知的過去,她選擇放棄升學的機會,重蹈母親的腳步,拋棄相依為命十多年的父親,割捨與過往有關的所有連繫,踏上前往波士頓的旅程。
她在波士頓遇到來自富裕上流家庭的醫學院學生尼可拉斯,兩人不顧男方父母斷絕金援的威脅堅持共結連理,婚後的裴琪埋藏繪畫天分忙於工作養家,尼可拉斯則專注於成為頂尖的心臟外科醫師。但隨著尼可拉斯的事業日漸攀向高峰,兩人的分歧也越來越大,裴琪始終覺得自己與丈夫的世界格格不入,懷孕生子並沒有將兩人的裂縫修補,反而將裴琪推入崩潰的境地。
從知道懷孕以來,裴琪就終日惶惶不安,她不知道要怎麼照顧小孩,害怕自己無法勝任母親的角色,從來就沒有人教她如何當個母親。孩子呱呱墜地後,裴琪的焦慮有增無減,她必須獨自面對鎮日哭鬧的嬰兒,她不知道為什麼明明已經餵過奶、換過尿布、所有生理徵兆都一切正常,但是兒子還是不斷哭鬧不睡覺。
裴琪開始相信自己真的是個不合格的母親,她找不到自己生存的價值以及人生的目標,她直覺自己必須離家透透氣,哪怕只有一晚都好。她衝動地步上母親的後塵不告而別,而回家的路途卻比她想像的還要艱辛困難。
【媒體讚譽】
「在這本令人屏息、讀來驚心的小說中,茱迪.皮考特將相守伴侶之間牽繫的脆弱細線攤露出來,甚或任它們斷裂四散。她的敘述,尤其她的家庭觀,讓我想起年輕的安.泰勒。本書是一個新的聲音,為我們道出一則動人心弦的故事。」──瑪莉.莫里斯,《紐約時報》書評
「茱迪.皮考特以她第二部層次豐富的小說,探索了身為人母的矛盾情結與脆弱地帶。」──《紐約時報》書評
「皮考特對維繫或分裂家庭的種種力量賦予深思,她以譬喻也用直描的方式檢視了人心的複雜。」── 《圖書館期刊》
「這是一位年輕女子尋找自我的現代故事,皮考特將她的驚人才華帶進這個故事裡……這也是一個寫實故事,作者以回憶片段的形式,述說了童年和青少年的心境、為人母親的辛勞、個人成長的艱難路程,更告訴我們愛情需要多麼慷慨的精神付出。作者絕妙的想像力令人嘆為觀止;透過這齣動人的戲劇,她筆下人物的舉手投足是如此真實可信。」──《出版人週刊》
「皮考特利用幾個令人頗有共鳴的角色人物,穿針引線編織成一個美麗的故事,她的敘述從兩個不同觀點出發,而過程充滿懸疑,戲劇性十足。」──《夏洛特觀察家報》
「對母愛的檢視別出心裁、令人動容,充滿細節與感情。」──《李奇蒙時遞報》
「皮考特描寫家庭以及物換時移的家人關係,下筆層次豐富又精確……《最初的心跳》是一幅動人心弦的畫,描繪出婚姻和為人父母的難處。」──《奧蘭多守望報》
「皮考特書寫年紀輕輕就身為人母的心境至為拿手。」──《紐約每日新聞報》
「極度吸睛……細節豐富,深具個人風格。」──《魅力》
「《最初的心跳》令人聯想到蘇.米勒的《好母親》,但它有自己完全不一樣的聲音。」 ──《芝加哥論壇報》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最初的心跳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最初的心跳 作者:茱迪.皮考特 / 譯者:席玉蘋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12-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284 |
美國現代文學 |
$ 306 |
小說/文學 |
$ 324 |
小說 |
$ 335 |
英美文學 |
$ 335 |
英美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最初的心跳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
1967年生於紐約長島。普林斯頓大學創意寫作學士,哈佛教育碩士。
她的作品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並在四十餘個國家發行銷售,繁體中文版有:《姊姊的守護者》、《事發的19分鐘》、《第十層地獄》、《換心》、《死亡約定》、《小心輕放》、《當愛遠行》、《完全真相》、《失去的幸福時光》、《家規》、《魔鬼遊戲》、《凡妮莎的妻子》、《留住信念》、《消逝之行》、《孤狼》、《大翅鯨之歌》、《最初的心跳》(依臺灣商務出版時序)。皮考特眾多著作中的《第十層地獄》、《死亡約定》、《完全真相》、《Salem Falls》已被改編成電視電影集,暢銷著作《姊姊的守護者》並翻拍成電影於全球上映。
其在2003年獲得美國新英格蘭最佳小說獎,並榮登《紐約時報》暢銷作家之列,多部作品皆一出版便盤據《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數週之久,2012年與女兒Samantha van Leer合著青少年小說《Between the Lines》, 2013年新作為《The Storyteller》。
目前皮考特和丈夫及三個子女住在新罕布夏州。
個人網站:www.jodipicoult.com
譯者簡介
席玉蘋
政治大學國貿系畢業,美國德州理工大學企管碩士。曾四度獲得文建會梁實秋文學獎之譯詩、譯文獎,現居高雄,專事譯作、寫作。譯有《愛因斯坦檔案》、《追鬼人》、《匠心獨具》(以上皆由臺灣商務出版)等書。
圖書評論 - 評分: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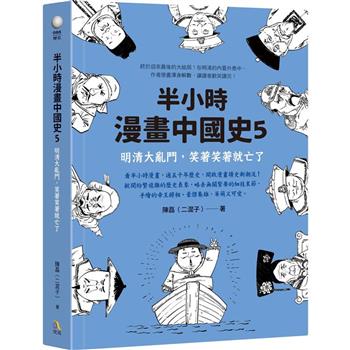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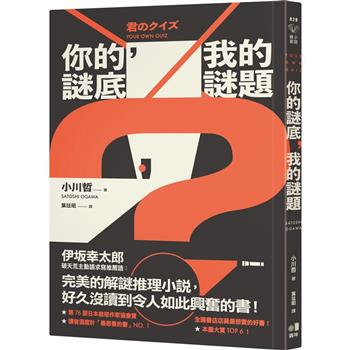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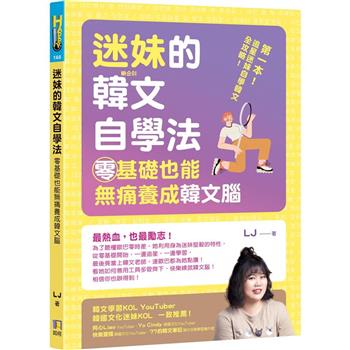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