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英國大兵幫她把幾箱番茄醬搬到樓上。到三樓的時候,樓梯間的燈一如往常地熄掉了,他們繼續摸黑往上。然後,發生了一件事:蓮娜.布綠克,這位曾經在這樓梯上下千百次的女人,即使閉著眼睛也能毫不遲疑地往上爬的女人,對每個腳步甚至每一階的不平處都摸得一清二楚的女人,竟然在樓梯上跌跤。她跌了一跤,因為她在想那咖哩粉,那罐她放在那箱番茄醬上一起往上搬的咖哩粉,不過她其實更想著布列門,回想著他們兩年多以前是如何一起走上這個階梯的,回想著他們如何在那公寓裡共度了二十七天,那和諧美滿的二十七天,直到那次的爭吵,直到他的手在門把上撞到流血,直到她看到那些可怕的照片,直到他穿著她先生的西裝離開,就這麼消失,就跟其他男人一樣。每當她想到,當過了那四個星期後,他走在一個對他來說已經是另一個世界的街上,他會怎麼看待她,她的腦袋裡就會充滿羞愧。她一直希望,有一天他會突然出現,那麼她就可以向他解釋這一切。但她再也沒有任何關於他的音訊,而這時她就這麼跌倒在那黑漆漆的樓梯上。啪。破了三瓶番茄醬。她打開頂樓的電燈,開了房門。一團紅色的爛攤子。在那團爛攤子裡還摻著她為了在車上嚐一口味道而打開的咖哩粉。然後她就這麼坐在樓梯上,開始嚎啕大哭了起來。她也無法向那試著安慰她的英國大兵解釋說,她心疼的並不是那三瓶打破的番茄醬,不是那打翻的咖哩粉,不是她不喜歡那味道,也不是因為她做了這輩子最差勁的一次交易,更不是因為她想到了就這麼離開的布列門,也不是因為想到了被她踢出去的丈夫,甚至不是因為她斑白的頭髮就即將要變得全白了,或是因為過去幾年的日子就這樣和她擦身而過,沒留下任何痕跡—唯一的例外,自然地,就是和布列門相處的那幾天了。那位英國大兵給了她一根菸。電燈再度暗去,他們肩併肩地坐在階梯上,坐在黑暗中抽著菸,一句話也沒說。
然後,她抽完了菸,那已經是那天的第二根菸了。她把菸放在樓梯的鐵條上捻熄,走上最後的幾格階梯,開了燈。英國大兵把剩下的東西提了上樓,揮了揮手,他說:「Good luck. Bye bye.」然後就走下樓了。她一直按著開關,好讓燈一直亮著,直到她聽到樓下的大門關上為止。
她把箱子裡沒摔破的番茄醬和那破掉的三瓶舉高,然後拿到廚房裡。幸運的是瓶子並沒有被摔得支離破碎,所以她還是可以把沾在上面的紅棕色混合物倒掉就好。她把番茄醬裡面的碎玻璃片給挑了出來。但是那番茄醬已經被毀了,咖哩粉混進去了。她把垃圾筒搬過來,正要把這團東西丟進去的時候,她心不在焉地舔了一下沾到醬的手指—又舔了一下,突然清醒了,然後再舔—她嚐到那味道,那味道讓她笑了出來。那味道是辛辣的,但又不只是辛辣,而是帶有點水果味的濕辣。她笑那意外跌倒的一跤,這個美麗的巧合。她笑那件美麗的灰鼠毛皮大衣,如今一定是穿在那位後勤官漂亮,又有頭紅金相間頭髮的太太身上。她很高興她曾經把那個男人留在她家久一點。想到她是如何把丈夫攆出家門,還把門大聲關上的事,她更是放聲大笑。
她把煎鍋放到瓦斯爐上,把地上掃起來的咖哩粉和番茄醬放進去。
然後,慢慢地,廚房裡開始充滿著一股芳香—《天方夜譚》裡的那種芳香。她沾了一些溫熱的、紅棕色濃稠的醬,嚐了一口,那味道不錯,沒錯,但那味道到底像什麼?她的舌尖感到一股麻刺,她的上顎好像在變大,對,那感覺實在很難用苦或甜這樣的詞來形容,卻又不是辛辣。不,上顎的感覺就好像要彎了似的,上顎和舌頭的感覺都很強烈,令人驚喜,令人專注於自己、專注於那口味。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伊斯坦堡的玫瑰,天堂樂園!
她花了整晚做實驗,把地板上的那團東西拿一些起來,加一點辣薄荷和一點野生墨角蘭,兩種嚐起來都沒那麼好。又用一些香草試試看,還不錯。加一些霍卿格當時給她的黑胡椒,一些剩下來的豆蔻,那是她當時特別為了替布列門做馬鈴薯泥而弄來的,還有些大茴香籽。她嚐了嚐那紅棕色的醬泥:完美的平衡!言語無法形容。既然她早餐到現在什麼都沒吃,她就把一塊沒有皮的小牛肉香腸切片丟進鍋裡,用那咖哩醬泥來煎它。現在,原來吃起來乾澀無味的香腸,竟帶著果香的濕氣,有種遙遠而難以形容的滋味。她坐了下來,盡情地享用第一盤咖哩香腸。之後她把那食譜給寫在一張從舊雜誌上撕下來的紙,記載了罐子上所標示的成份,還有她自己所添加的調味料:番茄醬、香草、豆蔻、大茴香籽、黑胡椒,還有原本用來熱敷小腿的新鮮芥菜籽。
第二天早上,一個濕冷的十二月天,灰暗到不能再灰暗的天氣裡,布綠克新開小吃攤的第一批顧客上門了:一開始是那些布拉姆斯街上,廉價妓院的妓女們,眼睛深陷著、精疲力盡、沒有希望。她們所面對的是比一無所有還要困乏的一無所有。她們的嘴裡完全沒有任何味道;現在她們想吃點什麼熱的,即使奇貴無比,一杯純正的咖啡或是一條燻臘腸或是一條煎香腸,有什麼吃什麼。但是今天既沒有燻臘腸也沒有煎香腸,今天只有皺皺的香腸。看起來笑死人了。那香腸還被切成一塊一塊的,上面還沾了一層濕潤、可怕的紅醬,或者說,一團紅棕色的醬糊。「噁心!」莫妮說,但是她吃了一口之後,那味道竟然讓她的知覺醒了過來。「棒呆了!」莫妮說。灰濛濛的天空突然變得亮了。早晨的冰冷也變得可以忍受了。她身體覺得很暖,凝重的沉默變成了大聲的交談,「對啊,」麗莎說,「這東西就好像會唱歌一樣。它真的是這樣!」在漢堡做了三個月了的麗莎說,「這就是人們需要吃的東西,真的超讚!」
於是咖哩香腸開始席捲各地,從新市廣場,到雷波街上的一個小攤,然後到聖葛奧爾教堂,然後因為麗莎的關係,咖哩香腸跟著傳到了柏林。麗莎在柏林的康德街上開了家小攤。後來也傳到了基爾、到科隆、到明斯特,還有法蘭克福,但很奇怪地就一直擴散到美茵河畔為止,再過去就是白香腸的勢力範圍了。不過,咖哩香腸倒是在芬蘭、丹麥,甚至挪威傳播開來。南歐的國家,則顯然極力抗拒著那食物。「也許這食物不可缺的一個自然條件,」布綠克太太說得有理,「是那吹過樹叢和草叢的西風。正因為那風的源頭,讓北方空氣總是灰濛濛的—而與灰色在氣味上相對的顏色,就是紅棕色。」社會的上層階級也抗拒這食物;沒有哪個喝沛綠雅氣泡礦泉水、逛精品服裝店的傢伙會想吃咖哩香腸,因為那得要站著吃,站在陽光或驟雨下,旁邊還站個靠年金過活的老人、有毒癮的女孩,或是個渾身尿騷味的流浪漢,跟你訴說他像李爾王一般的流落故事。你就和他們一起站著,舌尖嚐著咖哩的味道,聆聽著一段難以置信的故事,關於那個咖哩香腸誕生的時代的故事:廢墟與重建,甜蜜而辛辣的無政府時期。
一天,布列門也出現在攤子上。他從布朗茲維克市來到漢堡,走到布魯德街上,往上望著窗戶,跟自己說,如果他現在仍坐在那樓上的房子裡,而不必像現在這樣當個賣玻璃窗和接著劑的業務,整天四處奔走,那該有多好。他想過,要不要走上去按那門鈴。但他還是繼續走了下去,穿過那些即便他住了四個星期,卻一點也不熟悉的街巷。他來到新市廣場,看到那小吃攤,想要吃點什麼,然後他看見了她。他一開始並沒認出她來。她穿著件白色的工作服,頭髮高高地盤起。她的攤子旁圍滿了黑市販子。為了防雨,那攤子上鋪著一大塊迷彩的軍用防水布—那是一個單位發給他的布,一九四五年四月,好用來睡在林布堡荒原上,以及用來欺騙開過來的坦克。那也是他和她一起撐過的布,他們在雨中撐著它走過。
「一份切塊的香腸,謝謝。」
她立刻認出布列門來了。她轉過身去深深吸口氣,好克制住她切香腸時顫抖的雙手。他又瘦回去了,而且他正穿著她先生的西裝。那是最耐穿的西裝,用最好的英格蘭布料做的。他戴了頂帽子,一頂真正的義大利波沙麗諾帽,那是他換來的帽子。生意不錯。那時接著劑的需求量很大,因為有太多玻璃破掉等著要補。他一點都沒變,只有那帽子微微地遮住了他的眼睛。「來點咖啡嗎?」她對著他問。「純正的咖啡?」他看起來像極了成功的黑市販子。「都好。」他說,猜想她一定已經認出他的聲音了。「所以你要純正咖啡,還是橡樹籽咖啡?」她問。「一杯真品咖啡要兩根菸,或者三十馬克。」他仍然無法嚐出任何味道,所以事實上他不管喝真品還是喝橡樹籽咖啡,對他都沒差。儘管如此他還是說:「真品咖啡。」「再加上咖哩香腸的話,」她說,「總共是五根香菸。」索價驚人,不過他還是點了頭。她把她調的咖哩醬放進鍋裡,那有一種異國的香味,然後加進番茄醬,最後再把烤過的香腸切塊放進去。她把香腸切塊放在一個錫盤裡,推到他面前。他用竹籤插起一塊香腸,沾了沾那深紅色的醬。然後,突然之間,他嚐得出味道了:天堂花園在他的舌頭上展開。他一邊吃,一邊看她招待客人,親切又俐落,看她和客人聊天的樣子、說笑話的樣子、笑的樣子。她輕輕對他一瞥,短暫地,不帶半點驚喜或錯愕地,她看到了一張親切的臉孔。不,是一張容光煥發的臉—彷彿他剛剛才得到一樣重大的發現,他認出她來了。她猶豫了好一刻,正想跟他打招呼,不過這時來了另一位客人,點了一杯橡樹籽咖啡。她的手不再顫抖了。他細心地用麵包把盤子上的醬給抹乾淨,然後把錫盤還了回去。他走了一小段路,回頭再看一眼那攤子。她舉起上臂掠過額頭,把一撮跑到她額前的頭髮撥開。那是一束灰色的頭髮,在她一頭金髮裡幾乎看不出來。甚至因為這灰髮而使得那金色看起來更亮些。她取出杓子,將那紅色的醬倒在香腸丁上。他看著這個在我記憶中,她日復一日地重複的動作。那是個優雅的、明快的動作,輕柔而不費力。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咖哩香腸之誕生(二版)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咖哩香腸之誕生(二版) 出版日期:2014-05-01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5 |
Others |
二手書 |
$ 140 |
Others |
二手書 |
$ 153 |
二手中文書 |
二手書 |
$ 192 |
Others |
$ 205 |
文學作品 |
$ 205 |
文學 |
$ 221 |
小說/文學 |
$ 241 |
中文書 |
$ 242 |
德國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咖哩香腸之誕生(二版)
名人推薦
伊格言(小說家)
張國立(知名作家)
焦 桐(飲食文化專家)
楊佳嫻(詩人)
齊聲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列)
內容說明
愛情很美,因為兩個人在一起所以很美。
但也正是因為如此,要兩個人分開才如此困難。
大多數人只有在找到另一個可以和他廝守的人時,
才真的下得了決心離開。
戰火熾熱時,他們流轉的愛情,為生存誕下了希望,但止息的烽火,將人性、現實及孤獨帶進了他們的生命。
作者簡介:
作者 烏韋•提姆(Uwe Timm)
1940年生於德國漢堡,曾先後於慕尼黑和巴黎研習哲學及德國文學,為當代著名作家。長期在各國遊歷創作,足迹遍布南美、北美、北非,現定居慕尼黑。他的兒童文學名著《跑豬嚕嚕》(曾改編為電影)和《火車老鼠》以及《虎嘯鳥》等深受各國青少年讀者和成年讀者的喜愛,被譯成二十餘種文字在世界流傳。曾榮獲德國青少年文學獎、義大利文學獎等多種重要獎項。
譯者簡介:
劉 燈
中央大學英文所碩士。著有《背著電腦,去歐洲流浪》,譯有《20歲的環遊世界》(臺灣商務印書館)等書。
章節試閱
那位英國大兵幫她把幾箱番茄醬搬到樓上。到三樓的時候,樓梯間的燈一如往常地熄掉了,他們繼續摸黑往上。然後,發生了一件事:蓮娜.布綠克,這位曾經在這樓梯上下千百次的女人,即使閉著眼睛也能毫不遲疑地往上爬的女人,對每個腳步甚至每一階的不平處都摸得一清二楚的女人,竟然在樓梯上跌跤。她跌了一跤,因為她在想那咖哩粉,那罐她放在那箱番茄醬上一起往上搬的咖哩粉,不過她其實更想著布列門,回想著他們兩年多以前是如何一起走上這個階梯的,回想著他們如何在那公寓裡共度了二十七天,那和諧美滿的二十七天,直到那次的爭吵,直到...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烏韋‧提姆 譯者: 劉燈
- 出版社: 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5-01 ISBN/ISSN:978957052919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8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德國文學
圖書評論 - 評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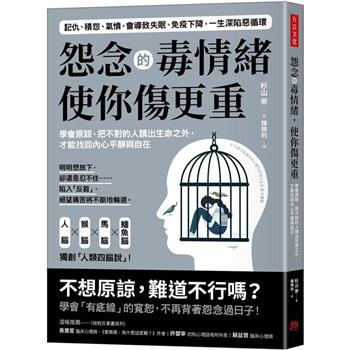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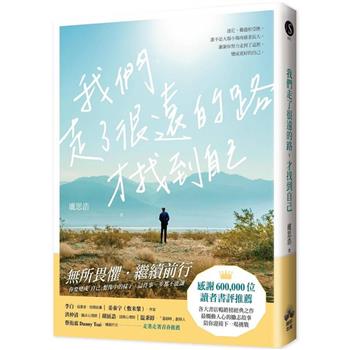








如果你是一位單純讀者,閱讀這本德國小說「咖哩香腸之誕生」是幸福的也是不幸的,幸福的是,若不是這本書,閱讀人很難去體會用簡單的故事去蘊釀出久久不能自己的多重且複雜的喜怒哀樂,不幸的是,能具有這般故事魔力的書真的很少很少。如果你像我是位文字或創意工作者,閱讀本書之後,你或許會和我一樣產生一股想要「封筆」的衝動,想想看,自己的東西怎麼跟這本書比呢! 故事的線條是這樣:二戰期間,四十歲的蓮娜˙布綠克的丈夫被徵召離家,她從街上帶回一個可以當他兒子的年輕逃兵,藏在她家中那張宛如孤島的床墊上,飄流出一段27天的短暫忘年之戀。二十七天後德國戰敗投降,逃兵不再是逃兵,離開了布綠克。 這位曾經去過印度當兵的年輕逃兵曾經告訴布綠克有關咖哩的美好,於是布綠克在戰後的德國漢堡擺起攤子,並開發出咖哩香腸這道美食,這道美食沒多久就傳遍半個歐洲。 二十七天的邂逅,沒有什麼海誓山盟,反倒是作者還把對納粹的控訴很微妙地寫進故事內;二十七天的邂逅,沒有什麼男歡女愛,只有整整沒有丈夫在身邊十年的布綠克和不願意調到漢堡城外散兵坑送死的布列門,彼此的相依;二十七的邂逅,沒有死去活來的甜言蜜語,只有倆人在精神與物資都極度潰乏的環境下的互相取暖。 看過「麥迪遜之橋」嗎?看過「家傳大煎鍋」嗎?看過「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嗎?如果把這三本動人心弦的元素混在一個故事當中,就是本書的靈魂。 為了不要陳述太多本書的故事以免影響讀者閱讀的樂趣,我只好用比較隱喻的形容詞彙來傾吐我讀完本書後的那股磅礡的共鳴與感動;本書的故事也好、主角也好、場景也好、甚至那美味的咖哩香腸,全都是歷史上的宿命與巧合所共同譜成的,咖哩香腸是一連串巧合的產物,二十七天的畸戀是歷史宿命的捉弄,整代的德國人更是集體錯誤與莫名悲劇的加害者與是受害者。 書中有段話:「愛情很美,因為兩個人在一起所以很美。但也正因為如此,分手才會如此困難。太多人只是勉強撐著過著其實並不愉快的兩人生活,直到第三者出現才結束。」 在愛情中有多少人能不為那美麗的花火吸引,不顧一切地去做一些事後懊悔不已的蠢事?世故的蓮娜˙布綠克用邂逅的小情人給她的味道,去封陳一段短短二十七天就足以回味無窮的愛情;一如「麥迪遜之橋」片中的中年女主角梅莉史翠普,用幾本雜誌與幾張照片作為悸動的封印。 布綠克所尋到的那道他的男人在印度所嚐到味道,一道撫慰破脆人心的美味,回不去的往事,回來了的故事,總只能停在某一個時間點上,但是咖哩香腸的美好感官歡愉卻可以在人的記憶與味蕾間來來回回穿梭。至於那老情人或那故事,或許有一天也會從你的記憶裡跑出來,等著等著,笑一笑,再跑回你心底。 閤上本書,不免會想想「咖哩香腸」的美味祕訣是什麼?是辛香料調理的咖哩?是新鮮甜美的蕃茄醬?是口感層次豐沛的牛肉? 還是那段可以藏在心中品償一生的真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