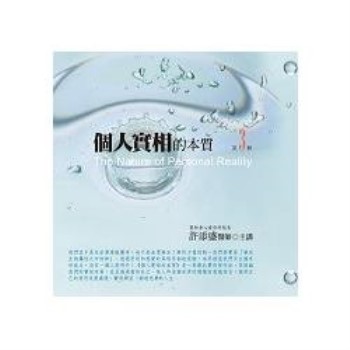這本書之所以命為《允執其中─朱高正六十自述》,是因為只有中道思想才能貫串我的一生。《尚書‧大禹謨》記載,當帝堯要將天下傳給帝舜的時候,提醒帝舜在做任何事,只要能「允執厥中」,不偏不倚,不要太過也不要不及,如此自能平治天下;而在《論語‧堯曰》中,也提到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允執其中」就是「允執厥中」,就是要人信守中道,做任何事都要像孔子所說的那樣:「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就是說,沒有一定要怎麼樣,也沒有一定不能怎麼樣,只要合於義理就好。從高二開始自學《易經》,《易經》最重要的思想莫過於崇中、貴中。因此從小以來,在我身上看不見教條,也沒有禁忌,只要合於正道,雖千萬人,吾往矣。一輩子中,我做了很多事情,在別人眼中總是難以理解,其中最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朱委員,你只要不離開民進黨,怎麼會輪得到阿扁當總統?」對於這種問題,我只能一笑置之,就如莊子所說「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本書特色
★昔稱「台灣第一戰艦」的親筆自述。
★「康德」博士重建中國文化主體的心路歷程。
★具體落實「批判時代」的社會價值。
名人推薦
廈門大學台研所所長 陳孔立先生
立法委員 李慶華先生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允執其中:朱高正六十自述的圖書 |
 |
允執其中:朱高正六十自述 作者:朱高正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11-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508 |
二手中文書 |
$ 632 |
傳記 |
$ 680 |
社會人文 |
$ 744 |
中文書 |
$ 744 |
政治人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允執其中:朱高正六十自述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朱高正
南宋大儒朱熹二十六代孫,一九五四(甲午)年出生在台灣省雲林縣,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聯邦德國波昂大學哲學博士。致力弘揚傳統優秀文化不遺餘力,本身又酷愛太極拳運動,《近思錄通解》與《白鹿洞講演錄》《四書精華階梯》是最近力作。
朱高正
南宋大儒朱熹二十六代孫,一九五四(甲午)年出生在台灣省雲林縣,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聯邦德國波昂大學哲學博士。致力弘揚傳統優秀文化不遺餘力,本身又酷愛太極拳運動,《近思錄通解》與《白鹿洞講演錄》《四書精華階梯》是最近力作。
目錄
序一 陳孔立
序二 李慶華
序三 王在希
序四 朱茂男
導讀 林深靖
第一個30年的上半段(1954-1969)
第一個30年的下半段(1969-1984)
第二個30年的上半段(1984-1999)
第二個30年的下半段(1999-2014)
後記
序二 李慶華
序三 王在希
序四 朱茂男
導讀 林深靖
第一個30年的上半段(1954-1969)
第一個30年的下半段(1969-1984)
第二個30年的上半段(1984-1999)
第二個30年的下半段(1999-2014)
後記
序
李慶華序
沒有朱高正,經國先生就不會解除台灣地區的戒嚴;沒有朱高正,經國先生就不會開放台灣同胞前往大陸探親。眾所公認的,朱高正是台灣民主化的頭號功臣,也是結束兩岸軍事對峙、促成兩岸和平交流的第一人。
我何其有幸,能夠成為高正兄的兄弟。其實,早在我們結成知交的二十年前,家父就是經國先生的左右手,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工會主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當時,高正兄還在國立台灣大學唸書,由於他是校園裡面的活躍份子,而且是位讓國民黨極為頭痛的學運領袖,他從那時就與家父結下不解之緣。二十年前,我們在新黨有三、四年的同志情誼,但我們的兄弟情誼則遠非同志情誼所可比擬。當高正兄開始著手《六十自述》時,就邀我為本書寫序,礙於情分我沒有理由可以推卻,只好應承下來。
這部《六十自述》凡七十六萬言,可謂是一部堂堂巨著,費時一年兩個月乃得完成。據我所知,高正兄到現在所寫的任何一部著作,包括博士論文與其它學術著作,不曾用超過三個月的時間,可見本書應該是高正兄這輩子最重視的一部著作。本書首先回顧他人生的第一個及第二個三十年,從對這兩個三十年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他對第三個三十年的自我期許。第一個三十年上半部所敘述的是,從出生到上高中;下半部則是從高中、大學、服役,以至於留學;第二個三十年上半部則從完成博士學位、返台投入民主運動、擔任立法委員四任十二年,以至於在北京的講學;而下半部,則開啟了整個關懷與工作的重點逐漸轉向大陸。
其實,高正兄的天賦之高,世所罕見。他本來已經準備前往美國留學,手續都辦妥了,只因為韓忠謨先生剛為了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將當時為了聲援余登發而組織遊行抗議的桃園縣長許信良,予以停職兩年的處分,乃毅然辭去司法院副院長,告別公職生涯,賦閒在家,卻極為懇切地鼓勵高正兄前往德國留學。而高正兄竟能只花八週不到就學好德文,而且拿到教育部留德語文考試第一名,光憑這一點就令人匪夷所思。
高正兄從高二就自學《易經》,早在上個世紀末,他的易學著作就在大陸獲得國家圖書獎的殊榮,在易學界備受推崇,被不少高校選為教材。更有趣的是,他在德國攻讀哲學,且專攻人人視為畏途的康德哲學,他有關康德哲學的德文著作也被世界權威哲學刊物《康德研究季刊》,評為當代研究康德法權哲學四本必備著作之一。高正兄能夠同時對東西方學術界的兩座高峰──《易經》與康德哲學──有如此的造詣,實在令我打從心裡佩服。我發現,他的學術成就之所以如此的豐碩,除了他有極高的天份以外,更重要的是,他的勤奮不懈。
我發現高正兄從小就非常善於利用零零碎碎的時間:初中時代,天天兩個多小時往返通車的時間,從來就是手不釋卷;很多朋友告訴我,高正兄在機場候機或是等行李,甚至通關向來都是手不釋卷,或是嘴裡唸唸有詞地在記誦經典。這也就難怪他也是朱子學的專家。當他在1993年得知自己的確是南宋大儒朱熹的第二十六代裔孫之後,他就自認為對弘揚傳統文化有責無旁貸的責任。就像《孟子》最後一章所言「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刪述六經,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子在稷下學宮,舌戰諸子百家,弘揚聖人之道;朱子創立道統說,集理學之大成,使千餘年來不斷被邊緣化的儒學,重新成為主流思潮,且影響力遍及東亞文明圈。我看高正兄也有「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這種感慨,大有以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者自居,在全球化的的新時代,有再度弘揚聖人之道的弘願。
高正兄陰錯陽差,由於身處戒嚴統治時期,而未能在學術界發揮所長,反而一頭栽入民主運動的洪流。高正兄與一般政治人物最大的不同,在於能夠說到做到,他每一次參選立法委員的主要政見,都能很快實現。他第一次在雲嘉南參選立法委員,向選民保證,把他送進立法院,非逼得實現國會全面改選,決不罷休。結果,他做到了。第二次回雲林老家參選的主要政見是廢除水租,結果當選後,就職前,他就做到了。第三次參選的主要政見,引進德國先進的老農津貼制度,結果他也做到了。其實,我第一次領略到高正兄的文采,是他在1993年初發表給李登輝的公開信〈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在經國先生生前,他就不只一次在立法院大聲疾呼,要求經國先生辭掉總統,以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身份接任行政院長,而讓李登輝接任總統,成為名副其實的虛位元首,如此內閣制就可以底定。事實上,經國先生去世之後,就是因為李登輝不願遵守憲法,不甘當一位沒有實權的虛位元首,以致每一次的修憲,無不是為他個人的攬權與擴權來服務。換句話說,由於內閣制遲遲無法確立,導致台灣政治亂象延宕了二十多年。就如高正兄所指出的,李登輝是台灣由盛世轉向衰世的罪魁禍首。
高正兄曾對「衰世」下了一個定義:「大道不行也,私慾橫流;鄉愿當道,賢能隱退;凡事沒是沒非,無可無不可;若真有問題,先拖一陣子,當大家懶得再追究時,問題就算解決了。」我覺得高正兄對衰世的界定,十分傳神,而且維妙維肖。用「衰世說」來回顧台灣過去二十多年的亂象,真是若合符節。高正兄常跟人家說:「處在衰世,千萬不能太過關心公共事務,因為越關心,挫折感就越大。」他老是勸大家,先把自己的家庭照顧好,行有餘力再幫忙身邊的人。我身為立法委員不能同意他這種看法,但也很難駁斥它。
從高正兄的衰世說,我倒是看出他漸漸把他的關注重點從台灣移往大陸,他在大陸的活動在這本書裡頭,有很多精彩的描述。反正,高正兄是位精彩的人物,他在台灣表現十分精彩,我相信他將來在大陸的表現也將十分精彩。所以這本書,其實就是高正兄精彩人生的縮影。最後,我想引述前賢、原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博士在1995年為高正兄的著作所寫的序:「想要了解朱先生這個人,就一定要看他的書;關心國家前途的人,也非看他的書不可。朱先生治學之勤勉,問政之純真,在在使得筆者深信他的思想一定會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產生極大的影響。」
沒有朱高正,經國先生就不會解除台灣地區的戒嚴;沒有朱高正,經國先生就不會開放台灣同胞前往大陸探親。眾所公認的,朱高正是台灣民主化的頭號功臣,也是結束兩岸軍事對峙、促成兩岸和平交流的第一人。
我何其有幸,能夠成為高正兄的兄弟。其實,早在我們結成知交的二十年前,家父就是經國先生的左右手,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工會主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當時,高正兄還在國立台灣大學唸書,由於他是校園裡面的活躍份子,而且是位讓國民黨極為頭痛的學運領袖,他從那時就與家父結下不解之緣。二十年前,我們在新黨有三、四年的同志情誼,但我們的兄弟情誼則遠非同志情誼所可比擬。當高正兄開始著手《六十自述》時,就邀我為本書寫序,礙於情分我沒有理由可以推卻,只好應承下來。
這部《六十自述》凡七十六萬言,可謂是一部堂堂巨著,費時一年兩個月乃得完成。據我所知,高正兄到現在所寫的任何一部著作,包括博士論文與其它學術著作,不曾用超過三個月的時間,可見本書應該是高正兄這輩子最重視的一部著作。本書首先回顧他人生的第一個及第二個三十年,從對這兩個三十年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他對第三個三十年的自我期許。第一個三十年上半部所敘述的是,從出生到上高中;下半部則是從高中、大學、服役,以至於留學;第二個三十年上半部則從完成博士學位、返台投入民主運動、擔任立法委員四任十二年,以至於在北京的講學;而下半部,則開啟了整個關懷與工作的重點逐漸轉向大陸。
其實,高正兄的天賦之高,世所罕見。他本來已經準備前往美國留學,手續都辦妥了,只因為韓忠謨先生剛為了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將當時為了聲援余登發而組織遊行抗議的桃園縣長許信良,予以停職兩年的處分,乃毅然辭去司法院副院長,告別公職生涯,賦閒在家,卻極為懇切地鼓勵高正兄前往德國留學。而高正兄竟能只花八週不到就學好德文,而且拿到教育部留德語文考試第一名,光憑這一點就令人匪夷所思。
高正兄從高二就自學《易經》,早在上個世紀末,他的易學著作就在大陸獲得國家圖書獎的殊榮,在易學界備受推崇,被不少高校選為教材。更有趣的是,他在德國攻讀哲學,且專攻人人視為畏途的康德哲學,他有關康德哲學的德文著作也被世界權威哲學刊物《康德研究季刊》,評為當代研究康德法權哲學四本必備著作之一。高正兄能夠同時對東西方學術界的兩座高峰──《易經》與康德哲學──有如此的造詣,實在令我打從心裡佩服。我發現,他的學術成就之所以如此的豐碩,除了他有極高的天份以外,更重要的是,他的勤奮不懈。
我發現高正兄從小就非常善於利用零零碎碎的時間:初中時代,天天兩個多小時往返通車的時間,從來就是手不釋卷;很多朋友告訴我,高正兄在機場候機或是等行李,甚至通關向來都是手不釋卷,或是嘴裡唸唸有詞地在記誦經典。這也就難怪他也是朱子學的專家。當他在1993年得知自己的確是南宋大儒朱熹的第二十六代裔孫之後,他就自認為對弘揚傳統文化有責無旁貸的責任。就像《孟子》最後一章所言「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刪述六經,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子在稷下學宮,舌戰諸子百家,弘揚聖人之道;朱子創立道統說,集理學之大成,使千餘年來不斷被邊緣化的儒學,重新成為主流思潮,且影響力遍及東亞文明圈。我看高正兄也有「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這種感慨,大有以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者自居,在全球化的的新時代,有再度弘揚聖人之道的弘願。
高正兄陰錯陽差,由於身處戒嚴統治時期,而未能在學術界發揮所長,反而一頭栽入民主運動的洪流。高正兄與一般政治人物最大的不同,在於能夠說到做到,他每一次參選立法委員的主要政見,都能很快實現。他第一次在雲嘉南參選立法委員,向選民保證,把他送進立法院,非逼得實現國會全面改選,決不罷休。結果,他做到了。第二次回雲林老家參選的主要政見是廢除水租,結果當選後,就職前,他就做到了。第三次參選的主要政見,引進德國先進的老農津貼制度,結果他也做到了。其實,我第一次領略到高正兄的文采,是他在1993年初發表給李登輝的公開信〈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在經國先生生前,他就不只一次在立法院大聲疾呼,要求經國先生辭掉總統,以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身份接任行政院長,而讓李登輝接任總統,成為名副其實的虛位元首,如此內閣制就可以底定。事實上,經國先生去世之後,就是因為李登輝不願遵守憲法,不甘當一位沒有實權的虛位元首,以致每一次的修憲,無不是為他個人的攬權與擴權來服務。換句話說,由於內閣制遲遲無法確立,導致台灣政治亂象延宕了二十多年。就如高正兄所指出的,李登輝是台灣由盛世轉向衰世的罪魁禍首。
高正兄曾對「衰世」下了一個定義:「大道不行也,私慾橫流;鄉愿當道,賢能隱退;凡事沒是沒非,無可無不可;若真有問題,先拖一陣子,當大家懶得再追究時,問題就算解決了。」我覺得高正兄對衰世的界定,十分傳神,而且維妙維肖。用「衰世說」來回顧台灣過去二十多年的亂象,真是若合符節。高正兄常跟人家說:「處在衰世,千萬不能太過關心公共事務,因為越關心,挫折感就越大。」他老是勸大家,先把自己的家庭照顧好,行有餘力再幫忙身邊的人。我身為立法委員不能同意他這種看法,但也很難駁斥它。
從高正兄的衰世說,我倒是看出他漸漸把他的關注重點從台灣移往大陸,他在大陸的活動在這本書裡頭,有很多精彩的描述。反正,高正兄是位精彩的人物,他在台灣表現十分精彩,我相信他將來在大陸的表現也將十分精彩。所以這本書,其實就是高正兄精彩人生的縮影。最後,我想引述前賢、原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博士在1995年為高正兄的著作所寫的序:「想要了解朱先生這個人,就一定要看他的書;關心國家前途的人,也非看他的書不可。朱先生治學之勤勉,問政之純真,在在使得筆者深信他的思想一定會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產生極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