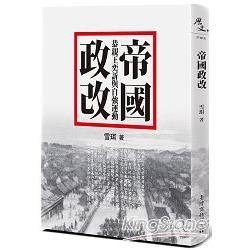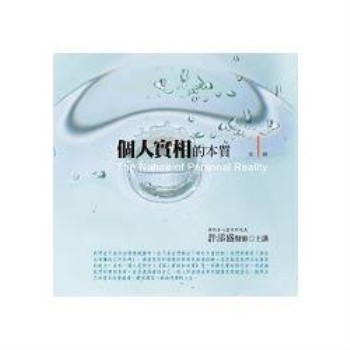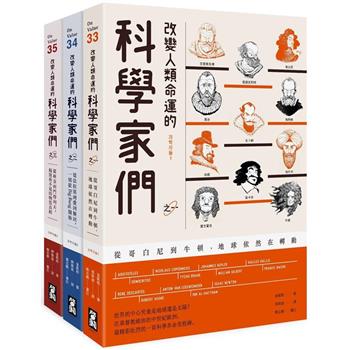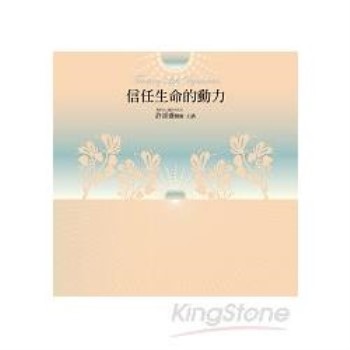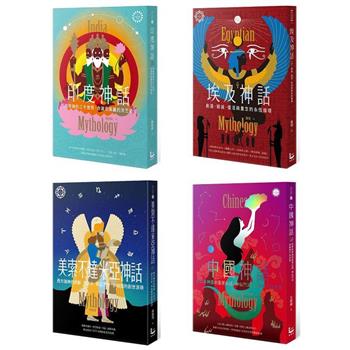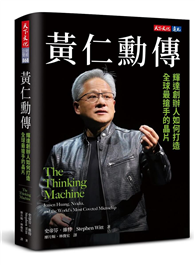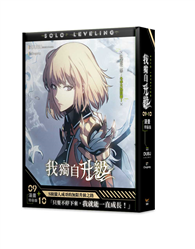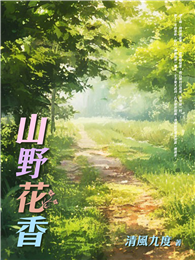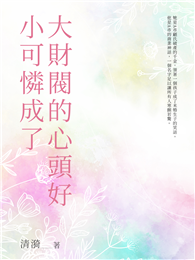代序
難以複製的大清王爺 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 孫旭光
一五○年前的一八六○年九 月,英法聯軍的隆隆炮聲將大清王朝的咸豐皇帝趕到熱河「狩獵」,而咸豐則將京城的爛攤子丟給了自己的弟弟 時年二十七歲的恭親王奕訢。幾天後,攻入北京 的侵略者悍然將號稱「萬園之園」的圓明園付之一炬。臨危授命的奕訢親歷了種種恥辱,與英法兩國簽訂了《北京條約》,以割地賠款的代價使內憂外患的帝國有了 難得的平靜。
可能恭親王本人也沒有想到,在此後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他將會在大清王朝扮演一個極為特殊的角色。在歷史浪潮的顛簸中,恭親王站到了舵手的崗位上,極力維持著大清帝國這艘破敗的巨輪緩慢前行,直至心力交瘁。
回顧起來,恭親王奕訢的一生確實具有濃厚的傳奇色彩。先是在與咸豐的儲君之爭中功虧一簣,被封為恭親王後不久便受到咸豐的猜忌和排擠。經過與外國交涉的 歷練,勇於任事的奕訢開始奠定自己在政壇的地位。咸豐死後,他抓住機遇,同慈禧共同發動辛酉政變,控制了中樞機關,總攬清朝內政外交,成為權勢顯赫的鐵帽 子王。作為清廷貴族中難得的有才識者,恭親王奕訢幾乎一手導演了隨後三十年間的王朝改革,可謂當之無愧的「總設計師」。從總理衙門到洋務運動,從近代海軍 到近代教育,使本已痼疾纏身的王朝居然出現了頗具聲勢的「同光中
興」,可謂厥功至偉。
遺憾的是,在錯綜複雜的權力鬥爭中,奕訢始終無法擺脫慈禧太后的陰影,不得不一次次在宦海沉浮中掙扎,最終抱憾辭世。但是歷史不會忘記奕訢,他的時代抱負和政治智慧至今仍值得後人思考。
十九世紀後半葉,西方列強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面都處於急劇發展時期,中華帝國卻裹足不前。清朝軍隊雖然屢屢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面前蒙羞,但多數士大夫仍然頑固地沉浸在天朝大國的舊夢中,無事則空談氣節,有事則顢頇畏縮。
即使貴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恭親王,也是在極為艱難地實施滿腔抱負。事實證明,在其一生的改革努力中,奕訢幾乎無時無刻不受到保守勢力的牽掣。他首先 必須在權力鬥爭的夾縫中謀生存,然後才能小心翼翼地為王朝謀發展,其代價便是個人命運的幾番沉浮以及朝野輿論的毀譽參半。正如本書作者曾經感慨的:「儘管 恭親王早已獲得了『鬼子六』的雅號,被人們貼上了自由派的標籤,但是,除了蔡壽祺之類投機鑽營的舉報者外,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對他的人品及政治 品格有過懷疑。這種穩健的政治手法,使恭親王在關鍵時刻,既能推動改革不斷前進,也能掩護激進的改革者從反對的聲浪中逃生。」
歲月如 煙,那位曾經書寫了一段傳奇的恭親王已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不過他的府第倒是在歷經滄海之後得以保存。如今,在風景秀麗的北京什剎海西南角,有一條靜謐悠 長、綠柳蔭蔭的街巷,當年門前車水馬龍的恭王府就坐落在這裡。作為現存清代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建築,恭王府已成為中外聞名的旅遊景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雖然近些年來這裡的遊人如織,但絕大多數看客都是為著恭王府曾經的主人著名權臣和珅而來的。現代的人們往往會對虛構的電視劇趨之若鶩,卻對真實的歷史漠然 置之,這恐怕要算恭親王奕訢的又一重悲哀了吧。
著名學者侯仁之先生曾說「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在浮躁喧囂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 真正體味這其中的含義呢?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現今恭王府的管理者,我由衷欽佩雪珥先生非凡的歷史見地。雖然雪珥自稱為非職業歷史拾荒者,但他多年來始終 以獨特的視角致力於中國近代改革史的研究,成果斐然,其已出版的《大東亞的沉沒》《絕版甲午》及《國運一九○九》等作品均引起了熱烈反響即是明證。在雪珥 看來,恭王府曾經的主人。
恭親王奕訢堪稱是中國近代改革的源頭。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本人曾多次前來恭王府實地搜尋資料,憑弔歷史,最終寫成本書,為我們展現了一代親王在那個雲詭波譎的年代中的颯爽英姿和痛苦無奈……
毫無疑問,恭親王的傳奇堪稱中國近代史上的絕版,但我希望像雪珥先生這樣的傑出研究永遠不會絕版。
二○一○年八月於恭王府
自序
欄杆猛拍春夢驚 雪珥
7月的鵝毛大雪,飛飛揚揚地飄落在澳大利亞的阿爾卑斯山上。套在厚厚的雪橇鞋裡,我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行路難。只有踏上雪橇板,才能從滑行的輕快中體會到減少摩擦所帶來的快感。
這種快感,應該是大家都喜歡的,至少光緒皇帝也喜歡。
這張發表於英國《圖片報》(The Graphic)的版畫,描繪的是光緒皇帝在北海冰凍的湖面上,乘坐著奧地利贈送的雪橇。拉雪橇的,是極具大清特色的"馴鹿"——8名太監,他們熟練地踩著同樣是舶來品的冰刀鞋,帶著帝國的最高元首,在冰面上滑行。
夜晚,守著熊熊燃燒的壁爐,孩子們熟睡的呼吸在屋子裡輕輕迴盪。看著手中發黃的老報紙,1895年1月19日的出版日期清晰地標註在報頭邊上。一個帝國,就如同雪橇急速而過留下的雪痕,隨即被時光的嚴寒封上,鏡面似的光亮得幾乎不留痕跡,讓人感慨歲月無情。
雪峰上的天空無比澄澈,南十字星閃爍,北斗星已無處可尋。即便斗轉星移,卻總是有顆星在指引著暗夜的方向,令你無法質疑造物主的神奇。
半年前,我也是在漫天的風雪中,第一次走進了後海邊的恭王府。
遊人如織,都是來參觀"和珅他家"的。中國人實在太渴望成功了,對於成功的路徑並不在意,走正途也好,撈偏門也罷,只要能成功,哪怕如流星般地劃過長空,也能成為萬人仰慕的榜樣。
在一道道流星的燦爛光芒下,那些恆星倒是顯得晦暗、無趣。
恭親王就是這樣的一顆恆星。
作為中國近代改革開放的第一個畫圈者,他不僅將那個背後世描繪為"腐朽、沒落、反動"的大清王朝延長了半個多世紀的生命,並且在歷經千年的自大後,第一次將中央帝國請下了神龕,主動平視——而非俯視,亦非被人打翻在地後被迫仰視——整個世界。
作為一個被革命者痛斥為"韃虜"的少數民族政權,清帝國以自己近300年的歷史,打破了"胡人無百年運"的宿命咒語,也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一個巨大的問 號,拷問著無數後人:走了那麼久,我們究竟離起點有多遠?離終點又有多遠呢?無數的大王旗換了又換,無數的海誓山盟說了又說,彷彿戲台上的斑斕戰袍和假聲 念白,曲終人散,如果失去了戲台,我們還能找到自己真正的角色嗎?
這是一個弔詭的現象:在主流話語體系對清王朝的普遍貶低和詛咒中,清王朝留下來的各種遺產,尤其是前30年經濟改革(洋務運動)和後10年政治改革(清末新政)的經驗教訓,卻成為後世自覺不自覺的效仿對象。歷史的傳承,其實並不是人力所能切斷的。
作為大國的"總理"、血統最為高貴的皇族、同時代人中難得的清醒者,恭親王實在是太低調了,他的光芒被掩蓋在太后那巨大的寶座陰影下和那些充滿八股陳詞的公文之中。
後人刻薄地說他"一生為奴",卻不知這並非個性的選擇,而是中國特色的權力運作的定位結果。作為接近最高權力的"老二",如果不甘寂寞,就只有兩種結 局:成為老大,或者成為零,all or nothing。這種勝者通吃的零和遊戲,註定了中國的舞台上只能上演獨角戲,梁啟超稱之為"一人為剛萬夫柔"。於是,恭親王便只能"柔",在政治精神層 面上自我閹割,以便在權力這一強效春藥面前令人放心。
恭親王故後,這座豪宅很少有人關注,除了後世那位贏得萬千民心的周恩來。不知未來的史家們,該如何解讀日理萬機的周恩來,何以會無數次地、低調地來到這裡,並將盡早開放恭王府作為其政治遺囑之一?
恭親王給後人留下一個懸念。
他曾經寫過一首七律,懷念他曾經的助手寶鋆:
只將茶蕣代云炚,竹塢無塵水檻清。
金紫滿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虛名。
因逢淑景開佳宴,自趁新年賀太平。
猛拍欄干思往事,一場春夢不分明。
這本是一杯盛滿了牢騷的女兒紅,卻在"猛拍欄干思往事"一句中,露出了燒刀子般的崢嶸烈度。
"拍欄杆"這種方式,最早是一位名叫劉孟節的宋人紀錄的,劉詩人常感懷才不遇,寫下了"讀書誤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杆拍"。道了辛棄疾那裡,就不僅"欄 干拍遍",還要"把昊勾看了",一手拿著刀劍,一手猛拍欄杆,這就不只是抑鬱,而且十分憤懣了。恭親王為何而抑鬱呢?又為何而憤懣呢?
更為吊詭的是,他後來又把"猛拍欄干思往事"一句刪除,改成了"吟記短篇追往事",拿刀子改成了拿筆桿子,拍欄杆改成了寫作文,硬生生地將一盤重辣重麻的川菜,改成了溫潤甜膩的蘇點。
或者,逝者如斯,恭親王想不豁達都難,牢騷太盛防腸斷呀……
《絕版恭親王》這個系列在報紙上連載時,一些讀者悄然而熱烈地反饋:這是一本中國官場的教科書。
我不禁愕然。
在我想來,這本該是中國改革史的另類紀錄和解讀。我曾經認真地回頭檢察,看看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我有心所栽的花成了無意所插的柳,卻隨即釋然。原來, 中國式的花、柳竟是如此難分難解,權謀幾乎無時無刻不是生活中的主旋律。無怪乎我的上本改革史小說《國運1909》,被一些朋友當作了"官場導讀",相互 推薦,居然多次登上排行榜。
這種特殊的市場"被定位",導致我的讀者大多是沉默的一群。他們在看,他們也在思考,但他們不說。不說,不是因為不會說,而是因為不便說,也不想說。我曾經的師長、紅牆內的一位顯官,據說看了我的專欄徹夜難眠,長嘆一聲後道:不當家不知柴米貴,難啊!
我似乎恍然大悟:他們並非喜歡我的文字,而是語文中得主人公產生了共鳴。體制內的改革者,一面要和光同塵,一面要負重前進,艱難而孤獨。掌聲難得,噓聲 易起,本想"左右逢源",卻往往是"左右為難",上下不討好,裡外不是人。這種"勢禁行格"下的痛楚,但凡是想有所作為的當家人,都能感同身受。
如果這本小書果能令"當家人"們產生小小共鳴,就算被人稱作"官場教科書",又如和呢?
現今恭王府的管理者們,的確很讓我大吃了一驚。
最初我是純粹從一個游客和商人的角度,驚嘆於這麼一家文化部直屬的文保機構,居然能把一個沒落了百年的王府,經營的有聲有色,再度驗證了體制中本就有不少能人,只是如何發揮而已。
而當我有幸參觀了他們的資料庫,並向他們的研究人員討教切磋後,那種只在象牙塔內瀰漫的書卷氣,十分令我陶醉。作為中國王府文化的研究中心,他們在這個喧囂的年代裡,依然默默地守著古卷青燈, 保存和琢磨著民族記憶中最可寶貴的一部分。
我必須向他們表達我的謝意,並在澳洲的星空下為他們禱告祈福:
——孫旭光博士,如今恭王府的"總管",一位年輕的學者型官員,他的史學修為、開明態度及經營能力,令我折服;
——劉霞大姊,恭王府管理中心副主任,她的熱情及對恭王府一草一木的極度熟悉,幫助我在最短時間內領略了恭王府的底蘊;
——陳光大姊,恭王府的學術領頭人,一位從事過很多年艱苦的野外考古的專家,踏實、勤勉、低調、博學,令我受益良多……
又開始下雪了,真正的六月雪,萬里外的故國想必早已一片火熱。明天不知道是否還能登頂,去拍拍那被冰雪包裹著的欄杆?
2010年7月6日記於澳洲阿爾卑斯山
導讀
改革比革命辛苦很多 公孫策
拿穿衣服為比喻,革命好比買一件新西裝,改革好比修改舊西裝,而且是穿在身上改。
年輕讀者沒有「西裝必須訂作的」的經驗,但可以嘗試想像:身上這件西裝是不可以脫下來的,但已經不合身了,不改就捉襟見肘,再拖則脫線落袖,最終將衣不蔽體。可是,穿在身上改衣服,就難免被針扎到、被剪刀刺到,甚至左右不對稱。
然而,改革還是比革命來得容易,因為改革者的必要條件是擁有權力。但擁有權力不代表就能夠從心所欲,因為改革一定是跟既得利益對抗;而既得利益的力量之大,平常不感覺,等到打下去,出現反彈,才知道有多厲害。
歷史上的改革者各有甘苦:漢武帝劉徹的改革最成功,但他得「忍」到祖母去世才能發動。北魏孝文帝拓拔宏的漢化與土地改革,則逼出了六鎮叛變。以上二位本身都是「老大」,可以乾綱獨斷「成大功者不謀於眾」,他們的改革也都能克竟全功。
相較之下,「老二」的改革就辛苦多多:
戰國時商鞅變法,由於秦孝公全力支持,所以能全面推動。但商鞅得罪既得利益最多,下場也最慘──車裂於市。北宋王安石變法,宋神宗支持,可是遭到舊黨(太后支持)杯葛,最終全面失敗。明朝張居正改革,明神宗與太后都支持,因此終其一生都沒問題,但死後仍遭抄家。
本書主角大清恭親王奕訢跟前面幾位都不一樣:他「處在大於二(老二),小於一(老大),但無限接近於一的地帶」。另外,他雖然一度擁有最大權力,可是大 清帝國卻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外有夷人,內有保守派,政府則上有太后,下有藩鎮,而藩鎮的坐大又是由於經過了一場長毛之亂(太平天國)。如此內外交迫、上下 相煎的處境,才造就了這位「難以複製的大清王爺」。
恭親王的改革有多好,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看得更清楚。作者雪珥先生一再提及恭親王對光緒說的:「小心廣東小人(指康梁)。」作者更形容戊戌變法是一種「休克療法」,事實上造成了大清這個體質虛弱的病人「休克致死」──武昌起義只是最後一根稻草。
也有論者以為,恭親王奕訢不但不是一位改革者,甚至是反改革份子。公平一點的說法是,恭親王不是主動要改革,可是在那個「京師的御林軍已經潰散,圓明園 被洗劫,北京城也已失陷」的情況下,恭親王「肩負著大清帝國最為沈重的擔子」,「髒活累活總得有人做,恭親王並沒有選擇的機會」。
一 個毫無心理準備的天潢貴冑,被動地接下了龐大帝國的爛攤子,卻能「宣導、推動並親自操盤大清改革,無論是深度、廣度、還是力度,乃至遭遇的阻力,都可謂前 無古人、後少來者」。「同光中興」那一批今人耳熟能詳的名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無一不是在他的保駕護航下,得以保全、發展」。恭親王和他的核心 幕僚文詳、寶鋆,不但能賞識、授權,更能駕馭控制這些手握兵權的漢人疆臣,「其政治智慧和手腕不容小覻」。
能夠統馭這一批湘、淮軍 頭,恭親王乃能斷掉洋人「不排除聯合地方將領」的念頭,而以總理衙門為唯一打交道的對象。這一點,在八國聯軍時,發生東南互保運動,中國從此成為孫中山口 中的「次殖民地」,更可對照出恭親王的可貴(當時他已去世二年)。回頭看那一段歷史,中國沒有陷入跟印度一樣的命運,恭親王奕訢爭取到洋人的敬重,是非常 重要的一個因素。作者並沒有用明顯的文字下如此結論,可是書中引用了大量的西方使節、學者,乃至卸任元首對恭親王的描述、印象,足以支持這個論點。
藩鎮配合、夷人敬重,恭親王才能從容應付以倭仁為首的保守派。他甚至發明了「西學源於中學」之說,並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認同天文、算學「本為儒者所當 知,不得目為求巧」。最後更用上了太極拳的精髓,先讓倭仁「來勁落空」,然後「借力使力」,任命倭仁也為總理各國事物衙門大臣,卒以倭仁墜馬(是意外或故 意,仍有爭議)收場。
然而,恭親王在怎麼厲害、機敏、有手腕、得人助,他終究是「老二」,擋不住「老大」慈禧太后的一擊、再擊、三擊。
但本書作者雖然推崇恭親王,卻也對慈禧太后持公平之論。
要說恭親王當初毫無心理準備,慈禧太后又何嘗有心理準備?這位懿貴妃葉赫那拉氏入宮時,「不是由大清門進入」(只有皇后過門才由國門大清門抬入),沒有 任何儀式,也就是「二奶」。雖說「母以子貴」,可是比正宮慈安太后仍然矮了半截,政權抓在肅順、端華等顧命八大臣手中。她得先跟慈安太后結成「生命共同 體」,然後聯合老六(恭親王)鬥垮肅順,之後,還要對付「老五(淳親王)、老六加老七(醇親王)──人家可是骨肉兄弟,凡事可以毫無忌諱的攤開來談。她則 是嫂嫂,絕大多數事情只能用「猜」的。
簡單說,「由蘭兒到老佛爺」,慈禧太后的成長、進步,著實令人刮目相看。而她的進步過程,在本 書中也可以看到,只不過,作者描述慈禧太后都是側影,讀者必須「別有用心」才讀得到。作者更不認為慈禧太后罷黜恭親王是權鬥,而是一種訓誡,「這種訓誡不 是因為政見,而只是因為老二離老大的位置過於接近,老大需時時敲打老二,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本書另一個值得今人參考的重點,是第五章〈美國兄弟〉寫到當年的中美關係,包括喬治.華盛頓如何受到中國人(甚至超過美國人)的高度推崇,以及首任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居然成為大清首位外國籍「欽差」(正一品頂戴花翎)。」
相對於當年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We should not do to others what we would not that others should do to us “蒲安臣語)關係,中、美兩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角色以及競合關係,其實頗多啟發,也是作者苦心孤詣,卻未刻意強調的。
在導讀之外, 個人有一點異於雪珥先生的見解。第三章〈風中蘆葦〉末尾提及:下崗在家十年,恭親王常去的地方是京西剎戒台寺,寺內有棵臥龍松,馳名京師,很少題詞留墨的 恭親王卻為之題寫「臥龍松」三字,刻碑立於松下。逐漸習慣於憂讒畏譏的恭親王,如此不避嫌疑地自比為「臥龍」,究竟是何心意?愚見以為,諸葛亮受劉備託 孤,大權在握,卻自始自終不曾取阿斗而代之,杜甫因此稱譽他「萬古雲霄一羽毛」。恭親王奕訢提寫「臥龍松」,應非悲憤失去權位,而是想藉此表態「絕無二 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