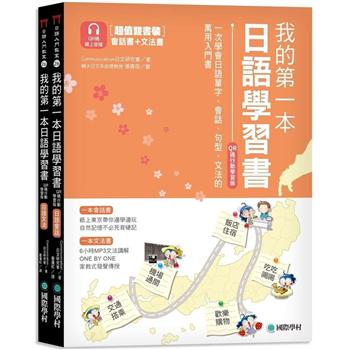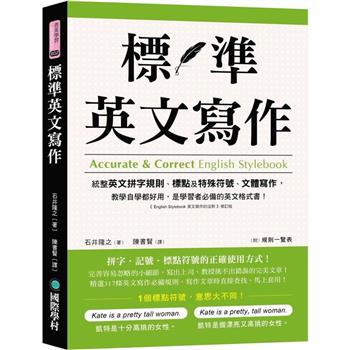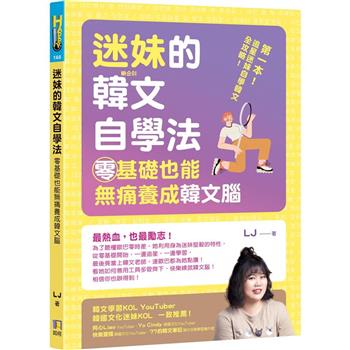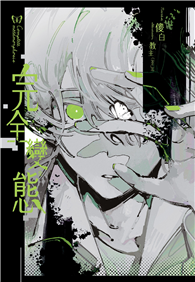盛花的起源
當今廣為流行的盛花〔1〕,被不少人視為一種獨立於各流派之外的特殊花法。說到插花的起源,大約中國和日本皆古已有之,而具體於何時興起,則概觀坊間種種傳說,均無確證,難為信論。其中一說,乃
謂在遠古的神代〔2〕,地神彥火火出見尊在日向國〔3〕海邊遺失了天釣針,由名為潮路翁的老人尋獲歸還,其時,老人將當地繁茂的千草萬花插於器皿內以為供奉,令神尊甚為滿意,由此插花之技廣傳於世。據說
至人皇第三十四代推古天皇〔4〕在位時,聖德太子〔5〕好此道,傳於才通和漢的近臣小野妹子〔6〕,世間才有了有程式規範的花道。邇來天下承平,各流派的法式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文人墨客間廣泛宣導各種應用
插花,為了在籃子、水盆中表現山野池澤的感覺,產生出所謂錦生、皿生等新插法。至近世,更創新出專用的缽等工具,插入和洋草木,為之新命名為盛花,並各處流行開來。
現在世間所稱盛花者,大致可以分為洋風(西洋式)與和風(日本式)兩種類。洋風盛花主眼於表現華美豔麗,並無特定法式,只將各種色彩的花相配插在一起觀賞,徒具豔麗,有乏陳雅味之弊,與普通國
人的審美不符,所以一般只用於西式居室內的裝飾。
與此相反,和風盛花有一定的規範,主張須具備天地人三才〔7〕而發揮自然的美感。技法上較洋風為進步,又適合國人欣賞品位,與室內環境相調和,其應用範圍也廣得多。
關於插花的起源與變遷,諸說紛紜,甚為複雜,相關的研究著作也很多,故在此僅作一極簡單的敘述。
世間對花的愛賞
設有人問,縱通古今,什麼東西最美,我們肯定毫不謙虛地回答是花。自古以來形容美女才媛,或喻以牡丹之豔麗,或喻以梅花之清楚,或喻以菊花之清豔,或喻以蓮花之清高、櫻花之妖姿豔態、海棠之綽
約嬌羞之類,總之少有不用花來形容其美的。無論怎樣貴重的美術品,相較于自然花的美,都相形見絀;再有名的畫家、造花師,其技術畢竟都無法寫盡天然花全部的美。我們必須感謝天地的造物主,為了給我
們精神的慰藉,造就了如此美麗之物。
我們無論是感到生氣、暴躁、悲傷、哀愁、寂寥,只要一看到花,自然就能使心靈得到安撫。這是因為花的美麗色彩和天真爛漫的風情映入人心之中。花之德感化人,花之香沁人心脾,花的美簡直要把人融入其中。
所以學習插花之道,精神自然變得優美高尚,繼而通過技術體現出自身的心靈即在作品上發揮每個人的個性。在這些帶有個人氣息的作品上,自然可見各自的德性及修養高下。
猶如畫家的畫、書家的字、雕刻家的雕刻、文學家的文章各自反映其內心世界一樣,花道家的心理在其手中的花朵上活躍著,且更明瞭地展現出其個人趣向。學習插花的技藝,讓適合的花朵依照個人趣向綻
放生命的活力,首先必須提高內心的修養,其中德性涵養和知識技能的修養尤為關鍵。這些修養不足,插花外觀無論如何巧妙,姿態無論如何優豔,在識者眼中看來,必能明見其趣向之缺點。
任何美術家都無法把活著的東西直接應用在其作品上,只有花道家可以讓鮮花為自己的精神工作,應用各種手法,加以個人趣向,造就出一個藝術品。這種技藝世間無類,是真正高尚優美之物,所以花道家尤須保持內心清淨純真,從而為世人所敬仰。
盛花的趣味
花道家在裝飾壁龕〔1〕的花器內設計插花,恰如畫家考慮構圖一般,心中先已組好了理想的花姿。然而細細觀察材料花枝,枝形常與預想花姿不合。若將它們作種種組合考慮,有時會得到有意外奇趣的造型。
仿佛創作詩歌的人,有了大體的腹稿,卻被平仄制約,被韻字拘束,不得立成,雖須費一番苦思冥想,到底成就了意外的名詩一樣。多費苦心之處,也是趣味所在。且世間優美清淨之物,莫過於花,面對花朵,一
時之悲哀、憤怒、疲勞,盡數揮散,不覺間已心曠神怡,栽培之有無限的趣味,賞玩之可得絕大的享受。是以一學插花之道,自然令精神高尚,與那有害無益的單純娛樂,不可相提並論。更何況都市生活,家屋櫛比,
無有尺寸空地,眼不能觀綠樹之雅趣,手不能玩花瓣之風致。此輩都市人賞玩盛花,只見滿盆清新楚麗,令人追憶起郊外的四季風情,油然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懷念。人類社會的精神壓力時刻加重,欲解其勞,舍
花何求?近來各地鄉村、城市,均盛行賞玩草花,廣為栽培,足可為此明證。
盛花之姿態。
第一節 洋風盛花
如前所述,現代盛花大體上可分為洋風(西洋式)和和風(日本式)兩種。具體從花上來說,洋風主要是桌上擺放,適合配置於餐桌、時下日本家庭中流行的會客桌等。其中四面觀的花型最搶眼,其他依據放
置場所的不同,也有兩面正面〔1〕、三面正面等各異其趣,其首要點都在於“堆高美感”。四面觀的插花多整體呈球形,中間高,四周逐漸降低,視材料花器的具體情況,也可以從水盤〔2〕自然垂下。兩面正面、
三面正面的花型則常是中間低,向兩面或三面自然變寬變高地插。
第二節 和風盛花
和風盛花主要依據草木自然的生長和風致來修整花姿,可謂極為自由,沒有生花〔1〕那樣的固定花形。然而其自由之中暗藏著不變的根本規律,且必須依據材料、季節、花器的不同而隨機應變,初學者往往因
此感到困難,卻又無法回避。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其難點反而會令人感受到趣味,正是自由的風格才能體現其真實韻味和價值。
第三節 盛花的基本花形
花道各流派多以構成不等邊三角形作為美的要素,同樣,盛花也是在不等邊三角形狀基礎上來完成一瓶花的。不講究方式和做法的插花最為簡單,將天然的花枝在色彩搭配上不失自然地插上去就好。但是,插
花如果不具備大體的所謂“天地人”格局的話,花姿不怎麼好看。因此將“天地人”應用於不等邊三角形中,才能恰到好處。即在一瓶插花中,中心高聳的花枝為“天”又稱“真”,低垂水際的花枝為“地”又稱“體”,兩者中間一枝為“人”又名“副”,並稱天地人三才。
這三枝是插花本體,其餘的花枝都是補充的配飾而已。盛花大體與之相同,一般使用以下的名稱:
天= 主位(真)
人= 副位(副)
地= 客位(體)
主位與副位的裝飾花枝為“胴”、“見越”〔1〕
客位的裝飾花枝為“前置”、“谷”
名稱大體如上,但並不確定,各有不同說法。尤須注意的是,中間裝飾之枝視時間和場合而變化,加以妙用可增添盛花的趣味,但如理解不深便貿然添加,可能反而有損花姿。上述雖然套用固定花型,仍有具體的變化。猶如書體有真(楷)、行、草之別一樣,盛花也分真行草〔2〕。插花時腦中預先設計好大體花型,實際操作中依據材料花枝、花器加以調整,有千變萬化之姿。詳細如圖所示。
花器與花留。
第一節 盛花的花器
初學盛花者在練習的時候所用的花器並無定規,依個人喜好任意使用也不妨事。盛缽一般多用水盤、竹籃、葫蘆之類,以闊口、腹內不深為好。其他金屬制或燒杉〔1〕等材質的舟形、井圈形、提桶形之類變
形盛缽,近來頗為流行,但是本質上而言插花畢竟花是主角,過於華麗喧賓奪主的花器反而有可能降低整個作品的品味,花銷上也有事倍功半之恨。(參照圖解)
第二節 盛花的花台
花台也有多種,盛花多用薄板花几、高桌等,一般的花台也可以使用。只要和花器協調的話就沒問題。
第三節 盛花的花留
花留也有形形色色的巧思新設計的,初學者仍是選用傳統的銻制七寶形、龜形、劍山(針山)等為好。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插花冊子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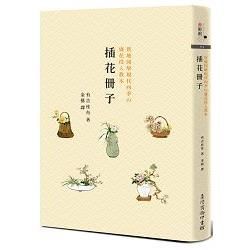 |
插花冊子 作者:有吉桂舟 / 譯者:金藝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6-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25 |
二手中文書 |
$ 356 |
休閒生活 |
$ 356 |
插花/花藝 |
$ 383 |
藝術設計 |
$ 418 |
中文書 |
$ 419 |
園藝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插花冊子
★完全不懂插花也看得懂!給插花初學者的小秘訣手冊。
★色彩豐富的手繪插圖示意,讓讀者可以輕鬆理解。
★全書示範的四季花材,近400種之多;手繪四季插花作品達70餘幅,物超所值。
本書於20世紀初流行於日本,並再版多次,是一本插花入門書,針對非花道專業人士以淺顯易懂的方式介紹日本花道「盛花」和「投入花」(盛花及投入花為日本插花的型式,盛花使用淺水盤之類的廣口花器,投入花則使用花瓶。)
以手繪圖畫表達相對複雜的內容,注重實用性,插花與掛畫的配合、插花與居室環境的配合等,範例眾多,示範的四季花材近400種。書中收錄手繪四季插花作品70餘幅,各附有使用的花材詳解,是插花初學者學習和收藏的佳作。
作者簡介:
有吉桂舟
別號松竹庵,屬於日本花道池坊流門下。
章節試閱
盛花的起源
當今廣為流行的盛花〔1〕,被不少人視為一種獨立於各流派之外的特殊花法。說到插花的起源,大約中國和日本皆古已有之,而具體於何時興起,則概觀坊間種種傳說,均無確證,難為信論。其中一說,乃
謂在遠古的神代〔2〕,地神彥火火出見尊在日向國〔3〕海邊遺失了天釣針,由名為潮路翁的老人尋獲歸還,其時,老人將當地繁茂的千草萬花插於器皿內以為供奉,令神尊甚為滿意,由此插花之技廣傳於世。據說
至人皇第三十四代推古天皇〔4〕在位時,聖德太子〔5〕好此道,傳於才通和漢的近臣小野妹子〔6〕,世間才有了有程式規範...
當今廣為流行的盛花〔1〕,被不少人視為一種獨立於各流派之外的特殊花法。說到插花的起源,大約中國和日本皆古已有之,而具體於何時興起,則概觀坊間種種傳說,均無確證,難為信論。其中一說,乃
謂在遠古的神代〔2〕,地神彥火火出見尊在日向國〔3〕海邊遺失了天釣針,由名為潮路翁的老人尋獲歸還,其時,老人將當地繁茂的千草萬花插於器皿內以為供奉,令神尊甚為滿意,由此插花之技廣傳於世。據說
至人皇第三十四代推古天皇〔4〕在位時,聖德太子〔5〕好此道,傳於才通和漢的近臣小野妹子〔6〕,世間才有了有程式規範...
»看全部
作者序
譯者序
本書原名《實地圖解現代四季盛花投入教本》。作者有吉桂舟,別號松竹庵,屬於花道池坊流門下,但查不到其他更多的資訊。原書初版於1929 年,在東京由《現代盛花投入刊行會》發行。從現存舊書的情況看,前後再版多次,在1932 年還由東京先進堂
書店刊行過一次,應是當時較受歡迎的插花理論書之一。本稿是根據先進堂版翻譯的。
本書最大的特點是淺顯,是一本介紹日本花道“盛花”和“投入花”的入門級的教材,甚至幾乎可以說是提綱式的小冊子,相對複雜的內容都盡可能通過圖解來說明,總字數很少。作者雖屬池坊流,但內容多為...
本書原名《實地圖解現代四季盛花投入教本》。作者有吉桂舟,別號松竹庵,屬於花道池坊流門下,但查不到其他更多的資訊。原書初版於1929 年,在東京由《現代盛花投入刊行會》發行。從現存舊書的情況看,前後再版多次,在1932 年還由東京先進堂
書店刊行過一次,應是當時較受歡迎的插花理論書之一。本稿是根據先進堂版翻譯的。
本書最大的特點是淺顯,是一本介紹日本花道“盛花”和“投入花”的入門級的教材,甚至幾乎可以說是提綱式的小冊子,相對複雜的內容都盡可能通過圖解來說明,總字數很少。作者雖屬池坊流,但內容多為...
»看全部
目錄
前編
第一篇 盛花
第一章 盛花的起源
第二章 世間對花的愛賞
第三章 盛花的趣味
第四章 盛花之姿態
第一節 洋風盛花
第二節 和風盛花
第三節 盛花的基本花形
第五章 花器與花留
第一節 盛花的花器
第二節 盛花的花台
第三節 盛花的花留
第六章 草木的陰陽及花葉的運用法
第一節 葉物、木物的運用法
第二節 葉組的運用法
第七章 自然與色彩本位
第一節 總說
第二節 自然本位的盛花
第八章 插花時的一般準則
第一節 選擇材料
第二節 插入時的注意點
第三節 色彩的配合
第四節 插入時的協調
第九章 盛花材料的選擇
...
第一篇 盛花
第一章 盛花的起源
第二章 世間對花的愛賞
第三章 盛花的趣味
第四章 盛花之姿態
第一節 洋風盛花
第二節 和風盛花
第三節 盛花的基本花形
第五章 花器與花留
第一節 盛花的花器
第二節 盛花的花台
第三節 盛花的花留
第六章 草木的陰陽及花葉的運用法
第一節 葉物、木物的運用法
第二節 葉組的運用法
第七章 自然與色彩本位
第一節 總說
第二節 自然本位的盛花
第八章 插花時的一般準則
第一節 選擇材料
第二節 插入時的注意點
第三節 色彩的配合
第四節 插入時的協調
第九章 盛花材料的選擇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有吉桂舟 譯者: 金藝
- 出版社: 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6-01 ISBN/ISSN:978957053002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開數:18開
- 類別: 中文書> 生活風格> 園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