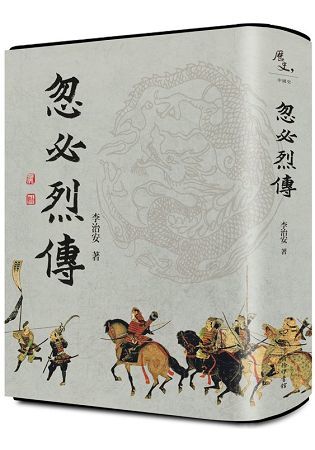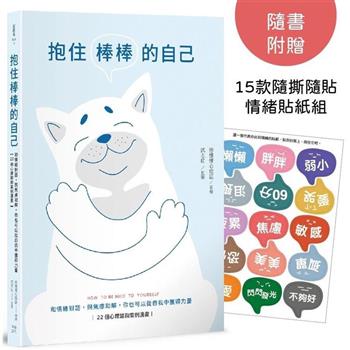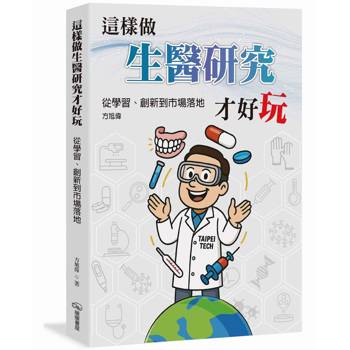對忽必烈的一生作了全面系統的介紹。
讀完這本傳記,相當於看懂了前半部元史!特別是蒙古各個部落乃至黃金家族的內戰寫的很細!
對蒙古帝國到元朝一系列歷史有清晰的評析。
讀完這本傳記,相當於看懂了前半部元史!特別是蒙古各個部落乃至黃金家族的內戰寫的很細!
對蒙古帝國到元朝一系列歷史有清晰的評析。
成吉思汗以征服震撼世界
忽必烈以文治著稱於天下
馬可波羅給予忽必烈很高的讚譽:
「大可汗,是一個最智慧,在各方面看起來,
都是一個很天才的人,他是各民族和國家的最好君主。
他是一個最賢明的人,韃靼民族從來所未有的。」
成吉思汗以蒙古的鐵騎掃蕩了歐亞大陸,建立起蒙古大帝國聞名,但是,如何去統治管理一個文化先進、經濟發達的地區,成吉思汗沒能來得及回答,而忽必烈基本上解決了這一點。他在一批蒙漢臣僚的幫助下,依照漢法建元改制,所制定和實行的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政策既為元朝的百年江山奠定了基礎,也為後來的清朝統治者提供了非常珍貴的經驗。
本書不僅是描繪一位王朝開創者忽必烈汗的偉業,更注意到蒙古原有文化對於忽必烈決策上的影響,如何成為複雜民族與文化的共同帝王,是忽必烈終其一生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讀者理解與閱讀此傳記應具備的起點。
「忽必烈是一個世界性的帝王,在十三至十四世紀的各種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形象,名滿天下。……他獨有的成功在於將自己從游牧征服帝國的大汗轉變成能有效統治定居社會的帝王。」—美國漢學家羅沙比(Morris Rossa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