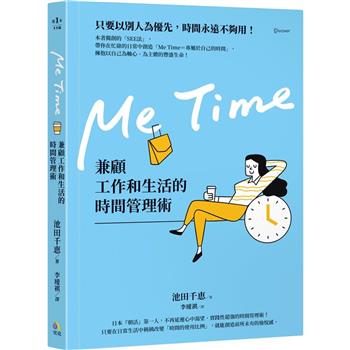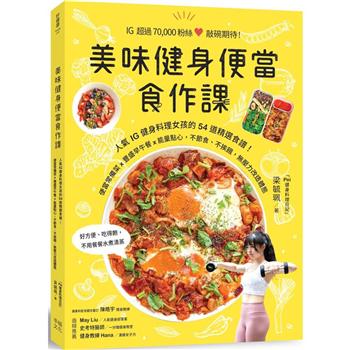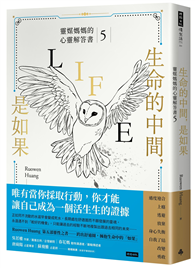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奔跑吧!爸爸的圖書 |
 |
奔跑吧!爸爸 作者:金愛爛 / 譯者:許先哲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01-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224 |
Literature & Fiction |
電子書 |
$ 238 |
小說 |
$ 255 |
文學作品 |
$ 289 |
小說/文學 |
$ 306 |
韓國文學 |
$ 316 |
中文書 |
$ 316 |
其他各國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韓國文壇最大的收穫
廿一世紀最受矚目作家
金愛爛
震驚韓國文學界的第一部作品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Jean Marie Gustave Le Clézio),推崇金愛爛是韓國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家之一。
23歲初試啼聲,金愛蘭以描述五個女生宿舍生活的短篇小說〈不敲門的家〉拿下文學大獎。2005年的作品《奔跑吧!爸爸》成為《韓國日報》文學獎最年輕的獲獎者,被媒體稱為「韓國文壇最大的收穫之一」。接下來她獲獎不斷,2013年更以《沉默的未來》拿下韓國最有影響力的文學獎─李箱文學獎,並創下最年輕得主的紀錄。2014年以《噗通噗通我的人生》為臺灣讀者所熟知。
「每當我想像爸爸,眼前總會浮現出一個場景:那是爸爸朝著某處全力奔跑的身影。爸爸穿著粉紅色夜光短褲,他有一雙毛茸茸的小細腿。爸爸筆直地挺著腰板、抬腿舉膝奔跑的身影,如同一個墨守成規的死腦筋官員的臉,讓人感到頗為滑稽……爸爸漲紅著臉露出兩排黃牙咧嘴傻笑,彷彿有人在爸爸的臉上惡作劇,貼上了不堪入目的塗鴉。」~~〈奔跑吧!爸爸〉
本書由9部短篇小說構成,涵蓋了家庭問題、城市和年輕人、蝸居族、現代社會人際關係的冷漠等主題,作者用細微的觀察、新鮮的感覺和豐富的細節,出色地描寫了年輕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狀態,再現了以創傷、痛苦、悲哀為代表詞的韓國現代文學。
他開始想像,整個屋子變成一條長滿紙鱗的魚,柔緩地在世界裡游來游去。他覺得自己緊貼在魚鰭旁,又似乎正好相反,自己是身在魚腹中。他不知道哪裡是裡面,哪裡是外面。他看到待在原地的自己,隨著魚的舞動而蕩漾起來。所有一切都異常真實,可這時某處傳來了沙沙的聲響。他嚇一跳,趕緊環顧四周。再次傳來一陣沙沙的聲響。低頭望向地板,發現四處散落著沙子。他用手掌掠過地板,竟然是真的海沙。眼前所見令他不敢置信,眨了眨眼睛。從數千張魚鱗之間,抖落出無數的沙粒。魚鱗款款飄擺,吹起了他的頭髮。他閉上雙眼深呼吸,呢喃著「這是真實的」。他想,只要貼上最後一張便利貼,魚會搖動著鮮活的背脊,帶著自己游向某處。
*孤獨感和奇妙的想像在金愛爛的筆下像是趁著月光爬到屋頂跳舞的猴子一樣靈活生動, 哪怕是現實生活的失落,都讓人讀來十分享受。
*金愛爛的作品中藴含了某種欲望的面貌,她想說的不是生命的壓抑,而是生命的迸發。
*金愛爛筆下的城市生活是很眞實的生活,讀者能夠在她的作品中看到自己生活當中「不忍心去看到的各種千瘡百孔」。
作者簡介
金愛爛(김애란)
1980年生於仁川,成長於瑞山,畢業於韓國國立藝術大學表演藝術學院戲劇系。
2002年以短篇小說〈不敲門的家〉贏得第一屆大山文學獎並正式踏入文壇,2005年憑藉《奔跑吧!爸爸》成為大山創作基金和韓國日報文學獎最年少獲獎者,被媒體冠以年度「韓國文壇最大的收穫之一」。之後陸續獲得黃順元文學獎、韓國日報文學獎、李孝石文學獎、今日新銳藝術家獎、申東曄創作獎、金裕貞文學獎、新銳作家獎等多項大獎的肯定,2013年更成為韓國三大最有影響力的文學獎「李箱文學獎」最年輕的得主。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Jean Marie Gustave Le Clézio),推崇金愛爛是韓國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家之一。
作品包括短篇小說集《奔跑吧!爸爸》、《垂涎三尺》、《飛機雲》,以及長篇小說《噗通噗通我的人生》。其中《奔跑吧!爸爸》於2014年出版法文譯本,並榮獲法國Prix de l’Inaperçu文學獎。《噗通噗通我的人生》則已授權臺灣、中國、日本、法國、德國、俄國、越南等多種版本,並被改編拍成電影。
譯者簡介
許先哲
自由職業人,2007年因翻譯《聖誕特典》一書獲得第6屆韓國文學翻譯新人獎,從此踏入文學翻譯的世界。至今已有多部翻譯作品,其中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張石兆家房客們》(金昭晉 著),短篇小說集《奔跑吧,爸爸》和《垂涎三尺》(金愛爛 著)。
*本書〈2019作者新序〉及〈解說〉由劉宛昀所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