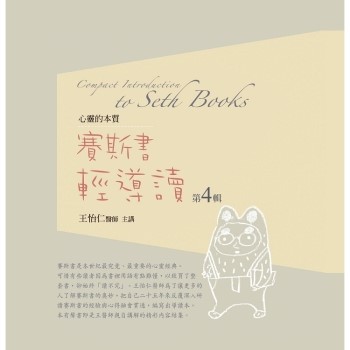圖書名稱:莊子人性論
本書特色
1.闡發人性本真的性情說
2.揭示中國哲學史上人性論的主線
3.對比孟子的道德心,陳述莊子的審美心
面對徬徨未來,你準備好了嗎?
受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啟蒙,
後轉入經典莊子思想,哲學大家陳鼓應老師——
描述鯤鵬展翅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
讓你在茫茫大海中找到方向,展現凌雲之志!
追求精神自由,不離人的心性情
人心,首要重視自我的生命
人性,在於保持天真的本質
人情,激發創造生命的潛能
透過深入自我的深層底蘊,達到游刃有餘的境界
儒家強調道德人生,而道家側重藝術人生。兩者的匯合又更能彰顯出中國文化的特質。——陳鼓應
先蹲低,再跳高
人生高遠的境界,並非一蹴而就,需要拾階而上,層層攀登。
遠大的事業,正需要毅力和耐心一點一滴地累積出來,
人的心靈由沉積而高舉。
懂得知足,反璞歸真
人們依其自然真性去生活,萬物各具有獨特屬性,
人與萬物共生並存,泯除階級之別,
世界能包容萬物的多樣性。
累積經驗,豐富生命
彰顯生命的本真面向,順著性情激發個體生命力量,
追求放達開豁的意境,生命的超越與不息的力量,
實現抱負要有耐心與積厚之功。
作者簡介
陳鼓應
一九三五年出生於福建長汀,一九四九年隨父母赴臺,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三年先後就讀於臺灣大學哲學系及哲學研究所,師從著名哲學家方東美、殷海光。兩度輾轉執教於臺灣大學和北京大學,曾任聘為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現為《道家文化研究》學刊主編。
著作有:《悲劇哲學家尼采》、《老莊新論》、《易傳與道家思想》、《道家易學建構》、《道家的人文精神》、《春蠶吐絲》、《莊子思想散步》、《莊子人性論》等十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