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是時代(人)所創造的!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選書標準,
《閱讀之旅》論及的一兩百本書,
是為今天這時代的大眾而選,
有這一代共同的情感、品味、理想和記憶,
可以視為二十世紀末
台灣社會諸多生命典範
自我回顧最珍貴的剪影!
| 購物比價 | 找書網 | 找車網 |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閱讀之旅(下卷)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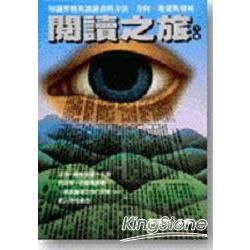 |
閱讀之旅(下卷)【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陳羲芝編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8-05-1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312頁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