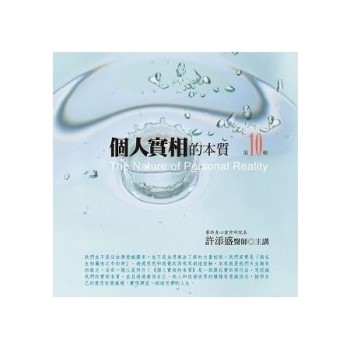國際著名歷史學家費利普.費爾南德-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介紹自文明肇始以來,構成我們這個世界的重要歷史和哲學思想。從食人到禪,從時間到無意識,從邏輯到無序論:世界上最重要的175個思想像晶體一樣清晰地展現在你的面前。伴隨著作者廣博、頗具個人見地的分析,如當代和歷史上、震撼人心的混合式畫卷,使往往難以理解的概念,得以栩栩如生地呈現。
本書以年代為序,體例易於掌握,卻又不拘一格,讀者既可由始至終專研,也可擷取一點流覽。此外,本書突出各原創思想之間的關聯,也提供了專家意見,有助於啟發性閱讀。
作者簡介
費利普.費爾南德-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
是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的歷史學和地理學教授、牛津大學現代史教授,並在歐洲和美國幾所大學任訪問教授。著有暢銷書《千禧年》(Millennium, 1995),《文明》(Civilization, 2000)和《食物》(Food, 2001)。他還常常為《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等國家級報刊撰稿;曾為第四頻道的《一個軍火商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Arms Dealer)和BBC2的《亨利五世》(Henry V)撰稿和播音,為BBC2的東尼獎(Tony Award)系列片《艦隊》(Armada)撰文,贏得了新聞聲望。他還為BBC/CNN根據自己的著作拍攝的十集系列片《千禧年》(Millennium)撰文,經常出席BBC第四電台的時事節目《分析》(Analysis)。
譯者簡介
陳永國
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文學博士,曾擔任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英語系訪問學者、美國杜克大學英語系富布賴特學者,現任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規劃專案和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出版資助專案《結構主義之後的西方文論》。曾獲社會科學類著作獎(省部級,2001)和寶鋼教育獎「優秀教師獎」(國家級,2001)。
2000年以來發表專著《海勒》和《文化的政治闡釋學:後現代語境下的詹姆遜》兩部。代表作品有論文《互文性》、《翻譯的不確定性》、《翻譯的文化政治》;以及在 Perspective: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和Ariel等國外刊物上發表的學術論文。主編項目包括:話語行動叢書、思想譯叢、《福柯的面孔》、《尼采的幽靈》、《後現代性的哲學話語》、《現代性:基本讀本》等。個人譯著有《謀殺者的時代》、《游牧思想》、《作為修辭的敘事》、《德國悲劇的起源》。合譯作品甚豐,其中《現代和現代主義》、《後現代歷史敘事學》、《美國思想史》等負責主譯和全書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