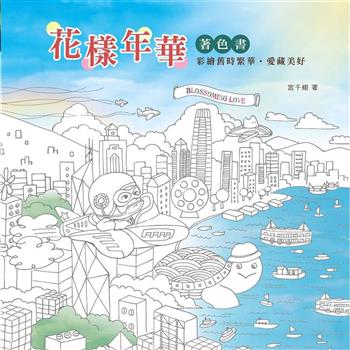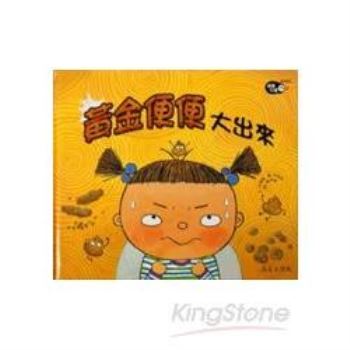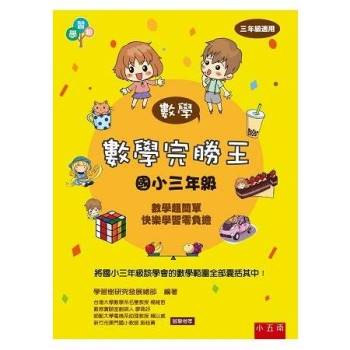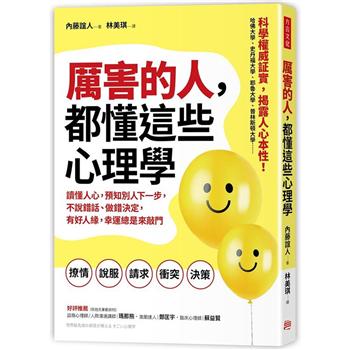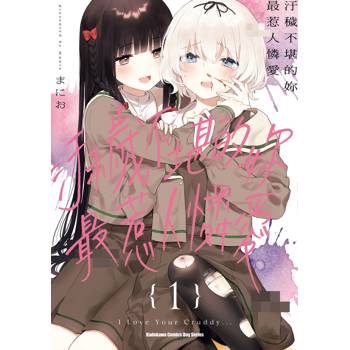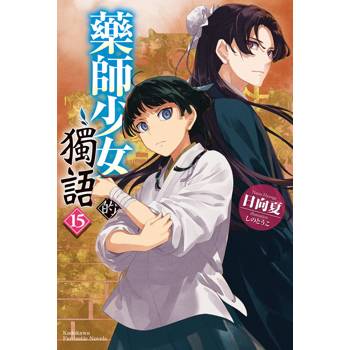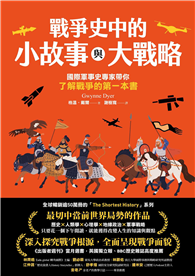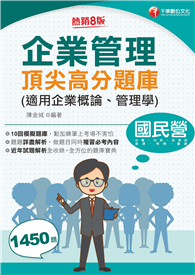天文種子的萌芽
天文,對於每個人似乎都有著說不出來的吸引力,尤其是無憂無慮的小孩子,好像一生下來就設定好了要當這個世界的探索者,每看到一閃、一閃亮晶晶的星空,就會東指、西指,用臭奶呆的聲音問大人:「那是什麼?」「為什麼會……」
1986年,是哈雷彗星最近一次造訪地球的一年,對於國小高年級的我們來說,銀河,聽說過;彗星,聽說過;北斗七星,也聽說過。但是,能否親眼看到這些心目中的「奇景」,無論身在台北或嘉義,都以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當時的資訊不像現在發達,對於看星星的要訣從未得知。也因此,腦海裡總是有個自我矮化的屏障擋在那裡,以為這些美麗的星空只有在國外才看得到,從此沒想過要抬頭好好地看看這塊土地上的星空!就像是當時的電腦,聽說很好玩,卻只能在別人家裡才看得到一樣的感覺。
就在這樣先入為主的觀念下,小時候的夜空,似乎總是飄著幾朵白雲,而雲縫中的灰黑色背景,「應該」沒有星星的蹤影。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台北的光害還不是這麼嚴重,但是門前的路燈、街上的招牌,同樣奪去昌任想看彗星的念頭。對詩怡來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努力說服媽媽買到生平的第一本天文書,那是一本介紹哈雷彗星的專刊,看著書中的照片,只能暗自感嘆無緣親眼看到彗星。
升學主義掛帥的時代裡,國中童軍課要是能實際打個繩結、升火烤烤肉,就算是很了不起的了。大多數藝能科時間,都被用來加強課業,學校更不可能在假日晚上或寒、暑假舉辦夜間觀測星星的活動。和我們同樣是六年級的同學應該都有類似的回憶吧!就這樣,曾經對星星的熱情,被升學壓力擠壓到沒有生存空間。還好,偷偷藏了一絲殘火在心中的角落,等待時機延燒開來。
巧遇在師大地球科學系
高中時期的詩怡和克林、大媽兩位死黨,一起出錢合訂牛頓雜誌,覺得每人每年可以看到完整十二個月份的雜誌,還可以分到四本雜誌收藏起來,實在很划算。每次收到雜誌,三個女生就會擠在一起看,對著雜誌中的星空照片、宇宙新知等天文話題指指點點。有一次在校園內看到參觀 NASA(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的暑期營隊活動海報時,詩怡心中雀躍不已,但是費用實在太高,最後只能繼續看著雜誌,望梅止渴,幻想自己就是照片中的天文學家。現在回想起來,不禁莞爾一笑。每個人小時候應該都曾有過這種偉大的志向吧!長大後,這個夢想沒有實現,卻實現了另一個夢想——當老師。
從高一開始,昌任就對數學產生恐懼感,每次考試最差的就是數學。大學聯考第一天的第一個考試科目,偏偏就是數學。雖然已經做了該有的準備,很奇怪的,一看到考卷,恐懼就油然而生。其實當天看到考題時,心中有些興奮,也有些忐忑不安,原本最擔心的科目,似乎不是很難。可能因為如此,回家對答案時才發現,由於興奮過度,竟然有將近20分的答案因為最簡單的加減乘除而算錯了,心中鬱卒了好久。而詩怡的數學,也是犯了粗心大意的致命傷,變成所有科目中考得最差的一科。繳交志願卡的日子一天天逼近,考量自己的興趣和爸、媽的建議,我們都將師大放在志願卡上最有可能的位置。錄取成績公布後,原本昌任以為進了師大化學系,心想至少還是個蠻感興趣的科目,但仔細一看才發現,雖然總成績在錄取分數之上,可是數學加權計分後,還是進不了化學系。又是可惡的數學搞的鬼!
就這樣,高中時代令我們感到困擾的數學,反而將我們兩個送進了另一個美麗境界——師大地球科學系,從此踏入快樂的天文領域。
連北斗七星都不會認的兩個人,從來沒想過會走進天文這個美好的世界。
聯考分數,註定讓我們一起到師大地球科學系,接觸夢寐以求的天文課程。不會看星星的都市孩子,第一次體會到台灣星空之美,也讓兩個瓶子從此沈浸在星空中。大二的天文實習課就像是國術的馬步,是跨入天文的基本功,而昌任老爸贊助的單眼相機,則是一切的開始。
首度接觸天文
其實,地球科學系在我們大學聯考時代算是個冷門科系,對於高中第一志願畢業的人來說,似乎不太風光。直到開學後,開始享受真正的大學生活,尤其是每個學期至少一次的野外考察活動,才讓我們身上被積壓已久的好動基因,有機會活絡起來,漸漸慶幸當初自己的數學考砸了,進到這麼一個最適合我們的科系。
大一對於天文方面的學習,僅有修習地球科學概論的那幾個月時間,感覺上天文就像是一杯烏龍茶,硬是要你在短時間內馬上喝下去,會是一種折磨,但是如果細細品嚐,每一小口的回甘滋味都是人生一大享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天文學課程,在大二下學期才正式展開,而在大一下學期就已經是地科系特產班對之一的我們,在星路歷程上,同時開始(每次說到班對,不免要很驕傲地告訴大家,我們全班36人,有7對班對在畢業後陸續都結婚了喔)。
運氣很好的是,輪到我們這一屆上天文學概論與天文學實習課程的時候,傅學海老師剛學成歸國,對於我們這批大學生要求很嚴格,再加上當時學制的關係,我們上了足足一整年6學分的天文課程。從天文學到天文觀測、天文分析實驗,都在一年內逐步學習,也因此比別人有更多的時間好好從基礎攝影學起。從自己分裝底片、沖片,到利用暗房設備洗出第一張自己拍攝的相片,以前那些專業人士才做得到的事,居然都會了。當然,這一切的源頭,都要來自於一台屬於自己的單眼相機。
聽傅老師說,天文攝影需要一台機械式單眼相機,昌任回家後向老爸提及這件事,才憶起小學時代的往事。從前家中有台很好的Canon單眼相機,但是在二十幾年前中和的六三水災中泡湯了。往事歸往事,老爸馬上答應讓昌任去挑選一台適用的單眼相機。真的要感謝老爸對於孩子在學習上的需求總是毫不吝嗇。
當時的我們對於攝影器材認識不多,看了看攝影雜誌,很滿意地開出了一張購買清單:Nikon FM2機身、50mm f/1.2標準鏡頭,心想,如果再加上一支300mm f/2.8的望遠鏡頭,那就什麼都可以拍了。沒考慮到價錢的問題就列出這張清單,直到訪價後才發現,那一支Nikon 300mm f/2.8的鏡頭就要將近20萬台幣!最後,老爸阿殺力的出錢買了機身與標準鏡頭,這套器材就成了我們踏進天文攝影最重要的基本裝備。至於300mm f/2.8的鏡頭,以後再說吧!
為期一年的天文實習課程,逐漸進入尾聲,但也是最令我們興奮的大雪山觀星活動來臨的時刻。昌任在高中時代就很想要參加登山社所舉辦的活動,但是基於安全考量,總是無法獲得爸媽的同意。現在雖然我們不是步行登山,但是終於可以名正言順的去享受一下高山的氣息,更希望能藉此機會拍下以前所不敢奢想的星空。
星星會因為地球自轉而看起來東升西落,如果只是將相機鎖在腳架上長時間拍攝,拍出來的就是星跡照片了。這樣的照片很美,但就是少了點專業的感覺,也無法讓星光累積在底片上同一點,而拍出更暗的天體。要拍出一點、一點漂亮星點的星座照片,就要會操作能追著星星跑的赤道儀。天文儀器的操作,就像是學開車一樣,多次練習會比同一天練習好幾次有效,而且每次練習時,最好都有教練在旁,立刻改正錯誤的動作,這樣進步最快速!高中時代就已接觸天文攝影的學弟——佑子,就像汽車駕訓班的專屬教練,讓我們對赤道儀的機械構造和對極軸的功夫,短時間內增進不少。還沒上山,兩人已經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了。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追星族的天空奇緣(彩色精裝)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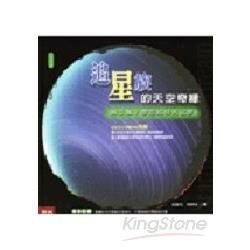 |
追星族的天空奇緣(彩色精裝) 作者:吳昌任、林詩怡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355 |
科學‧科普 |
$ 356 |
天文觀測/星座 |
$ 356 |
普及科學 |
$ 396 |
中文書 |
$ 396 |
天文/地球 |
$ 405 |
天文觀測/氣象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追星族的天空奇緣(彩色精裝)
康德:「有兩件事情,我愈思考愈覺得神奇,…,一是頭頂上的星空,一是人心中的道德準則。」
對許多人來說,頭頂上的這一片星空,除了神奇,還點綴了許多美好的回憶。
本書所呈現一對天文狂夫妻檔對天文的痴與狂,不只是星星,還有真誠的感受、經歷與想像,希望讀者們能用看故事的心情同遊天文夢。
本書也是一本非常實用的認識星空導覽書。書中特別設計「星八課」主題,帶領想一探星天奧秘的讀者,由淺入深地親近天文學,認識美麗的星空。
作者簡介:
吳昌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研究所天文組碩士
曾任台北市立南門國中地球科學教師
現任台北市立南湖高中地球科學教師
林詩怡
國立台灣示範大學地球科學研究所科教組碩士
曾任台北市立塯公國中地球科學教師
現任台北市立中崙高中地球科學教師
共同經歷
擔任觀星人雜誌編輯顧問群
擔任永和社區大學「星星月亮太陽」講師群
與傅學海等合著《星星的故事》一書
與魏毓瑩合譯《從哈伯看宇宙》一書
章節試閱
天文種子的萌芽天文,對於每個人似乎都有著說不出來的吸引力,尤其是無憂無慮的小孩子,好像一生下來就設定好了要當這個世界的探索者,每看到一閃、一閃亮晶晶的星空,就會東指、西指,用臭奶呆的聲音問大人:「那是什麼?」「為什麼會……」1986年,是哈雷彗星最近一次造訪地球的一年,對於國小高年級的我們來說,銀河,聽說過;彗星,聽說過;北斗七星,也聽說過。但是,能否親眼看到這些心目中的「奇景」,無論身在台北或嘉義,都以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當時的資訊不像現在發達,對於看星星的要訣從未得知。也因此,腦海裡總是有個自我...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吳昌任、林詩怡
-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ISSN:9570829214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2頁
- 類別: 中文書> 科學> 天文/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