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給青年學生的十封信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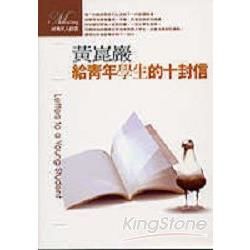 |
給青年學生的十封信 作者:黃崑巖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05-1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135 |
社會人文 |
$ 174 |
生活哲學 |
$ 174 |
社會 |
$ 174 |
聯經出版 |
$ 194 |
中文書 |
$ 198 |
社會人文 |
電子書 |
$ 220 |
個人成長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給青年學生的十封信
台灣的大專學生與外國學生相較,有成熟緩慢而延後的現象。本書作者認為該現象產生的因素,多半緣於青年人不知為誰而讀、為誰而工作、為誰而活。
本書十封信:
1. 愛因斯坦、倫琴與聯想力
2. 學習外語的訣竅
3. 閱讀是終身學習的唯一途徑
4. 象形文字的現代問題
5. 智識分子與知識分子
6. 研究不是專業名詞,是生活的態度
7. 為什麼要求學?
8. 勇於提出合理建議,社會才會進步
9. 你的典範是誰?
10. 如果我重做大學生,非常切中上述現象,也提供了思考與解決的脈絡,適合所有青年學子,為人父母、師表者,甚至一般人閱讀、參考。
作者簡介:
黃崑巖
美國華盛頓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博士。曾任美國海軍醫學研究院研究員、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教授、上海醫科大學榮譽教授、台大醫學院客座教授、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創院院長及教授、台灣數所大學通識教育講座、Project HOPE(美國霍浦基金會)顧問、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員(臨床組組主任)。
現任全國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主任委員、台灣杏林人文發展協會理事長、遊說台灣加入WHO之NGO團長、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常委、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教育部顧問。他非常關心國內醫學及一般教育的人文內涵,2004年2月總統候選人辯論時,曾以「何謂教養?」問題引起大家省思。
著作有專業性醫學書籍、《莫札特與凱子外交》、《外星人與井底蛙》、《醫眼看人間》、《醫師不是天使》、《SARS的生聚教訓》、《黃崑巖醫師談生命省思──生死關頭見豁達》、《黃崑巖談人生這堂課》、《黃崑巖談教養》(聯經)、《給青年學生的十封信》(聯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