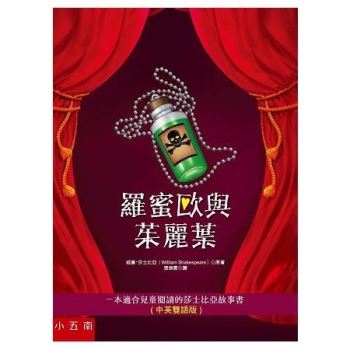四、斷片
在我們與過去相逢時,通常有某些斷片存在於其間,它們是過去與現在之間的媒介,是布滿裂紋的透鏡,既揭示所要觀察的東西,也掩蓋它們。這些斷片以多種形式出現:片斷的文章、零星的記憶、某些殘存於世的人工製品的碎片。既然在我們與過去之間總有斷片存在,思考一下它屬於哪一類範疇以及它怎樣發揮作用,是值得的。
一塊斷片是某件東西的一部分,但不只是整體的某一成分或某一器官。假如我們把各種成分組合在一起,得到的是這件東西的本身;假如我們把全部斷片集攏起來,得到的最多也只能是這件東西的「重製品」。斷片把人的目光引向過去;它是某個已經瓦解的整體殘留下的部分:我們從它上面可以看出分崩離析的過程來,它把我們的注意力吸引到它那犬牙交錯的邊緣四周原來並不空的空間上。它是一塊「碎片」:它與整體處於一種單向的、非對換的關係中。假如留存下來的是一部文學作品的梗概、內容目錄或者好幾章連續不斷的文字,那麼,我們說,這些留存下來的並不是斷片:所謂斷而成片者,就是指失去了延續性。一片斷片可能是美的,但是,這種美只能是作為斷片而具有的獨特的美。它的意義、魅力和價值都不包含在它自身之中:這塊斷片所以打動我們,是因為它起了「方向指標」的作用,起了把我們引向失去的東西所造成的空間的那種引路人的作用。
對髑髏的觀照不僅僅使我們想到死亡:髑髏的無名無姓也使我們感到痛苦。個體消失在類體之中;我們想要深入進去,發掘出個體來,但是,類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仍然是個難以解決的問題。相比起來,留做紀念的一撮頭髮則是一件真正的斷片,它使我們想起它的主人,那個個別的人。作為死亡提醒物的髑髏是換喻物(它代表它所屬的那類事物的類性或概念)。那撮頭髮,那件真正的斷片,則是舉隅物,是時間的寵兒。招魂的儀典需要死者的某一項遺物,這件遺物所起的就是斷片的作用,這個斷片所屬的世界,本身是而且幫助形成了一條連接過去與現在的紐帶。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任何文學作品都是一個搭配齊全的整體,它自身就是一個統一體;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又可以說,任何文學作品自身並不是真正完整的,它更多地根植在超出作品之外的生活中和繼承得來的世界裡。每一種文明都有它自己渴望去認識的東西,也有它盡力迴避、寧願視而不見的東西,在這方面,每個文明各有不同。西方的文學傳統傾向於把要表現的內容絕對局限在作品裡,就像《伊里亞德》中阿基里斯的盾牌一樣,自身就是個完滿的世界。中國的文學傳統則傾向於強調作品與活的世界之間的延續性。然而,除非我們曾經生活在作品寫成的那個時代,讓活著的世界如同作品描寫它時那樣展現在心裡,否則,作品根植其中的那個活的世界,對後世的讀者來說,就成了一片由失落而造成的空白。作品的號稱屬於綿延不斷的活世界的語言,就成了作為斷片的語言。
《聖經》可以視為是西方傳統中的原型書(Bible的原意就是指「書」),在西方文學思想的傳統中,無論是外在的方面還是內在的方面,它都被用作寫作的典範。它是有形的、可以隨身攜帶的萬物之道,相當於上帝心目中的生活世界。《聖經》有完整的時間結構,它以「起初」作為〈創世記〉第一章的第一句,以日子將要到頭時的〈啟示錄〉來結尾。沒有忽略任何真正有意義的東西:這是一篇內部完整的文字。
《聖經》的自身完整同亞里斯多德派強調內部整一性和必然性的主張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西方文學和西方文學思想中占主導地位的觀念。對什麼是完整和什麼是內部整一性的解釋發生過變化,但是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這種觀念。因此,當德萊頓(Dryden)在他的〈論劇體詩〉中反駁新古典主義對早期英國戲劇的抨擊時,不是摒棄完滿整一性的觀念,而是對整一性作了更為複雜的解釋。
我們的戲劇除了主要的構想之外,還有與不太引人注意的人物和劇情有關的次要的情節和偏離正題的東西,它們隨著主要情節的發展而發展:正如人們所說的天體,它們就像在其中有一定軌道的星球,雖然它們有自己的運動,但還是在天體運動的作用下公轉,它們屬於這個天體。在英國的舞臺上完全可以看到相似的表現;如果相反的運動就其性質而言可以相成;如果星球可以同時既朝東又朝西——一方面藉助它自身的運動,另一方面依靠始動者的力量,那麼,不難想像,次要情節隨著主要情節的發展而發展是很自然的事,前者同後者並不對立,它們之間只不過是有區別而已。
詩人據以形成他的「主要構想」的模式,在這裡說得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
有人可能會反對說,自從浪漫主義時代以來,「高雅」文學似乎已經轉向注重於不完整和不對稱了。然而,這種轉變的根源是一種浪漫主義的斷片理論,這種理論所說的歸根到底並不是真正的斷片,它不過是較早的完整和整一性理論的一種新的變體而已。德國浪漫主義者諾瓦利斯(Novalis)的《詩人聖殿》中的「花粉」,寫的就是這種假斷片。
還沒有人發現過寫書的藝術,然而它快要被發現了。這種斷片是文學家播下的種子。其中自然有許多癟種——然而,總有一些會生根發芽!
這種理論斷片的涵義同樣也適用於在浪漫主義時代已經初具規模的抒情詩;現代人鍾情抒情詩(通常人們把抒情詩用作詩的代名詞),與這種浪漫主義的斷片理論不無關係。然而,我們在這裡看到的不是真正的斷片而是種子,種子把整體作為未來的可能性包藏在自己體內。它是處於胚芽狀態的神性的邏各斯,盼望播到讀者的心裡時完滿地實現它的未來的可能性。
儒家典籍是由若干部不同的經書組成的,它們所起的作用與《聖經》相仿。西方的那種上帝循之以創造世界和《聖經》、詩人循之以舞文弄墨的方式,在這些經籍中是找不到的。最稱得上有相似之處的,要算是《易經》了,它系統地記載了所觀察到的物理世界的狀態。不過,我們可以看到,經典的權威主要不是來自系統的說明,而是來自編輯時的獨具慧眼的選擇:就像孔子在整理修訂《春秋》時選出有意義的事件和言簡意賅的詞句,或者他在編訂《詩經》時從篇幅更大的詩集裡選出有代表性的詩篇(以及在編選《尚書》時對文件、文獻的處理)。不過,最能體現人的思想和一個人的個性的要數《論語》,它記載了孔子的言論。
《論語》貯藏的滿是斷片,這是最值得注意的,這些斷片就是孔夫子的弟子們碰巧聽到、記得和保存下來的他的一些話。這些弟子們轉述了一位「述而不作」的人所說的話:現在輪到他們來「述而不作」了。每當我們讀到《論語》時,我們就會想到,孔子在他的一生中還談起過許多別的有價值的事,他智慧的別的斷片現在已經丟失了。更重要的是我們會想到,我們現在讀到的,也不是孔子就這件事所能說的全部的話,他本來有可能對這件事再說上許多,已經說出的這些話只不過是根據情況隨感而發的,導致他說這些話的智慧遠遠超出於這段具體的言辭。這種類型的言簡意賅的言辭,是一種標誌,表明它們是不完整的,它們的寓意比它們自身更為深刻。由於這些言辭是片斷不全的,我們的注意力就被引向那個已經一去不復返的生活世界。傳統注釋家所做的工作就是用這些言辭搭起一個框架——既用通常的注釋方法來注解,也提供個人生活的和歷史的背景以及臆測的具體場合,以告訴我們孔夫子為什麼這麼說,是對誰說的,談話對象對他的表達有什麼影響,在什麼環境裡有可能會引出這樣的反應來。
同《聖經》一樣,《論語》也是一個意義深遠的表率,幾千年來它一直在教導讀者應該怎樣去理解另一個人的思想。當你能夠從只有經驗豐富的眼睛才能勉強辨認出的地方,得到作品的表面拒絕提供給你的那種智慧和深沉的感情時,你就得到了為「含蓄」設立的獎品。作品本身是不完整的;只有在我們面向那些失落的與外部的關係時——與作者、環境和時代的關係,它才變得完滿了。
中國的古典詩歌是從《詩經》裡的詩延續下來的;它們與《論語》裡斷片狀的格言之間也有血緣關係,這一點承認的人就比較少了。如果說,西方的詩人暗地裡希望成為類似在錯綜複雜的主要情節中能控制局勢發展那樣的人,或是在世界播下種子的人,那麼,中國的詩人則暗地裡希望能成為聖人。詩人的用語同孔夫子的用語一樣,都是為了把讀者領向某種隱而不露的深處;它們只不過是從一個已經作古的、生活在他自己時代的、性格和社會關係豐富的人身上殘留下的斷片。雖然古典詩歌有整一的形式,它還是把自己作為更大的、活動的世界中的一個部分。由於這樣,它斷言自己的內容是有省略而不完整的,斷言它的界限割斷了它的延續性;這就提醒了讀者,告訴他們有鴻溝等待他們去填補。
有的詩人看到了語詞無法完滿地表現周圍的環境,無法盡數記載它們所應記載的感情,他們高貴而勇敢地接受了事情的真相;他們把他們的讀者出其不意地拋進詩裡,然後再拽出來,讀者還在尋找答案,仍然沒有得到滿足。
為了搞清楚對我們來說這樣的詩人如何在死後繼續存在,我們不妨來看一看對他們來說其他人是如何在死後繼續存在的。我們要尋找的是重複的疊影,是斷片與斷片銜接的鏈條。我們要物色的是一則描寫當時經驗的用詩表現的斷片,這種經驗又與接觸到來自更古的過去的斷片有關。李賀(七九一—八一七年)的〈長平箭頭歌〉就是一首這樣的詩:
漆灰骨末丹水砂,
淒淒古血生銅花。
白翎金簳雨中盡,
直餘三脊殘狼牙。
我尋平原乘兩馬,
驛東石田蒿塢下。
風長日短星蕭蕭,
黑旗雲濕懸空夜。
左魂右魄啼肌瘦,
酪瓶倒盡將羊炙。
蟲棲雁病蘆筍紅,
回風送客吹陰火。
訪古汍瀾收斷鏃,
折鋒赤璺曾刲肉。
南陌東城馬上兒,
勸我將金換簝竹。
他一下子把我們拋進去,讓我們去面對事物,面對它現在的模樣。「漆灰」、「骨末」、「丹砂」,他用來稱呼事物的不是事物本身的名稱,他用的每一個名稱都與其他名稱相互否定,沒有一個是這件物品的正名。這些誤名把我們帶進了李賀的思想活動中,他自己對物品的性質也還琢磨不透:他拿著一塊有一定形狀但是不知為何物的東西,這塊東西以前顯然是某種物品,然而現在卻失去了原有的外形,無法把它歸類,難以準確地稱呼它——煙黑色的「漆灰」(漆是用在盔甲上的);星星點點的白斑也許是細碎的骨渣;「丹砂」則是指乾了的血痕留下的鏽紅色。凡是有過從地下拾起一塊年代久遠的金屬物的經驗的人,都會理解這種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在這裡表現為隱喻,表現為試圖揭去外層假象的猜想。凡是有隱喻出現的地方,總會產生這件事物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然而,在知解的過程中,這些誤稱不是沒有意義的;它們在弄清事物究竟是什麼的進程裡,朝正確的名稱邁進了一步:灰炭是燃燒後的剩餘物;骨渣是死去的而且已經風化的東西留下的遺跡;丹砂則來自汞礦,人們把它作為藥物服食,以求在物質世界中長生不老。對於箭鏃它們是誤稱,作為斷片它們則是正確的引路者,它們是物質世界中的倖存者,使人們回想起碎裂和瓦解的過程。
我們最初用不止一個名字來描繪它,這是一塊其外形會使人產生誤解的東西,它表面的外形漸漸被揭開,物體的真實面貌逐步顯露出來。「淒淒古血生銅花」。這裡的「淒淒」指的不只是寒涼悲傷之情,它也指圍繞在物體四周的一種情態,古代金屬在手指上的陰冷感使得心裡湧出一陣陰沉憂鬱之情,一陣寒慄從手指傳遍持物者的全身,孤零零的物體再加上荒寂的景色,這些都構成了這種情態。揭去外形的污垢,我們看到了金屬物,不是黃燦燦的銅而是發綠的銅,在鏽跡斑斑的銅綠中,有的地方已經腐蝕發爛了,這些地方留有血跡,血跡在銅綠之中猶如「花朵」。這裡是死去的東西與新的生活的接觸點,生活雖然是新的,但已經受到玷染,已經變了色:綠色的花朵是由紅色的血跡導致的腐蝕留下的斑痕,由它們開始而使物體失去了原來的面貌,成了我們手裡的這塊東西,正如茂盛的穀物遮蓋住了周朝都城的遺址一樣。這些銅花生出的準確時間在歷史上是有記載的,當時,趙國的大批降卒被秦國的軍隊坑殺於長平戰場。在這些銅花之下隱藏著這一歷史事件,銅花把它保存下來,它們是永不褪色的。
在除掉表面污垢以發現其中存在的東西的同時,他也發現了其中已經失去的東西,「白翎金簳雨中盡,直餘三脊殘狼牙」。血帶來了花朵,雨卻引起腐爛。詩人在心中把已經腐蝕掉的東西重新構建起來;箭桿曾經從兇殘的秦軍的弓上射出來的,秦國當時被人稱為「豺狼之地」。「狼牙」就是這一史實的斷片。
我們揭去污垢而得到的物體已經不再是一件完整的物體,一個以其全貌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對象,然而,也不再是一塊渾然不知其為何物的東西。它是一個引路者,把我們引向由於失落而造成的空白,它是一個抓得住的具體物件,由它而生發開去,我們可以找出一連串互為依附的東西來:箭鏃連在箭桿上,箭桿上又連著羽毛,沿著羽毛飛行的軌跡,又可以找到豺狼之師手中的弓,豺狼之師又來自秦國這片豺狼之地,在箭桿上留有狼牙的痕跡。當一個人面對這件物體,除掉它表面的污垢以發現它所失去的與過去的聯繫時,這裡又出現另一部歷史,一部發現箭鏃的歷史。這個故事他能從頭給我們講起。在寫了揭示物體內容的頭四行詩之後,他跳到了發現箭鏃的故事上,這個跳躍是一種含意深長的間斷,它使我們了解到面對斷片時的思想運動。我們被拋了回去,竭力想要在原始的完整和具體的環境裡為斷片找出它應有的位置來。這件物體既是一部失落沉澱的歷史,也是一部尋而復得的歷史。
他對我們講的故事是他在原野裡同一群鬼相遇的事,在這片原野上籠罩著古代蒙難者的陰影。這些鬼饑腸轆轆,無處覓食;沒有人祭奠他們,沒有人關心他們,沒有人認為自己應該對他們負責。而李賀卻下了馬,給他們餵食——把羊肉提供給狼牙的犧牲品。在做完了祭奠和回憶的事之後,他發現了箭鏃。
在中國大部分敍事作品裡都可以找到相互呼應的韻律,即使是類似這一首詩的這種不完整的、以詩的形式來敍事的作品,也是這樣:詩中出現一個行動,就會有另一個具有相應性質的行動來呼應它。我們無法不認識到,發現箭鏃是對他的某種報償。這種報償還需要他自己再作些加工,它是用來報答他對饑餓的死者所做的善事。「訪古汍瀾收斷鏃,折鋒赤璺曾刲肉。」
我們又看到了我們的對象,它不像我們最初看到時那樣是排列在一起的幾個隱喻,現在,它像是一系列相互連鎖的關係——像是餓鬼與詩人的關係的一個象徵,像是一個泫然流涕的場合,像是古戰場上的一個死者。很難說它還稱得上是一個箭鏃;鏃尖折斷了,鏃體上滿是裂縫,上面似乎還沾著古代的血跡,彷彿它曾經造成的傷口已經與它連成了一體。發現這件「物體」的過程所揭示出的不是它的物性和它遠離人的世界的獨立性,與此相反,是它同人的種種複雜的結合。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的圖書 |
 |
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 作者:宇文所安 / 譯者:鄭學勤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11-2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20 |
二手中文書 |
$ 174 |
中國古典文學 |
$ 174 |
文學 |
$ 194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
本書是一個漢學家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是其基於個人感受的對中國古典詩文的印像式批評。作者從汗牛充棟的古典文獻中揀選了十餘篇詩文,出其不意地將它們勾連在一起,通過精彩的閱讀、想像、分析與考證,為我們凸顯了一個中國古典文學的經典意像和根本性的母題:追憶。
作為一個含蘊豐富的思想和藝術行為,追憶不僅是對往事與歷史的復現與慨嘆,也寄寓著儒家知識分子追求「不朽」的「本體論 」的焦慮;更體現了「向後看」這一延續了幾千年的中國文化的傳統和思維模式。
全書不按年代排序,也不求分類闡述,作者通過新穎獨到而又論證充分的闡述與分析,力圖為我們建構一個一追憶的殿堂:「詩、物、景劃出了一塊空間,往昔通過這塊空間又回到了我們身邊。
作者簡介: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年生於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1972年以博士論文《韓愈與孟郊的詩》獲耶魯大學東亞系文學博士學位,隨即執教耶魯大學,1982年應聘哈佛大學,任教東亞系、比較文學系,現為哈佛東亞系詹姆斯‧布萊恩特‧柯南德特級教授和比較文學系主任,是唐詩研究領域首屈一指的美國漢學家。
章節試閱
四、斷片在我們與過去相逢時,通常有某些斷片存在於其間,它們是過去與現在之間的媒介,是布滿裂紋的透鏡,既揭示所要觀察的東西,也掩蓋它們。這些斷片以多種形式出現:片斷的文章、零星的記憶、某些殘存於世的人工製品的碎片。既然在我們與過去之間總有斷片存在,思考一下它屬於哪一類範疇以及它怎樣發揮作用,是值得的。一塊斷片是某件東西的一部分,但不只是整體的某一成分或某一器官。假如我們把各種成分組合在一起,得到的是這件東西的本身;假如我們把全部斷片集攏起來,得到的最多也只能是這件東西的「重製品」。斷片把人的目光引...
»看全部
作者序
前言
《追憶》是嘗試把英語「散文」(essay)和中國式的感興進行混合而造成的結果。在我的學術著作裡,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這本書都產生了最廣泛的吸引力。這一「成功」很有意思,因為《追憶》可以說代表著在一種英語文學形式裡對中式文學價值的再創造。
英語的散文是一種頗有趣味的形式。它和現代中國散文有所不同:現代中國散文強調作者的主觀性和文體的隨意性,而英語的散文則可以把文學、文學批評以及學術研究,幾種被分開了的範疇,重新融合為一體。作為一種文學體裁的散文,必須讀起來令人愉悅;而且,既然屬於文學的...
《追憶》是嘗試把英語「散文」(essay)和中國式的感興進行混合而造成的結果。在我的學術著作裡,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這本書都產生了最廣泛的吸引力。這一「成功」很有意思,因為《追憶》可以說代表著在一種英語文學形式裡對中式文學價值的再創造。
英語的散文是一種頗有趣味的形式。它和現代中國散文有所不同:現代中國散文強調作者的主觀性和文體的隨意性,而英語的散文則可以把文學、文學批評以及學術研究,幾種被分開了的範疇,重新融合為一體。作為一種文學體裁的散文,必須讀起來令人愉悅;而且,既然屬於文學的...
»看全部
目錄
前言
導論:誘惑及其來源
一、黍稷和石碑:回憶者與被回憶者
二、骨骸
三、繁盛與衰落:必然性的機械運轉
四、斷片
五、回憶的引誘
六、復現:閒情記趣
七、繡戶:回憶與藝術
八、為了被回憶
譯後記
導論:誘惑及其來源
一、黍稷和石碑:回憶者與被回憶者
二、骨骸
三、繁盛與衰落:必然性的機械運轉
四、斷片
五、回憶的引誘
六、復現:閒情記趣
七、繡戶:回憶與藝術
八、為了被回憶
譯後記
商品資料
- 作者: 宇文所安 譯者: 鄭學勤
-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11-25 ISBN/ISSN:957083082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16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中國古典文學
|